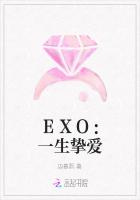不论是从下面他站的地方,还是从现在他的将军们站着的土岗上,就连从俄国和法国军队轮流占领的尖顶堡那儿,人们都无法明白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尖顶堡上又有死人,又有伤员,还有惊恐万状、吓得发狂的活的士兵。那儿一连几个小时枪声、炮声不绝于耳,一会儿只有俄国人,一会儿只有法国人,一会儿是步兵,一会儿是骑兵,出现,倒下,射击,交战,不知道拿对方怎么办,大喊一通,又向后跑去。
拿破仑派出的副官和元帅们派出的传令兵不断带着战报向他飞驰而来,但所有这些报告全是靠不住的,因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不可能说清此刻正发生什么事,也因为很多副官根本就没到达真正的战场,而只是传达了他道听途说的消息,还因为当副官骑马跑二、三俄里路程,来到拿破仑身边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带来的消息也就过时了。比如,总督派一名副官送来消息说,已经占领波罗金诺,科洛恰河的大桥也被法国人拿下。副官问拿破仑是否命令部队过河?拿破仑下令在河这边列队等候;但不仅是在拿破仑下令的时候,甚至副官刚一离开波罗金诺,大桥就被俄国人收复并烧毁了,这正是战役最开始皮埃尔见到的那场战斗。
一名副官脸色苍白、惊惶失措地从尖顶堡飞奔回来,向拿破仑报告说,他们的进攻被击退,康庞负伤,达武战死,而当这名副官得知法国人被击退时,尖顶堡又被另一支法国军队占领,而且达武还活着,只是稍微受了震伤。根据这些肯定靠不住的情报,拿破仑发布了一些命令,这些命令或者在他下达以前已经执行,或者不可能也没有被执行。
距战场更近一些的元帅和将军也像拿破仑一样没有参加实际战斗而只是偶尔去一下枪炮射程以内,他们不请示拿破仑就自作主张,下达了一些从哪儿往哪儿射击,骑兵往哪儿跑、步兵往哪儿冲的命令。甚至他们的命令也同拿破仑的一样很少能够付诸实施,而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与命令相悖的。命令往前冲的士兵们遇到了霰弹,立即往回跑,而命令原地待命的士兵突然发现对面来了俄国人,有些往回跑,有些向前冲,而骑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却去追击逃跑的俄国兵。这样,两个团的骑兵跑过了谢苗诺夫山谷,刚刚上了山,调转马头又拼命往回跑。步兵也是一样,有时根本不是往命令去的方向跑。所有的命令,包括大炮什么时候往哪儿移,什么时候派步兵去射击,什么时候派骑兵去冲撞俄国步兵,所有这些命令全都是队列里离得最近的指挥官们发出的,他们连内伊、达武和缪拉都没请示,更别说拿破仑了。他们不怕因没执行命令或随便下达命令而受处罚,因为在战斗中事关人最宝贵的东西――自己的生命,有时觉得向后跑就能得救,有时向前跑才安全,这要看当时处于战场上的这些人的心情。事实上,所有这些往前跑和往后跑并不会减轻也不会改变部队的处境。他们所有的你冲我撞并没给他们造成伤害,而伤害、死亡和重伤是因这些人在枪林弹雨中来回奔跑时被炮弹和子弹击中的。只要他们一离开炮弹和子弹飞舞的地方,站在他们后面的长官立即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服从纪律,而在纪律的约束下他们又被赶到战区,一到那里(在怕死的心情驱使下)他们又丧失了纪律,按人群当时的情绪左冲右突。
三十四
拿破仑的将军们――达武、内伊和缪拉,离战区很近,有时甚至骑马进入战区,他们数次把大批排列整齐的部队送上战区。但与以往的战场上所发生的情况相反,他们等来的不是敌人溃退的消息,而是出发时整齐的队伍惊惶失措,乱作一团,从那儿逃回来。他们再次组织这些队伍,但人数越来越少。中午,缪拉派副官去见拿破仑,要求增援。
当缪拉的副官骑马飞奔而来,保证说如果陛下再给他们一个师,肯定能击溃俄国人时,拿破仑正坐在山岗下喝藩趣酒。
“增援?”拿破仑吃惊又严厉地问,他好像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望着眼前这个还像孩子一样留着长长的黑色卷发的英俊副官(缪拉也留这种发型)。“增援?”拿破仑想:“一半的军队都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去的地方只是一个很弱的、没有防御工事的俄军侧翼,还要什么增援?”
“告诉那不勒斯王,”拿破仑严肃地说:“现在还不到中午,我还没看清棋盘上的态势。去吧778……”
778原文系法文。
留着长发的英俊小副官一直没把敬礼的手从帽檐上放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又跑回到厮杀的地方。
拿破仑站起来,把科兰库尔和贝尔蒂埃叫到跟前,同他们谈起了与打仗无关的事。
在刚刚开始让拿破仑感兴趣的谈话中间,贝尔蒂埃注意到一名将军骑着汙流夹背的马,带着一名随员朝山岗跑来。这是贝利亚尔。他下了马,快步走到皇帝跟前,开始大胆地、声音洪亮地陈述派援兵的必要性。他发誓说,如果皇帝再给他一个师,俄国人肯定会完蛋。
拿破仑耸了耸肩,什么也没说,继续走来走去。贝利亚尔高声、激动地与围着他的侍从将军们交谈起来。
“您太冲动了,贝利亚尔,”拿破仑说着,又走到了刚来的将军跟前,“在情绪激动时容易犯错误。您再去看看,然后来见我。”
贝利亚尔还没从视线中消失,另一个方向又有新派的人从战场上奔驰而来。
“又有什么事779?”拿破仑因不断受到干扰而有些生气。
779原文系法文。
“陛下,公爵他780……”副官开始说。
780原文系法文。
“请求增援吗?”拿破仑做了个生气的手势说。副官肯定地点下了头,开始报告,但皇帝转过身去,走了两步,停下了,又走回去,把贝尔蒂埃叫到跟前。“应该让后备队上了,”他说道,稍微摊开双手。“您认为,该派谁去?”他问贝尔蒂埃,后来他一直称他为被我变成雄鹰的雏鹅781。
781原文系法文。
“陛下,派克拉帕雷德师去如何?”贝尔蒂埃说,他对所有的师、团和营都耳熟能详。
拿破仑点了点头。
副官骑马向克拉帕雷德师跑去。几分钟后,位于山岗后面的这个年轻的近卫军出发了。拿破仑默默地看着这个方向。
“不,”他突然对贝尔蒂埃说,“我不能派克拉帕雷德去。还是派弗里昂的师吧,”他说。
尽管弗里昂的师并不比克拉帕雷德的师有什么优势,而且现在让克拉帕雷德停下来,再派弗里昂更麻烦,还要耽误时间,但命令还是准确无误地执行了。拿破仑没看出来,在对待自己的部队上他也扮演了一次用药物妨碍康复的医生的角色,这个角色他曾经那么正确地理解并批评过。
弗里昂的师像其它部队一样,消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不见了。副官们不断从各个方向跑来,就像商量好的一样汇报着同样的内容。大家都要增援,都说俄国人还在原地未动,火力非常猛烈782,法国军队上去后就像化掉了一样不见了。
782原文系法文。
拿破仑坐在折椅上沉思起来。
那个喜欢旅行的德·波塞先生783从早晨还没吃东西,一直饿着肚子,他斗胆走到皇帝面前,恭恭敬敬地请陛下进些早餐。
783原文系法文。
“我希望现在就可以祝贺陛下胜利了,”他说。
拿破仑默默地摇了摇头。德·波塞先生认为这个否定是针对胜利的,而不是针对吃早餐的,他大胆地半开玩笑半恭敬地说,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理由影响吃饭,假如有饭吃的话。
“滚开784……”拿破仑突然沉着脸说道,转过身去。波塞的脸上现出一种又是遗憾,又是懊悔又是高兴的怡然自得的微笑,他悄悄地向其他将军们走去。
784原文系法文。
拿破仑此刻心情沮丧,就像一个一直走运的赌徒,疯狂地下注,却总是赢钱,但当他周密地考虑赌局的时候,感到考虑得越是周到,却输得越惨。
部队还是原来的部队,将军还是原来的将军,准备还是那样准备,部署还是那样部署,告示也是同样的短小精悍785,而他也是原来的拿破仑,他知道,他现在比以前更有经验,更老练,甚至敌人也还是原来在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战役与他交过手的敌人,但使足劲挥起的胳膊却像见了鬼似的软绵绵地落了下来。
785原文系法文。
打法还是以前那样战无不胜的打法:把炮兵集中于一点,用后备部队突破敌人的前线,铁786骑兵冲锋,所有这些办法都已用上了,不但没取得胜利,而且传来的消息都是将军们伤亡,必须派援兵,无法击退俄国人以及自己部队溃乱的消息。
786原文系法文。
从前,只要发出两、三道命令,说两、三句话,元帅和副官们就满面笑容地跑来祝贺,报告战利品,成兵团的俘虏,成捆的军旗和队旗787,还有大炮和辎重,缪拉只是向他请求允许骑兵去收集辎重车辆。在洛迪、马伦戈、阿尔科拉、耶拿、奥斯特利茨、瓦格拉木788这些地方都是如此。现在他的部队不知出了什么怪事。
787原文系法文。
788在1796年5月10日的洛迪(意大利北部)战役中,拿破仑把奥地利一万人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在第二次远征意大利时,他在1800年6月14日的马伦戈战役中又击溃奥地利部队。1809年7月5-6日瓦格拉木战役的胜利结束了拿破仑与奥地利的战争。
尽管得到拿下尖顶堡的消息,但拿破仑看到这与以往所打过的仗是不同的,完全不同。他看到,他现在体验的这种情绪,他周围有战斗经验的人也同样体验到了。所有人的脸色都很沮丧,所有的目光都相互躲避。只有波塞一个人不明白所发生事件的意义。拿破仑有长期的作战经验,他很清楚历时八个小时,使用了全部力量还没赢得进攻战,这意味着什么。他知道,战斗失败几乎已成定局了,现在仍然进行战斗的地方,在那胜负未定的紧要关头,稍一疏忽就会导致他和他的部队覆没。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整个这次奇怪的俄国远征,在这次远征中他们没赢过一场战斗,两个月内没夺得一面军旗,一门大炮,一个兵团的部队。他看着周围人脸上隐隐露出的沮丧表情,听着俄国军队仍在坚守阵地的报告,一种恶梦中体验过的可怕的感觉缠绕住了他,他想到了所有会让他毁灭的不详的意外情形。俄国人可能会进攻他的左翼,可能会突破他的中央,流弹可能把他打死。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在以前的战役中他只设想成功的情形,现在无数不详的意外情形他都想到了,他也准备接受它们。是的,这真像在梦中一样,看到一个歹徒向他进攻,他在梦中会抡起拳头用力地打这个歹徒,他知道用这种劲应该把它打死,可他的手却是无力的,软绵绵的像一块抹布一样落下来。于是不可避免的毁灭的恐惧感笼罩了这个无助的人的心头。
俄国人进攻法军左翼的消息让拿破仑产生了这种恐惧。他默默地坐在山岗下面的折椅上,低着头,两个胳膊肘拄着膝盖。贝尔蒂埃走到他跟前,建议他去前线走走以便弄清情况到底怎样。
“什么?您说什么?”拿破仑说。“好吧,让他们把马给我牵来。”
他骑上马朝谢苗诺夫村走去。
拿破仑所走过的阵地上,硝烟正渐渐散去,人和马躺在血泊中,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一堆一堆的。不论是拿破仑还是他的将军们,谁都没见过这样的恐怖景象,在这样小的地方死亡数量如此之大。连续十个小时不间断的、让双耳饱受折磨的大炮轰鸣声又给这种景象增添了一些特殊的感染力(犹如给这种栩栩如生的图画配上的音乐)。拿破仑登上谢苗诺夫高地,透过烟雾看着一排排穿着陌生颜色军服的人。那是俄国兵。
俄国兵排着密集的队形站在谢苗诺夫村和山岗后面,他们的大炮不住地发着轰鸣声,前线硝烟弥漫。交战已停止了,只是厮杀还在继续,这不论是对俄国人,还是对法国人都没有任何意义。拿破仑让马停下,又陷入了贝尔蒂埃曾把他打断的沉思中;他已无力阻止在他面前和周围发生的事,这件事他原以为是由他领导并取决于他的,由于没有成功,他第一次觉得这件事是那么不必要,那么可怕。
一个将军来到拿破仑面前,恳请他派老近卫军参战。站在拿破仑旁边的内伊和贝尔蒂埃交换了一下眼色,对这个将军毫无意义的提议露出了轻蔑的微笑。
拿破仑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在距法国三千二百俄里远的地方,我不能让自己的近卫军去送死789。”他说着,调转马头返回舍瓦尔金诺去了。
789原文系法文。
三十五
库图佐夫垂下花白的头,肥胖的身体完全放松地坐在铺着地毯的长凳上,还是在早晨皮埃尔看见他的地方。他不下任何命令,只是对别人的提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
“好的,好的,就这样办吧。”他对各种各样的提议都这样回答。“对,对,亲爱的,去看看吧,”他一会对这个,一会对那个向他跑来的人说,或者说“不,不用,还是等等吧”。他听取送来的报告,当下属需要指示时也下达命令;但他听报告时好像对跟他说的那些话所包含的意义并不感兴趣,让他感兴趣的只是报告人的面部表情和语调中的某些东西。凭多年的军事经验他知道,凭老年人的睿智他明白,统帅几十万与死神搏斗的大军靠一个人是不行的,他也知道,决定战役胜败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也不是部队所处的位置,更不是大炮和死亡人数的多少,而是那种难以察觉的,所谓的军队的士气。他时刻关注着这股力量,尽最大的能力去控制这种力量。
库图佐夫脸上的表情总的说来是聚精会神、镇静安详和勉强控制衰老的身体时时袭来的疲惫而感到的紧张。
上午十一点钟,给他送来消息说,法国人占领的尖顶堡又被夺回来了,但巴格拉季翁公爵负了伤。库图佐夫哎哟一声,摇了摇头。
“到伊万·彼得罗维奇790公爵那里去看看,详细了解一下,怎样负伤的,伤势如何。”他对一个副官说,然后对站在他身后的符腾堡公爵791说:
790伊万·彼得罗维奇是巴格拉季翁的名和父称。
791符腾堡公爵(1771-1833)是俄国皇太后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弟弟,当时是库图佐夫的侍卫官。
“殿下,您是否去接替第一军的指挥?”
亲王走后不久,甚至他还没到达谢苗诺夫村,他的副官就回来向总司令报告说,殿下请求派援兵。
库图佐夫皱了下眉头,一面派人给多赫图罗夫下达指挥第一军的命令,一面让亲王赶快回到他身边,说在这紧要关头他身边没有亲王是不行的。当传来缪拉被俘的消息792,参谋们都向库图佐夫祝贺时,他笑了一下。
792这个消息是不确切的,当时被俘的是波纳米将军,当时他看到俄国兵的刺刀抵在他胸口,就喊:“我是国王!”,他被送到库图佐夫那里。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引用的是拉达日茨基的《炮兵远征记》(1835年出版),书中说,这个假消息是叶列茨基团的一个口齿不清的少校发出的,他骑马沿前线奔跑,兴高采烈地大喊:“兄弟们,缪拉被俘啦!”
“等一等,先生们,”他说:“战斗胜利了,俘虏缪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最好还是等一会再高兴。”但他还是派副官把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