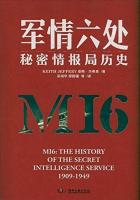何明光搬来几条凳子让大家坐下。婆娘也提了把瓦壶从灶间走了出来,给每人面前冲上一碗热茶。
热气就在众人面前升腾着,屋子里也变温暖了许多。
周大兴一边喝茶,一边问:“大家日子还过得好吗?”
二叔就说:“指挥长,我们知道你也是县长,大家就也都来了。”
“大家是来找我有事吗?”
二叔说:“县长,您不是问我们日子还过得好吗?这话还真不好说。说不好吧,大家还算有口饭吃,没有饿着就是。说好吧,可大家日子也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是吗?你们乡上年年汇报不是说村民的生活水平每年都提高了好几个百分点吗?”
“我们正要向您反映这事,”二叔又说,“书记、乡长像走马灯似的,要不了几年就换届,他们来了就只顾着抓政绩,谁还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呢?就说上届来了个鲁书记,就是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要求村民都种黄花菜,村上三天两头来督促,谁还敢不种?那就种吧。”
“结果怎样呢?”
“结果黄花菜卖不出去,只能放在地里烂。好些人家还晒成干草当柴烧。他可好,成了农村发展经济的典型,屁股一拍走人了,赔钱的就只能是我们老百姓了。”
一个瘦高个的村民接过话说:“这届来了个杨书记,说叫我们种花木,要办成花木村。我们对这热情也不高,不相信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村里看任务派不下去,最后就强行搞摊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务。”
周大兴一阵默然,说不出话来。
他心里清楚,现在官员们中都流行着“政绩”一词,为了“政绩”,官员们要千方百计地想出种种花样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以图升迁。说白了,就是上上下下自欺欺人,共同在做一个“画饼充饥”的无聊游戏。这种用搞“花架子”的手法“树自己的形象”邀功请赏的事,并非现在才有,只是很少有人下来了解民情,才会导致许许多多的问题产生。他记起一本史书上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北宋初年,赵匡胤是个不甘寂寞的皇帝,他常常偷偷跑出皇宫,去访问民情。然而,毕竟不能时时出宫。登闻二院便成了他了解下情的一条重要渠道。
有一天,东京市井间的一位市民,丢失了一头猪,他投诉无门,便跑到登闻鼓院敲起大鼓来。鼓院的官人们不敢怠慢,立即报告了皇帝。赵匡胤听说有一位市民要皇帝帮他寻找丢失的猪,竟然十分高兴。他写了一个手诏给亲近大臣说:“今天居然有人来敲登闻鼓向朕投诉,寻觅走失的猪。朕又何尝看到他的猪哩!然而,通过这件事可以知道,天下再也没有冤民了,这是应该与卿共同感到欣慰的事。”
赵匡胤这个判断,显然过于乐观,在封建统治之下,哪里会没有冤民?不过,市民丢了猪竟然可以向皇帝投诉,这倒是前朝所无,后代难见的喜剧性新闻。它说明北宋初年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这正是当时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官员就不能去了解民情民意,却热衷于自己的“政绩”与“形象”呢?
大家见他没说话,也就停住了没说,便低着头只管去喝茶。
他大概发现了气氛不对,便冲大家笑了笑,说:“怎么不说了?刚才不是说得挺好的嘛!大家心里想着什么就说什么,今天我来,就是来听取大家的意见的。”
二叔就又说:“县长,我们老百姓也没什么大的要求,只希望你们上面能派一个能体谅我们老百姓的好官下来,能让我们安生过日子就行了。”
“怎么能这样胡作乱搞呢?太不像话了!”周大兴便有些气愤起来。从他进村那一刻起,就感到了一种责任。他的根在乡村,他在乡村生活过,成长过,有过要为老百姓办一点实事的美好愿望,听了他们的话,他便深深地感到内疚,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他说:“我也有责任,偏听偏信没有下来调查了解,这种不正之风,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你们的意见,我会带到县长会议上去,会如实的向县委汇报。”
他这一说,大家一下变融洽了许多,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拘谨,有个村民甚至还把双脚蹲到了凳子上。二叔从腰上解下那杆水烟筒,捻满一锅黄烟末递给他,硬要他尝一锅试试。
他便接过水烟筒叭上,很惬意的叭得噗噜噜地响。
大家就都嘿儿嘿儿地笑。
二叔忽然问:“县长,听说你们那个采石场的石头不行,是真的吗?”
“是啊!”他叹了口气说:“那石里有泥土,不能用。”
“那怎么办呢?”
“我也正为这事发愁,”他看了他们一眼,又说:“石料供不上,拖住了工程的进度,秋汛一到,大坝就没法建了。”
“能有办法吗?”
“但要开辟一个新的石料场,要重新勘探,要添加资金,要命的是拖住了时间,困难大着呐!”
大家就都不再说话,像都在想着法子。
忽然,二叔一拍脑袋说:“有了!”
周大兴就惊疑地看着他:“什么有了?”
二叔起身打开后墙上那扇窗子,往外一指说:“看到了吗,这石料够好的吧?”
周大兴就也起身过去看,只见村后是一道嶙峋壁立的石崖,似斧削一般拔地而起。崖上有开采过的痕迹,露出灰白色的层面。
二叔说,“我们先前盖房子,就是从这里取的石头,全是上好的石灰石。”
周大兴说:“不行,这里采石,一爆破会伤人的。”
二叔说:“我们即刻就搬,住到临时工棚里去,反正我们这些屋子全都要拆迁。”
周大兴感到很意外,没想到问题会解决得这么快,便说:“这就谢谢你们了。不过一定得先把大家安顿好,我去县上,要他们先送些帐棚过来。”
“不用说谢,”二叔说,说得很诚恳,“政府修这电站,是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实话说,这些我们老百姓都懂,也都赞同,要不是你们那两个干部乱搞,也不会闹成这么僵的。”
周大兴就用力握住他们一个个的手,还使劲的摇了摇,以表示他的内疚,也表示他的感激。
夏天的雨水容易降落,也很容易收场。不远处的河水,就有着喧扰和开阔的声响。山石和树枝也被雨水洗净了,从山石和树叶上不断地滴下透明的水珠。空气里没有了半点灰尘,如同掺了薄荷一般透心的爽快极了。
大家就一个个起身走出屋来。
二叔还对他说:“县长,下次进村来,一定要上我家来喝口茶啊!”
他便说:“一定来,一定来,还有好些事会要来麻烦您哩!”
“说不上麻烦,呵呵!”众人就沿着山路,踩着泥水“吧叽吧叽”地走了。
他这才回转身来,同着李小刚往指挥部走去。
李小刚一边走,一边深有感触地说:“这些老百姓真好。先前我还总认为乡下人蛮不讲理,现在看来,往往不讲道理的还是我们干部。”
“一千多年前的唐大宗就曾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盘’,这水,说的就是我们的农民。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历朝历代没人不知道农民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干部,也必须正确地看待农民。”他说,心里像压着一个秤砣,沉甸甸的。
“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必须要整治整活了,”李小刚说“不知你听过没有,现在社会上编排我们官员们的民谣很多。”
“都有些什么?你说说看。”
“多啦!比如说: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睡,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累,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有些人也确实如此,这样的人还会去关心群众,去为群众干事吗?”
“是啊!”他也很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总是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看,这观念是非改不可了,最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他说着,深吸了一口空中浮满了草木的香气,通身显得清澈了许多,心里便想要好好地唱出一些什么来。
四十
指挥部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做食堂的工棚内,一个个脸上都表情严肃,气氛显得紧张。
这是指挥部的全体干部会议,并且还邀请了几位村民代表参加。
周大兴这会正在主席台上发言,脸色显得十分严竣,他眼光或仰视或平视都显出威严得令人畏惧的神态。他说:“我们的干部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因为是人民养育了我们。想想啊,我们吃的、用的,还有我们每月花的工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人民群众,我们有什么权利不去服好务,有什么权利要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
他说话时,脸块便涨红了,青筋突起,并以右拳击着左手掌,身子微微的向前倾。
他继续说:“有的人就偏偏要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那么一点儿权力,便胡作非为,向群众要吃要喝,收受红包,这还像一名党的干部吗?根据村民的反映,我们指挥部负责征收土地、房屋拆迁的干部刘子青和张建阳在山下村的行为就极为恶劣,影响极坏。这是一种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我已通知检察机关前来把人带走,希望他们俩人能在检察部门能够好好地交待自己的问题,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
全场很静,没有一人作声,连咳嗽声也没有。
他又说,而且放缓声调,一字一句咬得十分清晰:“我们都是党的干部,要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诚心诚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要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不然,这和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又有什么两样?我以为,我们党的干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区别,最重要的便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不同。因此,我希望大家都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每人都在静听着他的讲话,当他讲完之后,静场了片刻,接着便报以十分热烈的掌声。
吃过晚饭,他回到宿舍刚坐下,电话铃就又响了。是何伟光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周县长,刘子青和张建阳也做的太不像话,他们一个是我小舅子,一个是我姨夫,刚才我在电话里把他们俩个狠狠地骂了一顿。您看是不是这样,念在他们年轻,又是初犯,处罚时就别太重,好吗?”
周大兴便回说:“老何,他们做的这事的确是比较恶劣。”
“那是,那是,我也是这么说他们的。”
“能不能从轻处理,这就要看他们自己能不能把问题交待清楚。这样吧,老何,你也做做他们的工作。”
“好好,工作我一定会做的。”
刚放下话筒,又有人打来电话,对方竟然是老书记何求。
电话里传出何求的声音:“喂,是小周吗?这向可是辛苦了啊!”
他便忙说:“不辛苦。何书记,您还好吗?”
“好,好,”何求说,“小周啊,那两个年轻人要批评,可别处理过重,年轻人嘛,重在教育,我们党的政策历来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
“何书记,请您放心,我会按政策办的。”
“这就好,这就好。小周啊,好好干吧!”何求的话就变得很温馨。
放下话筒,周大兴就沉默着,抓起桌上的一缸子茶咕嘟咕嘟地往口里倒了一大口。
一会,李小刚跑了进来说:“周县长,市委办的鲁主任打来电话,希望您能对他们俩人从轻处理。”
周大兴皱着眉说:“知道了,我这里已有几个来说情。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就没有人替老百姓说说话呢?哪怕是说一句话,也没有啊!”话里充满了愤怒,更有几分悲怆。
“那这事怎么办?”李小刚问
“小刚,你还记得花鼓戏《七品芝麻官》里的徐九斤说的一句话么?”他忽然这么问。
“记得,他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去卖蕃薯’。”
周大兴便觉得血直涌到脸上,心口里怦怦地撞起来,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要讲党性,作为一个人要讲良心,无论是党性还是良心,都要求我不能黑白不分,人要处理,我会要求检察部门依法办事,就是撤职回去卖蕃薯也要这么办!”说罢便站到窗前,一动不动,像是在静静地休息。其实,他心里有无法抑制的怒火在腾腾燃起,脸色铁青,脸上的肌肉在跳动。他心里还有话没有说出来,他在心里说:“农民的利益问题得不到解决,还能谈什么教育农民?干部的作风不改变,不去关心群众,不去为他们解决问题,还能谈什么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呢?”他忽然觉得有种叫人喘不过气来的烦躁,一种推不开、甩不脱的郁闷,心里像堵了块石头,就像河水被枯枝败叶和杂草垃圾堵住了去路,一时间流不动了。
李小刚便不出声响地看着他,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眼睛里游动,很涩,也很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