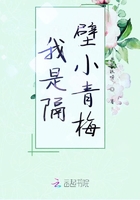荞荞在床上坐了一夜。天亮后,那个女人走了。马豁子没有送女人。
荞荞咬着牙狠拍自己的腿,就算长在了床上,她也要拽出来。荞荞铁了心,半夜里她就拿定了主意。离三个月的时间只剩最后两天了,马豁子总不至于强迫她再干两天吧。
荞荞先捡了钥匙,然后拍马豁子的屋门。半天没应答,荞荞顿了顿,固执地拍下去。
没长手?马豁子的声音恶狠狠的。
荞荞推开门,浓烟呼地扑出来,几乎燎着荞荞。荞荞以为着了火,一看,蓝烟是从马豁子嘴里跑出来的。满地烟头和碎玻璃,荞荞都没处下脚了。马豁子还没起床,他歪在被窝里,只伸出一颗乱蓬蓬的头。看见荞荞,马豁子有些不好意思,一向怕羞的荞荞却没觉得什么,她把准备好的帐目及剩余的钱搁在桌子上。
马豁子愕然地问,怎么了?
荞荞说,我不想干了。荞荞不看马豁子,用脚捻着无处不在的烟头,仿佛这一切全是烟头惹出来的。
马豁子呼地坐起来,怎么了?……你听到了?荞荞,跟你没关系。
荞荞说,我啥也没听到,我就是不想干了,那三千块钱,我会还的。
马豁子的嗓音更哑了,荞荞,你怎么这么糊涂?
荞荞转身就走。她没糊涂,糊涂的是他。
你站住!马豁子喝道。
荞荞抽搐了一下,慢慢转过身。马豁子的眼睛透着苍老的红,一触即枯。他的声音却鲜得淌水,还不到三个月呢。
荞荞说,只剩两天了。
马豁子说,再干两天,三个月,一天也不能少。
马豁子凶狠的表情触怒了荞荞,荞荞很少动怒,可这阵儿,她突然控制不住了,嚷,那你就告杨来喜吧,摔门出来。
昨天晚上,女人一来,荞荞就想躲走,那个尴尬的夜晚还在她脑里长着呢。可没等荞荞收拾好,女人和马豁子已吵得不可开交。激烈的争吵声传过来,荞荞的心就乒乒乓乓地跳。起先,两人的争吵是绞在一起的,听不清吵什么,争吵的内容被粘粘稠稠的声音淹没。荞荞不想听下去,刚迈出门,两人的声音分开了。原来女人在说她,荞荞不由哆嗦了一下。
女人叫,你哄谁?那个破女人天天住在这儿,还说没鬼?
马豁子说,闭上你的臭嘴。
女人说,嫌我臭了,是不是她香?
马豁子骂,日你妈,你倒会咬。
女人连珠炮似地嚷,我就咬,我就咬,你心疼了?
妈的,我叫你咬。掴耳光的声音。
女人骂,好啊,你打我!
两人干了起来,叮叽当啷的,不知踢翻了什么,打碎了什么。
荞荞的心被扎满了窟窿,听到撕打声,荞荞想跑过去,却怎么也抬不起腿。
屋内突然静下来。荞荞怔在那儿。片刻的死寂之后,马豁子骂了声我操,女人气咻咻说,你滚开。马豁子叫,你现在还是老子的女人。女人骂不要脸,可她的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马豁子说,我操!我操!女人骂,你个儿马,你个驴!马豁子说,你不就要这个吗?女人不骂了,夸张地叫起来。哎哟,疼死我了……
冬日的寒气卷住了荞荞,荞荞的脸热得烫手。
声音终止下来后,马豁子长长地叹口气。
女人说,满意了?
马豁子说,还是离了吧。
女人说,谁也甭计较谁。
马豁子说,不,我要离。
女人冷笑,你早盘算好了吧?
马豁子说,随你怎么说吧,反正我不想过了。
女人说,离可以,给我二十万块钱。
马豁子的声音粗了,你把我的骨头榨了吧。
女人说,没二十万,想离,没门儿。
荞荞怎么也没想到两人的吵打竟然与她有关,更没想到两人闹到离婚的地步。荞荞一直低眉顺眼,还是招惹了大麻烦。当初,她就不该住这儿,可当初由得了她吗?就是那一刻,荞荞决定离开,天一亮就走。
荞荞的步子迈得很快,冬日的寒风被荞荞踩得嚓嚓响。半路上,马豁子追上来。马豁子气喘吁吁地说,荞荞,你听我说。荞荞不听,几乎是小跑了。马豁子拦在荞荞面前。荞荞骂,你无赖。马豁子不说话,墙一样堵着荞荞。荞荞怕人看见,下意识地望望四周。马豁子看出来了,故意大声说,我就不让你走。荞荞想狠狠骂一句,把马豁子的脸骂破,可搜肠刮肚,没找出一句解恨的话。荞荞被抽了筋似的,软软地坐到地上,伤心得哭起来。
马豁子蹲下来,你别多心,真和你没关系。
荞荞抹抹泪,放了我吧,马老板,有关系没关系我都不想干了。
马豁子叹口气,你是逼着我说实话。我离婚,是……我没想到她会背着我干那种事,若不是撞个正着,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荞荞的脸僵住了,马豁子在寒冷中揭开了伤口,脸上却平静如水。
竟然是这样。
马豁子的背影消逝后,荞荞继续朝围子里走去。没人追她,荞荞用不着那么快了。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她想弄清楚一件事,可脑子里乱糟糟的。直到村长喊她,她才醒过来。村长说,荞荞,想什么心事呢。村长的目光粘在身上,荞荞甩了几下,没甩脱。村长并不在意荞荞的态度,他跟在荞荞身后,甜腻腻地说,荞荞,你可出大名了,和你商量件事,咱村妇联主任缺个助手,我想让你来干,平时没啥大事,有事你就来,没事该干啥干啥,年底一样发补助。荞荞的步子加快了。村长说,噢,你等等,这是好事,你考虑考虑。荞荞不知这是咋了,“好事”突然没头没脑地往她身上扑。薛书记让她当广播员,村长让她当妇联助手。荞荞想起那张存折,她的心针扎似地疼起来。村长说,荞荞,村里也有事求你。荞荞纳闷,她能干什么事?村长说,镇里弄回一批扩音器,你和薛书记说一说,给咱村弄一台。原来是这样,荞荞猛地甩回头,霎白着脸说,你寒碜死了!村长猝防不住,吃了屎一样愣在那儿。
荞荞被冰冻住了,寒气刀子一样捅着她。荞荞回到家,点着炉火,开始清扫屋子,烧炕。荞荞的背上伏着一层汗,可她还是感到冷。冷气是从心里透出来的,她阻挡不住。荞荞后悔只骂了村长一句,那个狗杂种,骂出他的肠肠肚肚都不冤。
荞荞又冷又累,她双手抱着膀子,想躺下窝一会儿。门外传来二香的声音,走到哪儿,干净了哪儿,怪不得招人喜欢。荞荞吃了一惊,没等她撩开身上的被子,二香已进来了。二香怪腔怪调地哟了一声,看不出来,你还这么娇气?荞荞忙叫了声姐。二香说,行啦,你躺着吧。二香肯定是为薛书记来的,荞荞不知怎么办,她惹不起二香。果然,二香虚晃了几枪,单刀直入地问,听说老薛还找你。荞荞急忙否认。二香盯着荞荞,做出推心置腹的样子,说,其实我不是和你争,我上了当,不想让你再上了,别看他装腔作势的,其实不是正经东西,我和他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能从他的嗓眼儿看到他的屁眼儿,知道他有几根肠子。二香说得赤裸裸的,荞荞快要吐出来了。也许是荞荞“表现”较好,二香没有寻根究底,荞荞暗暗松了口气。二香又问荞荞别的女人缠薛书记没有。荞荞摇头道,不知道。二香说,你在镇上,听的事到底多一些,有哪个女人不知趣,你告诉我,我非撕烂她。荞荞听出二香在警告她。二香以为别的女人都和她一样,抱个牛粪块当金元宝。荞荞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村长和二香这么一搅合,荞荞本来就极糟的心情,现在收拾都收拾不起来了。不过,这一来倒让荞荞更加清醒了,她必须躲薛书记远点儿。她的麻烦够多了,不能再往浑水坑里掉了。
第二天,荞荞早早地醒来。往天这个时候,她正给马豁子准备早饭。荞荞躺不住了,可出门时又迟疑起来。她从大门口到屋子,从屋子到大门口走了七八个来回,最后才下了决心。
马豁子看见荞荞,说,看来我不用吃方便面了。荞荞不理他,把屋子打扫干净。吃饭时,马豁子显得很客气,就像荞荞刚来时一样。马豁子显然怕伤害了荞荞,他的好意让荞荞难过。荞荞沉默着,马豁子很随意地说,薛书记来找过你。荞荞的体内有什么东西崩断了,她弓了一下腰,没吱声。马豁子问,还要作报告?荞荞摇摇头,她本来想跟马豁子说的,现在改了主意。
杨来喜是吃晚饭的时候来的,没等马豁子让就大模大样地坐在餐桌旁。马豁子要买酒,荞荞用眼神制止了。杨来喜边吃边嘲弄马豁子的饭是喂长工的,一盘菜连个肉星子都找不见。杨来喜的嘴皮子比过去更损了。马豁子只是浅笑着,荞荞看出笑后面含着轻蔑。杨来喜觉不出来,依然胡说八道。荞荞劝他少说废话,杨来喜眉毛一挑,碍你什么事了?荞荞不敢和他争吵,怕杨来喜趁机闹事。杨来喜见两人都不和他说话,就问马豁子,今儿够不够三个月?荞荞吃了一惊,杨来喜竟记得一天不差。马豁子笑着说,你好记性。杨来喜说,少寒碜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丧什么辱国?马豁子说,丧权辱国。杨来喜说,我他妈丧权辱国三个月。
杨来喜让荞荞马上跟他回家。荞荞平静地说,那三千块钱,你挣够了?杨来喜咦了一声,看样子,你不想回去?荞荞反问,凭什么?杨来喜说,我是你男人。荞荞气哼哼地说,男人哪有你这样的?杨来喜抻抻脖子,说,荞荞,我这次回来准备干一桩大买卖,三千块钱算啥?不出一年,我要把马豁子的收购站买下来……荞荞打断说,少说废话,你先把钱还了。杨来喜骂声操,猛然扬起手……杨来喜怔住了,他的手僵在半空,他从荞荞的脸上看到了执着,看到了轻蔑,那意思很明显,就是打死她她也不回去。
杨来喜垂下手,他抱住荞荞,身子朝地上坠去。杨来喜说,跟我回吧,哪怕就一天呢。竟然哽哽咽咽地哭起来。
荞荞绷紧的身子被杨来喜泡得面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