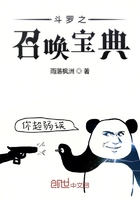长路漫浩浩
《元宁实录•顺宗卷》
崇明九年八月初七,大军越清支山口。
崇明九年八月十三,大军克罗显,擒乱首。
崇明九年八月十五,苏达扎呈奉请表。
格桑高原是地广人稀的地域,所以,康焓接到永宁王“安!进!”的密信后,根本没有分兵去占领各个城池,而全军直逼罗显。罗显城不仅是格桑高原的中心,更是康人的圣地,攻克罗显,让苏达扎臣服,康人也就臣服了。
康焓以大将军的半幅天子旌旗收下了苏达扎的奉请表,自圣清皇朝德宗二十六年,格拉桑尔郡王阿克烈反叛,至略失去格桑高原的统治权五百余年后,元宁皇朝重新让康人称臣。
对于这一切,成佑皇帝比阳玄颢早四天知道,但是,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康焓以前所未有的犀利指挥用兵,永宁王用严阵以待的北疆大军防范他的任何行动。至略的庞大在这个时候便是莫大的优势,永宁王可以用人海封锁每一处关隘,监视古曼人的一举一动,并作出实质的威胁。成佑皇帝不得不考虑取舍。
直到这个时候,成佑皇帝才再次想起,应该见一见那个一点都不着急的齐朗。
齐朗也正等着成佑皇帝的决定,他不担心对方要杀自己,但是,若是古曼强行扣留他,也不会是太过份的事情,因此,当陪同的古曼大臣转告他,成佑皇帝宣召他时,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实在暗暗松了一口气。
“景瀚这些天很悠闲快活吧?十部的景致,你似乎都游遍了吧?”成佑皇帝依旧以爽朗的笑语招呼齐朗,齐朗也笑道:“古曼的风物自成一格,别有趣味,此前都未能细赏,这次总算如愿了!”
双方都在话中留了三分余地,十分克制,因此,谈话的气氛一直保持在平和的水准。
格桑高原绝非必争之地,又只是对古曼称臣,对于成佑皇帝远谈不上至关重要,最初的暴怒更多的是针对齐朗如此设计他而产生的情绪,搁置几天,再思考这个问题,成佑皇帝对于取舍很快就有了决定。
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中,成佑皇帝已经知道至略人对所谓的全境旧土是何概念,而至略人对之近于狂热的追求更是令他迷惑,吕真告诉他:“至略曾经的强盛对于所有的至略人都如同一个最美好的梦。因为那梦曾经以最明确的方式真实存在,因此,梦也就成了理想!沉浸其中最不可自拔的便是元宁的天子!为了那个梦一般的理想,阳家人可以仁泽天下,也可以冷酷残忍,之于他们的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于任何的感情,都不可以妨碍这个梦的实现!”
如果紫苏听到这番话一定会惊讶,因为,吕真的说辞是那样熟悉,在夏氏的秘记中,在最初的最初,夏汐澜会选择支持阳渊昊,便是因为,那个男子背对满天的晚霞,看着城墙边蜷缩的难民,很认真地说:“我想结束这个乱世。我们至略人不应如此凄惨地生活,我心中的至略应该是像圣清皇朝那样的强大帝国,足以保护她的子民平安和乐地生活,如果能够做到,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这位元宁的太祖皇帝后来又说过:“如果不能光复至略全境,谈什么强大……”
也许敌人的确是最了解你的人!吕真对至略、对阳氏的看法正确无误;齐朗对成佑皇帝的认识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虽然那片高原对成佑皇帝算不得必争之地,但是,齐朗很清楚,成佑皇帝也没有轻易让出的打算,他仍然尽一切努力想维护古曼的利益与权威,同时,齐朗更清楚,格桑高原并非他最关切的目标——成佑皇帝的目光始终投向东方。
后世的古曼学者总是惊叹于成佑皇帝超越时代的眼光,在世界还没将眼光投向海洋时,这位皇帝就已经在努力为古曼寻求一个出海口,当然,具有同样目光远非他一人,至少,元宁皇朝就从未停止对海洋的探索,对优良海港同样充满志在必得的兴趣。
齐朗并不清楚成佑皇帝是否想得出海口,但是,成佑皇帝有多么渴望得到一块富饶的土地作为古曼的粮仓,他却是很清楚。
对于成佑皇帝而言,如果用格桑高原可以换到一块产粮的富庶之地,他也不会有任何意见。齐朗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才敢于让康焓急攻罗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成佑皇帝作出让步,以换取更多的主动。
当然,成佑皇帝选中的就是周扬的白河平原,他最期望的元宁可以出兵牵制周扬,但是,现在,实现的可能性太低了。
齐朗的目的实际上已经达成,因此,他根本是咬死了——不可能出兵!元宁的态度是不干涉、不介入、不表态,承认既成事实。
废话!
成佑皇帝心中早已骂开了——只要不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又没有更大利益诱惑,谁都会是这种态度!
典型的“好处顺手捞一些,半点风险不沾手!”
盟友?需要结盟时才是朋友!
其实,古曼也不见得有多高尚,只是,这种主动权不在手的感觉实在不好,成佑皇帝也无法一直保持十分平静的心态。
虽然,有无元宁的牵制,他都能达到目的,但是,能减少一些损失是一些,毕竟,古曼的敌人也不少!
齐朗从不是固执的人,更何况,他本身的安危就是成佑皇帝最大的筹码,在成佑皇帝表示了足够的诚意之后,齐朗作出了让步——为保证元宁自身的安全,一旦战事邻近元宁的边境,元宁会主动确定出足够的缓冲带,以保证边境安全。
古曼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承认格桑高原的归属并撤出所有军队与官员、赠送大批牲畜与矿石以及一笔高价黑煤的定单。——毕竟双方对于开战都有顾忌,且都不是彼此的首要目标
关于古曼陈于边境的重兵,齐朗没有提,倒是成佑皇帝主动说明,只是为下一步行动集结而已。
于是,在永宁王与康焓联名呈上战报的同时,齐朗关于此次和议的奏章也到了御前。这回,阳玄颢没有再犹豫,他在当天即照准了两份奏章。紫苏与谢清都松了一口气,对于皇帝也稍稍恢复了点信心。
也仅仅是稍稍恢复了点信心。
一直以来,紫苏不曾放弃权力,却没有任何控制朝政、控制皇帝的打算与行动,但是,她也无法确定,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她的儿子不缺乏作为皇帝的自觉,却对如何完成皇帝的职责缺少应有的认识,即使他已经学了这么多年!
元宁的历史上,摄政的后妃即使归政也仍然拥有极大的权力,毕竟,权力这种东西并不是谁想拥有就可以握在手中的,可是,拥有权力并不代表可以随心所欲,至少归政之后,在名义上,后妃,哪怕是太后也失去了干涉朝政的正统名义,紫苏也无意冒犯这个规矩。
名不正,言不顺。紫苏不愿谈论朝政的原因正是这一点。
阳玄颢同样无意加强母后对朝政的影响,有意无意间,他自己甚至都在抗拒母后的意见,无论意见的正确与否,紫苏对此几乎是深恶痛绝,她一直希望自己与皇帝的关系如显成太后与德宗般亲密,毕竟,她是皇帝的生母,他们之间无论有多少分歧,至少不应该敌对,但是,很显然,她的儿子此时并不想倾听母亲的话语。
这让紫苏在困惑的同时,也不得不产生糟糕的念头。
其实,阳玄颢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想法?亲政之后,他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但是,他的母亲在十年间的作为太成功了,成功到令他无法摆脱母后的影响。
哪个皇帝不想乾纳独断?亲政前,阳玄颢只是觉得母亲永远在自己背后操纵着一切,亲政后,他却觉得整个朝堂都被慈和宫的影子笼罩着。
他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正确,但是,他并不愿意母后的势力在朝中增强,因此,他极不愿意齐朗回朝。
谢清在朝中的权势虽盛,但是,毕竟,谢家是尚主之家,权势被加了许多限制,齐朗却不同。齐朗的出身、经历、学识都让他拥有了足够的人脉,他本身的性格更让他足以协调多方势力为己用。元宁要求议政首臣有这样的本领,但是,前提是忠诚,虽然有诸多的牵制,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在一定情况下,议政首臣足以将皇帝架空,就如中宗朝的杜英深,权势只手遮天的他甚至可以让中宗无法确立太子,若非中宗临终前忽然宣召杜英深与两位德高望众的老臣,亲口颁谕“皇长子继皇帝位。”德宗未必能成为皇帝。
阳玄颢不想成为中宗,可是,他现在已经感到,他的母后虽然没有做,但是,她完全可以阻止他的任何行动,更可以让他的任何诏命成为一纸空文,终究,他还是太年轻了!他的经历也无法让他如紫苏一般,在年少时便足以独挡一面。
也许,阳玄颢最缺乏的仅仅是自知之明,不仅是作为皇帝,也作为一个普通人!
如果看清这一点,尹韫欢对祖父的担心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了!
尹韫欢并不是担心阳玄颢会将所有的责任推给祖父,阳玄颢从未失过应有的担当,却也正是这点,才让她倍感忧虑,她在祖母入宫探望自己时,面对担忧又关切自己的祖母,几乎泣不成音:“太后娘娘不会允许皇上犯错的!皇上怎么可以犯错呢?”
无论阳玄颢的想法如何,最终,他不可能担负任何罪名,而他越是有担当,越会激怒紫苏,甚至会让紫苏直接处置尹朔,那才是无可挽回的最糟糕的局面!——阳玄颢还不明白,对于一个皇帝,年少永远不能是犯错的理由!
年少的皇帝不可以犯错,尤其是在臣民的心中,皇帝必须永远是对。
阳玄颢的权威还不足以承担错误!——紫苏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否则,不仅是他权威受损,更会使民心不安,国家震荡。
尹韫欢其实也是在赌,若是赌错了,赔上的不仅是她的祖父,还有她自己以及整个尹家。幸运的是她赌对了——紫苏虽然不满,但是,终究没有处置她,她的身孕还是换来了太后的罢手,其它的一切……都可以补救。
只是,尹韫欢不明白,这个世界,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补救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机会只要一次就足够了!
尹朔对此也只能叹息一声:“傻孩子!”他无法过多地关注这个孙女,因为齐朗即将归来。
九月初六,带着完成的和约,齐朗回到成越,同一天,苏达扎关于请求册封教主的奏表也到了成越。
不能不说,康焓对时间的把握十分准确,而谢清在当天晚上为齐朗接风的宴席上,带着三分笑意戏言:“这两年,景瀚与平南大将军的关系不错啊!”
声音极小,别人听不到,只当两个好友在说笑话,齐朗也只是轻笑,甚至还放下了手中的酒樽,他同样轻声地回答:“康大将军是个很聪明也很随和的人!”
谢清为之莞尔:“与你很像!”齐朗微笑不语。
那个晚上,两个人的三言两语,谢清便确定了齐朗对格桑高原一定还有安排,但是,直到三天之后,谢清才有机会与齐朗深谈这个话题。
齐朗很随和,但是,他同样有自己的人脉势力要维护,更何况,丁忧以来,他手下的人其实是最受排挤的,谢清能给予的照顾始终有限,而且,谢清自己也有必须首先维护的人,这些人是真正失去了庇护,现在,齐朗回来了,虽然很多事情不是一次见面就能解决的,但是,让那些人直观地明白他们从未被抛弃却是必要的!所以,齐朗很忙。
无论齐朗一系的人多么想了解他对以后的打算,当夏茵带着女儿到达成越这一天,所有人都不敢再上门询问,但是,永宁王府与谢府却再一次从容登门了。
永宁王妃带了丰厚的礼物,大部分是给年幼的书莞的,这个时候,书莞的孝服已满,永宁王妃这一次正式询问齐家是否可以行定聘之礼,夏茵欲言又止,齐朗只能苦笑:“王妃娘娘,现在谁不知道我这个女儿是永宁王府未来的世子妃,您就这么着急?非得在我孝服未满的时候,让齐府行吉礼?”
永宁王妃一边哄着书莞,一边不在意地回答:“我只是这么问一下,你给个日子就可以了,也不算为难你,你何必这样说呢?”
齐朗还能怎么说?倒是倩仪在一旁与堂妹好好说笑了一通,谢清只是好笑地看着这一幕,却是半个字都不说。
书莞显然困了,不一会儿就哭闹起来,夏茵带着女儿离开,几个好友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品了几口香茗,相互看了几眼,谢清抿抿唇,不甚在意地问齐朗:“景瀚有计划?”
齐朗端着茶盏,细细地摩挲着上面的纹样,浅笑着反问了一句:“你指哪方面?”
谢清微哂:“先说格桑高原吧?”
永宁王妃也凝了神,专注地看着齐朗。
“朝中的意见似乎倾向于圣清旧制,是吗?”齐朗沉吟着看向谢清,谢清点头,眼神却是不以为然。
“元宁各地都有世族名门,权势炙手可热,但是,政出中央却是更加无可置疑的,格桑高原也不应该例外。”齐朗无意掩饰自己的想法,谢清轻轻击掌,附和他的意见。
永宁王妃好心地提醒两位:“据我所知,康人的天便是青教,你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康人也许与天塌地陷无异!”
谢清微微皱眉,齐朗却轻笑着搁下茶盏:“从我所知道的情况下,康人一样也是人,不是无欲无求的圣贤!宗教可以禁锢思想,却无法磨灭***,而只要有***,就会想要更多,争斗也就由此而生。”
谢清与倩容同时愣住,最先明白的却是倩仪,她听完齐朗的话,眼睛便是一亮,笑着反问:“你不会是想让水变得更浑些吧?”
“为什么不?”齐朗笑得很愉快,“张翊君对宁重说‘非我族类,其心必诛。’难道不对吗?”
“张翊君会错吗?”谢清哭笑不得,“反正,康人越弱,事情越好办!”
“那样会不会让格桑高原牵制住我们?”倩容仍然不放心,齐朗这个想明显需要时间。
齐朗轻摇茶盏,看着里面旋转的茶叶,低低地问了一问题:“如果有绝对的一方存在,规则会崩溃吗?”
三个人不由一惊,相互看了一眼,半晌,谢清才轻叹:“景瀚……你有些变了……”
齐朗摇头,轻言:“我只是……觉得我……离开得有些久了……”
对于这句话,三个人又是一愣,半天才反应过来——齐朗动怒了!
难道他不该生气吗?
回到成越以来,阳玄颢除了最开始见了他一面,就再未见过齐朗,也没有任何旨意,这种做法在引来非议的同时,也引来了对齐朗的怀疑。他们当然不会认为阳玄颢真的可以抛开齐朗,但是,有些人却未必。这三天,齐朗的怒意只会不断地积累,而现在,他不过是找个渠道发泄出来而已。
气氛有些沉重,但是,没一会儿,倩仪却笑了起来,引来几人的注目后,她才稍敛笑声,期待地道:“我只是想到,最近,后宫一定有不少好戏!”
是的!——如果紫苏不想因齐朗的事情与儿子直接冲突,那么,借处置另外一些人来警告便是必然的,所以,后宫会很热闹!
也只有亲身经历过类似事情的倩仪会这么快联想到这些!——世族豪门的后宅与后宫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