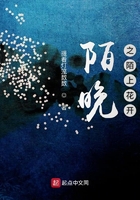据说大雪会吸走声音,所以慕容璟珑在风雪中静默地穿行,随着慕容儁身披裘绒的背影,灯光变换,直至抵达玉绥宫前。
跨过宫门,前庭早已掌了灯,纷繁的雪絮萦绕着方寸的光芒,晃出斑驳的影,就像夏夜义无反顾的飞蛾。
两人穿过回廊,仪鸾阁桂殿巍然,可是比之更让人惊异的,却是一阵若即若离的香气,慕容璟珑凝目去寻,居然是几株倔强的梅,细小的花瓣凝结为冰,缀在枝头恍如绯色的残片,泛着月色的玉茗,堇紫的鸢尾,突兀的与苍白的景致扞格不入。
他静立在花丛中,落英随风雪飘落化作猩红,雪如玉碎,纷纷被朔风裹挟,最终消失于浓郁的天底。
仪鸾阁高大的门扉缓缓开启,慕容儁背着柔光向他招手,他恍如惊醒般快步迈上石阶,门扉在他身后无声地关闭,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寒意。
仪鸾阁永远如眼前这般舒适、温暖、奢靡,而又拘谨,琉璃的灯彩悬在穹顶,大殿四角燃着掺入龙涎的炭火,墙壁蒙着防寒的皮革,脚下铺着松软的毛毡,在为十子准备的坐席前,此时有八人正襟危坐,而在大殿深处,在一副镌刻凤纹的横案后太后已面带愠色。
“儁儿,你已身为君上还如此般不识规矩!”她语带不满,虽是细语,却足以让殿上每个人都感到震颤,所以慕容儁保持躬身的姿态,像在等待宽赦,慕容璟珑只好与他保持一致,佯装出一副罪孽深重的表情,可他恨这个气氛,更恨这番光景。
“算了,今日气氛敦睦,便入座吧。”太后语气倨傲而散漫。
慕容儁径自走向席首,慕容璟珑则挨着慕容恪坐在末席,之后内侍奉上膳食,几样菜品,分别是清蒸燕鸢、白灼鱼肚、笋片、草菇与温热的梅酒,倒是相得益彰,若不是在令人拘谨的仪鸾阁中的话。
太后轻咳一声,“终于是齐了,”她面露笑意,缓缓地说:“哀家因离殇之愁痛贯心膂,难得今日十子聚齐,熙熙融融,哀家由衷忻愉,便与诸位皇儿小酌一杯,”她缓缓举起酒盏,“首先告慰先帝,愿他也能见此情景...”
因为提及逝者,气氛难免变得哀伤,不时慕容璟珑听到对面传来抽泣,不用侧首他便知道是刚行冠礼不久,被御封为远至迩安的始安王慕容默。
“幸于儁儿已龙袍加身,”太后接着说,“值此,哀家想与诸位皇儿一同祝贺君上,祈望他如先帝,受万世敬仰。”她语音已难掩欣悦,殿上的气氛也随之灵动,恭贺声此起彼伏,宴席亦就此拉开序幕。
觥筹交错,气氛热络,唯独慕容璟珑如坐针毡,独自饮酒。
“璟珑,去看望过皇甫大人了?”慕容恪执着酒壶,侧身与他说道。
“看过了,”他转过头,望着慕容恪的双眸露出清浅的笑意,“皇兄,最近钟情于醇醪?”
“宫中闲逸,无所寄托,不若醉生梦死,你也与我一般吧?”
“不,”他摇摇头,“皇兄,我前几日出城,顾不得饮酒。”
“哦?是去见皇甫大人时?”
“嗯,还见了贾玄心。”
“是太医院首席?”
“是,”他凝视着慕容恪细长的眼眸思忖半晌,“皇兄,贾玄心认为,父皇是误食了什么与药理相悖的东西,以至久病难愈。”
香醇的梅酿清露令人燥热,气氛更是醉人,推杯换盏间,仪鸾阁开始弥漫朦胧的醉意。
“什么,误食?”慕容恪握紧酒壶,手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光,“璟珑,他有依据?”
“依据?无非是药理常识,”他摇摇头,“可是,皇兄,”他刻意避开慕容恪的目光,说道:“可是我相信他。”
“一名抱病的垂老医者,璟珑,”慕容恪颇为诧异,“你相信他?你如何知道他不是臆想?”
“抱病的垂老医者不是更让人信服吗,皇兄?贾太医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父皇病情反复,所以他认为是内侍失职,或是药剂调配有舛讹,又或是某种食材与药理相悖。”
“璟珑,”慕容恪沉吟半晌,“贾玄心对你说了什么?”
“贾太医只是质疑父皇的病因,”他口上说,心里却在想,颖悟如慕容恪,终于听出了端倪,“父皇秋末尚能御马巡狩,会屈服于病疾吗?”
“璟珑,人有旦夕祸福,父皇的病...听母后说是积劳成瘁...”
“不,”慕容璟珑端起酒盏,殷红的梅酒仿若浓稠的血浆,“不,皇兄,”他说,“我相信父皇是死于外因。”他目光灼灼,映出火色。
“这不可能,”慕容恪摇摇头,“璟珑,君子之言,信而有征,你不能托于忖度,或是臆测..”
“皇兄,”他打断道,“我不过是设想,希望你能为我分析,为我剖断,若父皇真死于外因,死于..”他深吸口气,又颤抖着呼了出来,像是终于下定决心般说道:“死于中毒,皇兄,你认为凶手会是谁?
“璟珑,”慕容恪双眉紧蹙,语带嗔责,“我不敢这样设想,你也不应如此臆测。”
“皇兄,只是设想。”他坚持着。
“即便只是设想...”慕容恪喟然长叹,“璟珑,我不应这样说,可是终究拗不过你,”他将梅酒一饮而尽,之后无奈地摇着头,“如你所说,凶手能在皇城瞒天过海,必是有着通天能耐,而且父皇信任他,不然,怎避得过绣衣御使的眼线?”
“确是如此,皇兄。”他轻声浅笑,有能力下毒的,只能是同时拥有决意与动机的人,譬如仪鸾阁主,他边想,边望向正喜笑颜开的太后。
不止醇醪醉人,若是希冀品味醉意,便是热络的气氛也会让人忘形,可是对慕容璟珑来说殷红的梅酒非但尝不出醉意,反而流经之处皆如凝冰,一寸一寸,变得愈渐决绝。
四周觥筹交错,他却陷入犹疑,太后的动机,太后的决意,是为了慕容儁,还是为了她自己?因绣衣司而****到名为权力的毒,继而沉溺于高处的风景?以致动起了牡鸡司晨的心思。他不住思忖,直至慕容儁喟然长叹,殿上热络的气息便仿如退潮般销声匿迹。
“君上有心事?”与慕容儁比邻而坐的慕容交率先问道,他蓄着修剪整齐的短须,光滑的丝质长袍几乎映出炭火,而其他人,则像在等待宣判般静候着新王的回答。
“母后设宴,寡人本不应多言,”慕容儁龙袍上的金线亮得刺眼,他环视众人,说道:“可是孤近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君上,为何这样?”慕容交蹙眉问。
“或许是寡人力薄,父皇功列在上,寡人却感到力不从心,”慕容儁面色怅然,言之殷殷,“幸有母后提点,与诸位手足,不然孤何以坐拥江山?”
“君上又何必自谦?”太后说,“时政之事,多数急不得。”
“是,母后教诲的是。”慕容儁轻声应道。
“然而也有些,是刻不容缓,”太后说,“君上,不止一人向哀家进谏,说,战争未平之时,遭逢更迭大事,巩固皇权才是当务急迫,幸好太傅未雨绸缪,早已拟好法案,有关兵权变革,至于具体事宜...哀家不谙,似乎就是卫戍更替、驻将轮换。”
有人急不可耐地喝彩,虽然慕容璟珑知道他们其实并不懂得领兵权与谴兵权的区别,可是他懂得,他当然懂得,此时慕容恪也心如明镜,因为在仪鸾阁中,在整座玉绥宫中,还有谁握有兵权呢?他垂首不语。
“君上仁慈敦厚,可是仁慈敦厚难以安国,”太后说,“我们鲜卑一族繁衍自极北,诸子应居安思危,时刻谨记严寒的苦楚。”她声音袅如莺啭,可目光却怫郁难安。
“劳烦母后费心政事,诚然,巩固皇权是如今最急若星火的事!”慕容交附和道。
接下来仪鸾阁中絮语绵绵,对于太后刚刚描画出的眉目,诸子纷纷急遽地表达拥护,慕容璟珑却如置身事外,似乎已参透这场酒馔的真实用意,不是与赵高的指鹿为马异曲同工吗?
“哀家身为国母,诸事理应以国事先,可是哀家向佛,心余力绌,大燕的社稷之梁,终归还是要倚仗在座,对了,哀家最近听法师讲经,对一则禅理印象颇为深切,今日便与在座分享!”
相比无为而治的道,慕容皝显然更乐于国民信奉三世因果的佛,所以在燕国建立初时便摒弃巫教,开始推行佛法,并奉之为正宗,太后自然也过上了晨起焚香、暮落听经的生活。
巫教信奉万物通灵,相信黑羽所以驭空是因为栖宿着天空的灵魂,卵石所以光滑是因为栖宿着河流的灵魂,据说巫教的法师沐火而生,能参悟梦境,可是显然佛法更适宜统治,不论是对旅居的鲜卑,还是被套上枷锁的晋民。
“传说,灵山有一渊深潭,潭水澄净,水流通透,”太后缓缓叙述,阁中诸子纷纷放下竹箸酒盏,开始凝神聆听,“水中有一尾青鱼,每日摇曳,自在逍遥,因为灵山有灵,聚纳精气,渐渐青鱼竟有了清净之心,得以窥探四谛的真意,佛陀说未成佛果,先结善缘,青鱼自此开始不记春秋的苦修,这本是桩妙事,直至某天,谭中坠入一枚锦帕,其上几缕凡尘溅起了凡念的哀怨,也侵扰了青鱼的修行...”
太后讲及此,众人无不感喟。
“恪儿,”她接着说,“诸子中属你颖悟,满腹经纶,不如忖度一下这则禅理的结局。”
“忖度?”慕容恪放下酒盏,细长的眼眸在垂落的发丝下闪着光,“母后,儿臣相信万物皆有禅心,也许溅落的凡尘,不过是禅修途中的试炼,若青鱼心诚,必能修得正果。”
“嗯,好!”太后面露喜色,抚着手,“璟珑,你与恪儿亲近,想必也如此认为吧?”
青鱼吗?慕容璟珑不禁冷笑,“深潭不过方寸,青鱼所能追寻的善也无非本性,”他说,“一方锦帕所沾染的凡尘,又能有几许?”虽有些漫不经心,可他的心意与口气,还是被怨气占据了上风,“母后,若如此便让青鱼忘却初心,想来,恐怕万行所成的佛果,也不过如此。”
“璟珑,你!”太后秀眉紧蹙,面露愠色,“璟珑,你万不可轻慢佛法!”她声音细弱,却仿若一支沉重的羽箭,在射向慕容璟珑的同时也将诸人的目光引了过去。
“母后,璟珑一定没有轻慢的意思,”慕容儁从中劝解,“若青鱼五蕴皆空,无所住而生其心,相信清修日久,必能得善终。”
他边说边朝慕容璟珑使眼色,可慕容璟珑却视若无睹,反而继续说道:“母后,若人知佛法,世有因果,坠入谭中的锦帕不也是佛祖安排吗?那青鱼不过是在因果循环中身不由己苦苦纠葛的傀儡,能否结出善果便早已注定,又何苦挣扎?”
太后一怔,沉吟半晌,最终摇头长叹,“璟珑,心为万法源,若要明事,先要净心,”她语气平和,透出疲惫,并未继续表达不满,“哀家知你为战事操劳奔波,顾不得焚香听经,心中难免有些执念,所以哀家不怨你,不怪你,只是期盼某日,待到战事结束,你能诚心随哀家礼佛...”她极力按捺,可言语间依旧能听出些许斥责的意味,掷于阁中,溅起不安的波澜。
“哀家讲此禅理,是想告诫诸位:善者,诚谦慈勤俭也,恶者,欺骄嗔惰淫也。法师说予哀家,众生往往身处于顿悟的瞬间,成佛,成魔皆是一念执著,哀家期盼你们谨记,尤其是你,璟珑,”她语气中多出一分殷切,“先皇器重于你,大燕仰仗于你,但你一定要克服傲慢与自负,才能统御军马,成为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