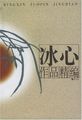有没有那么一滴眼泪能洗掉后悔
化成大雨降落在回不去的街
再给我一次机会将故事改写
还欠了他一生的一句抱歉
照片是在一个硬皮箱子的布缝里不经意发现的。
硬皮箱很大,现在被堆放在母亲房间的角落位置,多年不去想它,如今箱子上面被铺上了不薄的一层灰。
打开箱子,里面却是干干净净纤尘不染的样子,这是90年代前期才有人用的行李箱,这个箱子可能是父亲当年迎娶母亲时买的。
也许父亲结婚时父亲给母亲买了一个箱子,没有嫁妆,只带了些衣裳和贴心之物就奔赴向这样一个未来。
此时眼睛底下朝着绸带看见这样的旧夏,温和的河流寒缩,余晖打在杉树枝上斑斑落下。
细窄的小院里楼房旁边的那棵梧桐茂密伸展,它的旁边半年前是另一樟树,不知在哪个傍晚回家时它就变成了矮矮的树桩。
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她坐在树桩上和旁边的老人交头接耳不知在说哪一家小孩的坏话。
老人手持枯老色泽的圆扇,那原是一穗穗稻谷的长梗。余晖落在老人的圆扇上,不知何时消失远去了。而原本蒸腾的大地一粒一粒也在老人的圆扇底下变作清爽的夏夜。
空气里漂浮着一粒一粒的仲夏味道,掺着似有若无的樟树清香。
女孩的目光深深浅浅地穿过我不知放在了哪里,这个老夏天像颗粒分明的胶片电影跟着女孩的目光带到我的身旁只看到石桥上的女孩倒影深深,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照片里的小女孩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母亲说那时正值五岁半的老夏天。
照片很旧了,甚至有一些划痕,背景大抵是年少时喜欢的那条小河,所有的年少的炙烈美丽流淌成河。
即便到如今我已经不能够再记得那条河的名字,我知道在这不能有尽头的河流上,脉脉晖光将河流变作是一条不问未来的绸带,带着所有当日不能理解的悲怆走远了。
天气放晴好,年华正葳蕤。
有人说旧时光她是个美人,女孩在夏日夜晚捂着被窝在电话的这一头笑了。我们相识多少年,曾有多少年我们在同一个教室里望过窗外的野姜花一片一片跟着我们生长成为一座锐不可当的城。
小学六年级的毕业照还在吗,你还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知道他们如今是不是过得好吗?
初三毕业照是在教学楼的花坛前拍的,站在我旁边的女孩你还记得现在她在哪里吗?
可能你已经不能准确说出你的高中同学如今是在哪个城市读书吧。
后来我们都只是鲜少同几个朋友久久联系一次。
忽然我怀念每个夏天的夜晚我们同路回家的心情,还有灼灼路灯只有我看得见昏黄灯光四周环绕着的七色光。
他们说我是个奇怪的人。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的时候不经意间目光怔怔不知是想起了什么。你不知道少年时的夏日傍晚,你曾是我心里最美的梦。请你盖住自己的眼睛,再也不要在阴影里犹豫。
生命像一场细碎的勃发,内核被掩藏在海底。
而那一座座活火山则是一节一节向上拔长。
一月气聚
二月水谷
三月驼云
四月裂帛
五月袷衣
六月莲灿
七月兰浆
八月诗禅
九月浮槎
十月女泽
十一月乘衣归
十二月风雪客
你知道,这一月一月女子的一生不知疲倦地走过,稍稍停驻也应惊醒世间千般惶惶然,不要流连在旧季节里。
六月莲灿少年最是莲灿时,七月兰浆你走后又归来,八月诗禅人心易变你还是不得不舍,九月如浮云它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在你面前。唯有旧时光,幸好有你在那里,又幸好我们都还记得又舍得。
你是不是还记得当日有女孩面目清透疏朗,问你这老夏天何时回来。你知道生命里总是有些事没有答案。你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却不知盛宴过后,非要泪流满面才好。
于是我听见有人唱:
十七岁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
十七岁的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
有没有那么一种永远永远不改变
拥抱过的美丽都再也不破碎
有没有那么一张书签停止那一天
最单纯的笑脸和最美那一年
书包里面装满了蛋糕和汽水
双眼只有无猜和无邪让我们无法无天
有没有那么一首诗篇找不到句点
青春永远定居在我们的岁月
男孩和女孩都有吉他和舞鞋
笑忘人间的苦痛只有甜美
有没有那么一个明天重头回一遍
让我再次感受曾挥霍的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