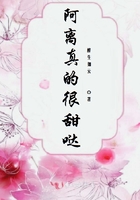景舍前后微摇着上身,说道:“鬼谷先生乃世间高人,人不能及,陈子师从鬼谷先生,不知从先生处习得何种高妙学问?”
陈嵊躬身朝景舍行了一礼,说道:“先生本领通天彻地,包罗万象。一曰未卜先知,预测吉凶之术,日星象纬,在其掌中,占往察来,言无不验;二曰兵家争略之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三曰言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词吐辩,万口莫当;四曰出世,修真养性,却病延年。陈嵊跟随先生三年,这些皆未悟到要旨。”
景翠咳嗽一声,说道:“但昨日陈子滔滔雄辩,引经据理,细数楚之要略,分明胸怀大才,这岂能作假?”
陈嵊指了指自己的眼睛与耳朵,道:“嵊从先生处所学,尽在此处。”
楚宣王与景舍皆有些皱眉,景翠讶道:“眼睛?耳朵?”
陈嵊微微一笑道:“也对也不对,嵊所学,乃观,听两字,观人面,察人色,听人言,循物法,得事理。庄子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事万物皆有多面,寻常人得其一,而不知有其二,得其二却不知有其三,概莫难全。”
楚宣王奇道:“陈子之说是否有些过于飘渺,譬如在庭前的一树,它乃本王亲手所栽,天地间只有一株,何来多面?又如陈子,天地也只得一位,难道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不成?那天地岂不乱套?”
陈嵊笑道:“庭前之树,王上栽种时多高?现在多高?春至而叶发,夏则叶绿,秋来则叶黄,冬却枝枯,日夜交替,树的景象又是各不相同,王上,这岂不是一物之多面么?”
陈嵊又道:“又如令伊大人,施仁政,息兵戈,生养休息,楚之百姓皆称其仁义,可对其余诸侯而言,令伊便如他们喉中鱼梗,背长针芒,恨不得令伊早早告老还乡,王上,这岂非是人之多面?”
景舍微微一笑,抚了抚花白的胡须,楚宣王哈哈大笑道:“有趣,陈子说得有趣,不知陈子的观听之说可否能施于国政之上?”
陈嵊低头沉吟少顷,微微一笑,说道:“王上,草民便斗胆试言。”
楚宣王点头道:“有景老令伊及司马,诸位大臣在场,陈子但说无妨。”
陈嵊拱手道:“请问王上,诸位大臣,现今天下,七雄并立,楚的局势是好还是坏?”
一臣说道:“本官乃下大夫江亿,来回答陈子的问题,楚疆域广阔,王上在位任贤而赞德,令伊当政而使百姓富足,司马将兵而使兵甲锋锐,民乐政而士有勇,拒齐魏,制远秦,摄九夷蛮越,天下莫不仰之。”
陈嵊答道:“依草民看来,楚正处险境诸位却不自知,下大夫之言可笑之极。”
江亿大怒道:“陈嵊,你岂敢在朝堂之上危言耸听,妖言惑众,眼中可有王上及诸位大臣?”
景翠不满地看了江亿一眼,对楚宣王说道:“王上,陈子如此说法必有因由,请许陈子继续论说。”
楚宣王点点头,脸色平静,不知其想。
陈嵊说道:“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秦争魏之河西之地长达百年,何也?皆因占据河西,秦骑便可直进中原,再无屏障可阻。魏为何要与韩赵为敌?皆因占据韩赵便可恢复昔日强晋,方可与齐楚争霸。”
“秦魏皆有争霸之心,君臣民齐心,故兵精将勇,而反观北地之燕,空占渔阳,上谷之地,却偏居苟安,国弱不堪,晋中韩赵,累受秦魏所迫,难有气数。”
“今天下七雄,楚地非独大,楚臣非独贤,楚民非独勇,楚兵非独精,楚不以强者而效,却口呼‘天下莫不仰之’,以强者而居尊,心存安逸养富之态,外人皆跑步向前,而自己则志得意满,原地踏步,距离越拉越大,若满朝楚臣皆是如此想法,岂非等同乱臣误国乎?”
满座无声,景舍看了陈嵊一眼,说道:“陈子所言,未免夸大其词,你口中秦魏虽强,但为争河西,两强连连征战,两强相争,必成一死一伤之局,而我楚居侧休养生息,壮大国力,待两强争休,精兵尽出,以逸待劳,岂不是全胜之局。”
陈嵊哑然而笑,说道:“令伊之言适合莽夫争勇,不可用于国政施略。”
景翠说道:“令伊大人,领兵之道,不在力,而在略。王上,微臣觉得陈子所言确实肺腑之言,楚该有所行动了。”
楚宣王不点头,亦不摇头,摆摆手道:“今日便议到此处吧,不知陈子现居何处?”
陈嵊答道:“客店之内。”
楚宣王对景翠道:“陈子乃是楚的贵客,岂能陋居在客店,烦请司马替本王好好招待陈子,明日再领陈子入殿廷议。”
又转头对陈嵊道:“陈子,你看此安排可妥当?”
陈嵊拱手道:“让王上费心了。”
司马府中,景翠坐在堂上,皱起眉头,眼睛看了几眼陈嵊,才问道:“陈子,你看今日王上为何突然休议?”
陈嵊抿了一口茶,淡淡说道:“王上虽有心动,但仍有顾虑。”
景翠讶道:“什么顾虑?”
陈嵊沉吟道:“为君者,善驭臣之道,王上若以我为臣,也需照顾老令伊之心,结果如何,明日该有分晓。”
令伊府中,老令伊眉头深锁,无精打采地坐在堂前,旁边站着一人,乃是他的儿子景唤,景唤见老令伊面色发忧,忙问道:“父亲,今日朝中发生何事,让你忧虑?”
景舍叹口气道:“今日司马引荐了一位士子给王上。”
景唤道:“楚得人才,父亲怎显忧虑,莫非王上未有表示?”
景舍摇头道:“非也,只因此子怪才巧辩,想法激进,与老夫政见相左,如今朝上,司马与父,一个主张强兵争霸,一个主张富民修生,刚好势均力敌,但若此子得王上欢心,只怕朝中便无为父说话之处了。”
景唤微微沉吟,说道:“那今日王上可已册封此子?”
景舍摇摇头,说道:“王上虽然没有立即册封,但嘱司马好好招待此子,依老夫看来,此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这时下人来报,学士黄歇来拜。
景唤连忙退下,景舍忙请黄歇进屋,左右坐下,景舍问道:“不知黄学士前来府中有何要事?”
黄歇拱手道:“令伊心中有忧,但愿晚辈可为大人解忧。”
景舍表情微微一凝,问道:“学士何出此语?”
黄歇笑道:“今日王庭之中,那陈嵊咄咄逼人,尽数庭中大臣之丑,且他主张强兵之策,与司马志趣相投,令伊大人担心若王上以他为臣,楚将走向穷兵黩武之途,故此有所忧虑。”
景舍叹道:“学士所言正中老朽之心,老朽正不知该如何处之。”
黄歇摇头道:“令伊莫慌,王上似乎也对此子有所顾忌,并不敢放手相托国事,晚辈此来,是要告诉大人一个消息,必可解大人忧虑。”
景舍忙道:“学士请说。”
黄歇微微一笑,道:“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你可记得三年前洛邑之变中,周天子任命的太傅是谁?”
景舍微微沉思,脸色却突然惊变,惊呼道:“难道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