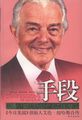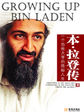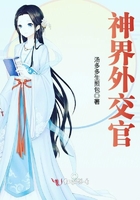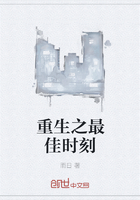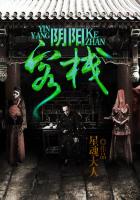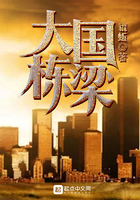小说之支配人道,有四种力:一是熏,“熏也者,如人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是浸,“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三是刺,“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他既明白小说的感化力如此的伟大,所以决意便于《新民丛报》之外复创刊《新小说》,然《新小说》刊行半年之后,梁氏的着作却已不甚见。大约他努力的方面后来又转变了。
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说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他最勤于发表的时代。我们看民国十四年(乙丑)出版的第四次编订的《饮冰室文集》里,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强。
《新民丛报》与《新小说》创刊的第二年(一九○三年),梁氏曾应美洲华侨之招,又作北美洲之游。这一次却不曾中途折回。他到了北美合众国之后,随笔记所见闻,对于“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结果便成了《新大陆游记》一书。
在这一个时期内,还有一件事足记的,便是从戊戌以后,他与康有为所走的路已渐渐的分歧,然在表面上还是合作的。到了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后,便显然的与康氏背道而驰了。他自己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学术概论》二百四十三页)世人往往以康梁并称,实则梁氏很早便已与康氏不能同调了。他们两个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执着的,不肯稍变其主张,梁氏则为一个流动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军起于武昌,很快的便蔓延到江南各省。南京也随武昌而被革命军所占领。梁氏在这个时候,便由日本经奉天而复回中国。这时离他出国期已经是十四年了。因为情势的混沌,他曾住在大连以观变。南北统一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司法次长招之。梁氏却不肯赴召。这时,国民党与“进步党”(民元时代名共和党)的对峙情形已成。袁氏极力的牵合进步党,进步党也倚袁氏以为重。梁氏因与进步党关系的密切,便也不得不与袁氏连合。他到了北平与袁氏会见。会见的结果,却使他由纯粹的一位政论家一变而为实际的政论家。自此以后,他便过着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竟有七年之久。这七年的政治生活时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时代,也是他的着述力最消退,文字出产量最减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与袁世凯合作的时代。癸丑(一九一三年)熊希龄组织内阁,以梁氏为司法总长;这是戊戌以后,他第一次踏上政治舞台。这一次的内阁,即所谓“名流内阁”者是。然熊氏竟无所表见,不久竟倒。梁氏亦随之而去。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说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然他却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凯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终要立在维持现状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为。欲有所表见,欲有所救益。这时,最困难的问题便是财政问题。梁氏在前几年已有好几篇关于财政及币制的文章发表(这时他的文章多发表在《庸言报》上)。这时更锐然欲有以自见,着《银行制度之建设》等文,发表他的主张。进步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出于他的手笔。袁世凯因此特设一个币制局,以他为总裁(一九一四年),俾他能够实行他的主张。然梁氏就任总裁之后,却又遇到了种种的未之前遇的困难;他的主张一点也不能施行。实际问题与理论竟是这样的不能调合。结果,仅获得《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辞职以去。自此,他对于袁氏方渐渐的绝望了,对于政治生涯也决然的生了厌恶、舍弃之心。他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即《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恳挚的说明,他自己是很不适宜于实际的政治活动的。他说:“夫社会以分劳相济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长为贵。吾立于政治当局,吾自审虽蚤作夜思,鞠躬尽瘁。吾所能自效于国家者有几。夫一年来之效概可睹矣。吾以此心力,转而用诸他方面,安见其所自效于国家者,不有以加于今日!”他更决绝的说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见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虽以骨肉之亲,或不能苟同也。”他这样的痛切的悔恨着过去的政治生涯,应该再度的复入于“着述时代”了。然而正在这时,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却恰恰与他当面。欧战在这时候发生了;继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机在中国获得意外的权利;继之而帝制运动突兴,袁世凯也竟欲乘机改元洪宪,改国号中华帝国,而自为第一代的中华帝国的皇帝。种种大事变紧迫而来,使他那末一位敏于感觉的人,不得不立刻兴起而谋所以应付之。于是他便又入于第二期的政治生涯。
第二期是“护国战役”时代。他对于欧战,曾着有《欧洲大战史论》一册;后主编《大中华月刊》,便又着《欧战蠡测》一文。更重大的事件,中日交涉。使他与时人一样的受了极大的刺激。他接连在《大中华》上写着极锋利极沉痛的评论,如《中日最近交涉平议》、《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示威耶挑战耶》诸作。及这次交涉结束之后,他又作《痛定罪言》、《伤心之言》二文。他不曾作过什么悲苦的文字,然而这次他却再也忍不住了!他说道:“吾固深感厌世说之无益于群治,恒思作壮语留余望以稍苏国民已死之气。而吾乃时时为外境界所激刺,所压迫,几于不能自举其躯。呜呼!吾非伤心之言而复何言哉!”(《伤心之言》)
更重大的事件帝制运动,又使他受了极大的刺激。他对于这次的刺激,却不仅仅以言论而竟以实际行动来应付它了。帝制问题其内里的主动当然是袁世凯,然表面上则发动于古德诺的一篇论文及筹安会的劝进。这是乙卯(一九一五年)七月间的事。梁氏便立刻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于《大中华》。梁氏在十年前,原是君主立宪论的主持者,然对于这次的政体变更,却期期以为不可。他的理由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里说得又透彻,又严肃,又光明,又讥诮。他以为自辛亥八月以来,未及四年而政局已变更了无数次,“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作帝制论者何苦又“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并为袁氏及筹安会诸人打算利害,以为此种举动是与“元首”以不利的。当时他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以上引文皆录自《盾鼻集》)他的此文,草成未印时,袁氏已有所闻,曾托人以二十万元贿之。梁氏拒之,且录此文寄袁氏。未几,袁氏又遣人以危辞胁喝他,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氏笑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的人语塞而退。这时,梁氏尚住在天津。他的从前的学生蔡锷,革命后曾任云南都督,这时则在北平。于是梁、蔡二氏便密计谋实际上的反抗行动。在天津定好后此的种种军事计划,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二人并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他们便相继秘密南下。蔡氏径赴云南,梁氏则留居上海。这一年十二月,云南宣布独立,进攻四川。广西将军陆荣廷则约梁氏赴桂,同谋举义事。他说道:“君朝至,我夕即举义。”许多人皆劝梁氏不要冒险前去,然他却不顾一切的应召而去。丙辰(一九一六年)三月,梁氏由安南偷渡到桂,时海防及其附近一带铁路,袁政府的侦探四布。梁氏避匿山中十日,不乘火车,而间道行入镇南关。至则广西已独立。不久,广东亦被迫而独立。然广东局面不定,梁氏冒险去游说龙济光,几乎遇害。两广局面一定,他便复到上海,从事于别一方面的活动。这时才知道他的父亲宝瑛,已于他间道入广西时病殁了。这时,情形已大为转变。浙江、陕西、湖南、四川诸省皆已独立;南京的冯国璋也联合长江各省谋反抗。正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忽然病死。于是这次的“护国战争”便告了结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梁氏则实践初出时的“决不在朝”的宣言。并不担任政务。然不久,却又有一个大变动发生,又将梁氏牵入漩涡,使他再度第三期的政治生涯。
第三期是“复辟战役”时代。当欧战正酣时,中国严守中立,不表示左右袒的态度,虽日本在山东占领了好几个地方,以攻青岛,我们也只是如在日俄战争时代一样的置之不见不闻。到了后来,德国厉行潜水艇海上封锁政策,美国首先提出抗议。中国的抗议也继之而提出。德国方面却置之不理。于是中国便进一步而与德奥绝交,协约国极力劝诱中国也加入战团。梁氏承认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增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可以收回种种已失的权利,便极力的鼓吹对于德奥宣战。他在大战的初期,着《欧洲大战史论》及《欧战蠡测》之时,虽预测德国的必胜,然在这个时代,他已渐渐的瞧透德奥兵力衰竭的情形了。在这个时候,黎元洪与段祺瑞已表示出明显的政争情态。实际上是总统与总理的权限之争,表面上却借了参战问题,做政争的工具,段氏主张参战,黎氏则反对参战。梁氏因段氏的主张与他自己的相投合,便自然的倾向到段氏一方面去。不幸这次的政争愈演愈烈;参战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而内政问题却因黎氏的决然免去段职之故而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澜。
段氏免职之后,继之而有督军团的会议,而有各省脱离中央的宣告,而有张勋统兵五千入北京,任调停之举。这个“调停军”的内幕,却将黎段两方都蒙蔽了。原来,张勋此来,系受了康有为诸人的怂恿,有拥宣统复辟之意。黎氏固不及觉察,即段氏也不甚明白。直到张勋到了天津,复辟的空气十分浓厚,他们才十分的惊惶。于是梁氏与熊希龄急急的欲谋补救,宣统复辟于六年七月初成事实。梁氏乃极力的游说段祺瑞,要他就近起来反抗。马厂誓师的壮举,一半是梁氏所怂恿的。梁氏自己也于七月一日发表了一篇反对复辟的通电,持着极显白的反抗态度。他陈说变更国体的利害,十分的恳切动人,较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尤为直捷痛切。他说:“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觉悟,洗心革面,则虽岁更国体,而于政治之改良何与者。若曰建帝号则政自肃,则清季政象何若,我国民应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过去罪将焉蔽。况前此承守成余荫,虽委裘犹可苟安,今则师悍士狡,挟天子以令诸侯。谓此而可以善政,则莽卓之朝,应成郅治。似斯持论,毋乃欺天!”这些话,都足以直攻复辟论者的中心而使之受伤致命的。梁氏又说:“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伐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抑天下固多风骨之士,必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然这事不必望之于他人,他自己便已投笔而兴了,他自己已不徒实行着口诛笔伐,而且躬与于“讨伐”之役了。这时,他与康有为已立于正面的对敌地位。自戊戌以后,梁氏与康氏便已貌合神离,为了孔教问题,也曾明显的争斗过。而这次却第二次为了政治问题而破脸了。梁氏自己相信他始终是一位政论家,不适宜于做政治上的实际活动。他非到于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肯放下政论家的面目而从事于政治家的活动。这一次,与护法战役之时相同,都是使他忍不住不出来活动的。他带着满腔的义愤,与段祺瑞会见于天津;他说动了段氏,举兵入北平。在这时,似乎也只有段氏一个人比较的可以信托。其他的督军军人们都是首鼠两端的。段氏的崛起,使张勋减少了不少的随从。段氏便很快的得到了成功,扑灭了以张勋、康有为为中心的清帝复辟运动。张康等皆逃入使馆区域。梁氏在政治上的成功这是第二次。他对于共和政体的拥护,这也是第二次。
段氏复任总理,黎氏退职,由副总统冯国璋就任大总统。段氏既复在位,对德奥宣战,便于那一年的八月十四日实行。梁氏这次并不曾于功成后高蹈而去。他做了段内阁的财政总长(一九一七年)。他很想发展他的关于财政上的抱负,然而在当时的局面之下却不容他有什么主张可以见之实施。不久,他便去职。经过这一次的打击之后,他的七年来的政治生涯便真的告了一个终结。自此以后,他便永不曾再度过实际上的政治生活。自此以后,即自戊午(一九一八年)冬直到他的死,便入于他的第二期的着述时代。
第二期的着述时代绵亘了十一年之久。这个时代,开始于他的欧游。一九一八年欧战告终,和会开始。抱世界和平的希望的人很多,梁氏也是其一。他既倦于政治生涯,便决意要到欧洲去考察战后的情形。他于民国七年十二月由上海乘轮动身。他自己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梁任公近着第一辑》卷上七十三页)在船上,他本着第二个目的,曾做两三篇文章,为中国鼓吹,其中有一篇是《世界和平与中国》,表示中国国民对于和平会议的希望。后来译印英法文,散布了好几千本。他在欧洲,到过伦敦、巴黎,到过西欧战场,到过意大利、瑞士,还到过为欧战导火线之一的亚尔莎士、洛林两州。这一次的旅行,经过了一年多。民国九年春天归国,他自己曾说起对于此行的失望,第一是外交完全失望了,他的出国的第二个目的,最重大的目的,已不能圆满达到;第二是他“自己学问,匆匆过了整年,一点没有长进”。在这一年中,真的,他除了未完篇的《欧游心影录》之外,别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写;而到了回国以后,所着作,所讲述的仍是十几年前《新民丛报》时代,或第一期的着述时代所注意,所探究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此可见他所自述的一年以来“一点没有长进”,并不是很谦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