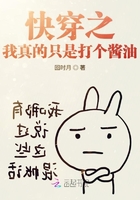“你会数数吗?”
“废话。”
“数到一万零七十七,然后按照我说的做。”
“……”
“怎么了?我说得还不够明白?你后悔还来得及。”
“不……为什么是一万零七十七?”
“喔,数到一万刚刚好,七十七是个多头,那是我的幸运数字。”凌子冲曾经嘻嘻笑着说,“七月七号是我的生日,如果你记得,下次给我礼物。”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齐家福数到一百零四的时候,他被带进了一个香喷喷的小屋,两个香喷喷的女孩子正在等他。
齐家福数到一百零五的时候,他眼睛上的黑布被摘了下来。
然后他差点就不会数数了。
那两个女孩子是真正的“女孩子”,跟她们比起来,齐府的那些下人们根本就是会说话的木头。
“我叫小苔。”
“我叫小藓。”
“我们会把你洗得香喷喷的。”
“然后吃掉。”
“你怎么不说话呢?”
“他被吓坏了,从上面下来的人都是这样。”
于是她们交头接耳的笑,黑色的长发和褐色的长发打着卷儿混在一起,缠绕着两个人圆润的肩头。
齐家福很悲愤地想……四百一十一。
小苔有一对雪白修长的手臂,小藓有一双淡褐色的、似乎随时随地就要起舞的腿。她们穿着白色的质地厚重的袍子,毫不介意长袍浸到半湿,湿漉漉水淋淋地勾出年轻的曲线来。她们在巨大的木桶里注满热水,洒进碎玉屑和一瓶又一瓶奇怪的东西,她们的样子专注又快乐,甚至没有看齐家福一眼——就像是一个好厨子在清洗他的蔬菜一样。
三千二百九十七……女孩子准备洗澡的时间真是长啊。
“你是自己洗呢?还是我们帮你洗?”
齐家福二十岁,他做了一个二十岁的男人应该做的选择。
黑铜指环摘了下来,与风影骑的联络彻底中断,两双美丽而柔软的手掠遍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这可能是他经历过最温柔的搜身。
温滑的热水浸泡着伤口,血污和泥垢被化开,疼痛从四面八方传来,但水里有什么东西在让痛苦迅速减轻。轻松和****贴着身体游走,喉咙在发干,身体的某个部位渐渐不受控制,但一个铁一样的声音在脑子里数着:八千九百二十五……
“你是要我们一起,还是挑一个呢?”小苔柔若无骨的手臂搭上他的脖子。
“挑一个,她。”齐家福指了指小藓。
小藓有一点吃惊,可这吃惊很快归于平静,她轻轻放下手里满桶的热水,向他走来,脚步轻盈如舞步。
小苔踢了一脚空水桶,离开。
小藓有着淡蜜色的肌肤和湖泊一样的眼睛,海藻一般浓密的长发打着卷,垂到腰际。齐家福年轻见识浅,没有见过活生生的女人的胴体,可他确定这是难得一见的极品——小藓本身或许没有那么美,可她只要一动起来,浑身每一个部位就像合着旋律在舞蹈。
“为什么是我?”
“怎么?你不愿意?”
“愿意,是我自己要来的。”
她不是那种让人怜悯的姑娘,可眼睛里盛着深渊一样的悲哀,似乎眨一眨,就有看不见的泪水流下来。
齐清燃也很美,但齐清燃美得像一朵花,一幅画,只让人想要后退一步,静静观赏。可是这个姑娘……可以让所有男人失去理智冲上去。
小藓的无袖长袍在左肩上打了个大大的结,随手一拧,长袍就松落下来。她的身体轻盈而充满诱惑,可眼睛里的痛苦越来越沉重,她无声无息地滑进齐家福怀里,呢喃如祷告:河神啊……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说?”齐家福的手握住她的后颈,浓密的长发和细细的脖颈只堪一握。
“是啊。”
“你上次爱的那个人在哪里?”
小藓嘴角有轻轻的笑,她的手抚摸着他的胸膛:“我并没有问过你,你现在爱的人在什么地方。”
“你问也没有关系,我没有。”
“你在骗我。”
“我说了没有。”
“那你就是在骗自己。”小藓抱紧了他,闭着眼睛:“抱紧我,不要动,抱紧我。”
齐家福不假思索地抱紧了她,他没有闭上眼睛,闭上眼睛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些不看到的东西。
一万。
一万还是很快的,一万也******太快了!
小藓在等待,等待一场纠缠冲散眼里的悲哀。
“你应该去找那个人。”齐家福在小藓耳边说,“我猜你知道他在哪儿。”
“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找到了不能怎么样,找到了就是找到了,总比你现在这样好。”
小藓有些愤怒地张开眼睛:“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一个奴隶。”
小藓的眼睛像是被深深地刺了一下。
“你第一眼就在看我手上的烙印,我想这不是烙印特别好看的原因。”齐家福顿了顿,一万零七十。
“我找过了,也找到了,他不爱我,他只爱自由。”
一万零七十七。齐家福伸手在小藓左颈上抹了抹,多说了最后三个字:“他骗你。”
他披上人生第一件长袖浴袍,走了出去。
掌心一粒蜡丸,已经捏得快要化了,齐家福小心翼翼地打开,那里面是一张薄如蝉翼的地图——他并没有想到,地下相城居然有如此庞大的规模。
凌子冲显然并不愿意他了解太多的情况,这张地图标注的不是很详细,但还可以隐约弄清楚,除了交易往来的公共领域,京城四少各自有一块地盘,其中一个人的地盘足可以抵上其他三个的总和,如果猜得不错,那应该是少一事。
有一条用指甲划出来的小路,曲曲折折,通向另一个区域某个小小房间。
“口令?”过路客好像在问今天天气如何,随口那么懒洋洋地一句。
“鱼目混珠。”齐家福也漫不经心地回答。
——这里是一个口令的世界,甚至你可能会发现每一道门,每一条甬道,每一处区域……都需要不同的口令,我给你的这个,只能确保你走到那个房间去,如果乱走,我保证你不得好死。
——我相信你甩开姑娘们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但是你不许伤害她们,如果你伤了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此后的余生恐怕都不会太愉快。
——你过来,我会告诉你来干什么,这是个赌注,我不保证你能活着走出去。
——做决定吧。
我早已决定。
一个人认识的第一个字,不应该是手臂上的那个字,不管那个字意味着什么。
齐家福向前走,但这个地下世界,并不象想象中那么阴霾,来来去去的人,也比意料之中多了很多。
大半都是年轻人,而且主动又热情地打着招呼,他们形形色色,有着近乎醉酒的迷幻和近乎嚣张的快乐,年轻的少男少女以放肆的姿态缠绕在一起,连体婴儿一样向前走着,脸上都有着终年不见阳光的苍白。
一大群年轻人,足足有十七八个迎面走来,堵满了过道。
“这里有什么不好吗?”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一样,一个浑身罩着层半透明纱笼的少女驻足,对着他眨眨眼。
她的朋友们看也不看她一眼,继续谑笑着向前。
齐家福顿时窘住了,这件纱衣未免太“那个”了一点,刚刚成熟的胴体曲线毕露,他一时不知道应该把目光投向哪里,眼珠乱转了几通,才终于锁定在少女左肩——那里有一朵金色的蒲公英饰物,打造得非常精巧,无数蓬绒的小伞罩住了女孩子的肩头。
“我认识这件浴袍,你是小苔带回来的吧……”女孩的手指滑过浴袍边缘,若有若无地触碰着齐家福的胸膛:“小苔总是很有眼光。”
“谢谢。”齐家福后退了一步。
“你很放不开呀……你是新来的?”
“嗯。”
“在这儿不用顾虑这么多,只要你不乱走乱问,想做什么都可以。”女孩子的眼睛开始闪光,她兴奋地微笑:“我喜欢调教新人,我喜欢看着你们慢慢的……变得自由。”
“你真的觉得这就叫自由?”齐家福是这么想的,也随口就这么说了。
“当然。”看得出女孩子真的是很热爱这里:“无拘无束,想做什么都随意,只要你有一样特长,随便是什么,都能去交换你要的东西。刚来的时候你会有点儿不习惯,很快就会好了,唔……你在上面是个奴隶,你做的很好了,我遇见过刚刚下来的奴隶,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撕掉自己的袖子。”她的手指已经顺着滑到了齐家福的手腕,啧啧惊叹地欣赏着手腕上的烙印,“字很漂亮。”
齐家福也不收回手腕,只是接着她的话头:“不用去顾忌想要的东西都是怎么来的,虽然有时候它们来的不干净也不公平,是么?”
“公平?”少女大笑起来:“喂,小黑奴,你在对我说公平?嘿,嘿,你不用皱着眉头,你要是不喜欢我这么叫你,你可以随便用什么词儿反击回来嘛……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你能活着走到这儿,靠的是干净,还是公平?”
齐家福没有说话,少女身边的人都在笑,但不是嘲笑。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好奇而已。”齐家福确实只是好奇:“这些话是少一事教你们的?”
“少一事是谁?”少女拧起眉头来,她停下来搭讪不是为了这种伤脑筋的谈话的,“你要去哪里?跟我们一起去玩吧,我们缺个男孩。”
齐家福摇摇头:“抱歉,我没有兴趣。”
女孩子直视他的眼睛,惊讶:“我明白了,你得病了。”
“没有。”
“胡说,骗我……你既然病了,就不应该这样走来走去,免得别人白费劲招惹你。”
“你说的……生病,是什么意思?”
少女从肩头摘下那枚蒲公英胸饰,别在齐家福的浴袍上,轻轻拍了拍:“病了就带上这个……好啦好啦,反正我我的病已经好了,送你吧,替我问小苔好。”她顺便在齐家福面颊上拍拍,声音轻佻而诱惑:“如果有一天病好了,记得来找我,我住在捺八区三道五里七洞,记住了?”
“记住了。”
他们和平友好地分道扬镳,那少女还抱着肩膀目送齐家福离去——他在第一个路口处停了停,没有拐弯,而是伸手在墙上试探着打开一道暗门,走了进去。少女大惊——“天哪,他怎么会去那个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