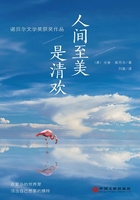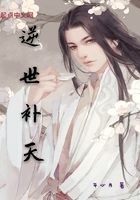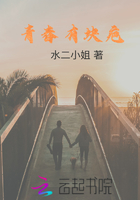宽敞中的孤独
我在一条名叫Antoinette(安彤耐特)的Lane里住了10年。Lane,在英文中是小巷、小道的意思。安彤耐特弄堂是一条死道(Dead Road),很像上海的弄堂。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把美国的一条死道和上海的弄堂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弄堂是有后门的,比喻得并不确切。但是,我相信在离开上海弄堂三四十年以后,它突然在异国他乡冒出来,绝不会无缘无故,一定是出于什么契机给我送来不寻常的信息。
我确实出生在上海一条弄堂的小阁楼里,只记得窗很高,屋顶很低,楼梯很黑,家里十分拥挤。那是清贫如洗的记录,家里人都不太愿意提及。可是,我的记忆恰恰是从那里开始。小孩子不喜欢宽敞,也不适应明亮,因为母亲的子宫也是狭小和黑暗的。
我在小阁楼里住了四年,留下的记忆并不可靠,有些可能是长大以后拼凑而成,因为上海的阁楼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小阁楼曾经数度在我的梦中出现,有时候独自爬在陡立的楼梯上,像睁眼瞎一样,伸手不见五指;有时候,站在小板凳上,踮起脚尖往窗外张望,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过,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梦了。
出国来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人生变化,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谁,更谈不上回忆出生的地方。是这栋房子、这条弄堂把我拉扯到记忆的源头。
也许离开母体的孤独和恐惧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小阁楼一直驻在我的心头,只是被时间的尘埃所湮没和封存。否则如何解释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它突然以死道的形式在我的眼前复活呢?
美国的死道与中国的弄堂完全没有可比之处。
安彤耐特弄堂很短,不到百米,共15户人家,多是四卧室两厅两厕两车位的平房,属于中产阶级的居住水平。路口朝西,对着太平洋。路的两旁各六栋房,路东三栋,呈半圆型,把路封住。路南第二栋就是我的家。
上海的弄堂是一个居民单元,由一排排像美国“Town House”那样的楼房组成,一栋楼有三到四个门牌号码。每个门牌里,卧室和露台在楼上,客厅和厨房在楼下,楼前还有一个空间,围在砖瓦水泥墙里面,供种花养鱼等休闲之用。这种房子,如果一个门牌只住一户人家的话,是蛮舒适的。
安彤耐特弄堂由一栋栋独立的洋房组成,房间的总数超过人口。
上海有“七十二家房客”的文化风情,每栋楼都塞满了人,房叠房(称为“阁楼”),床叠床(打地铺),一间睡房几代同堂,“集中营”式地挤在一起。楼上楼下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水龙头,居然相安无事,持续了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上海人精明、圆滑,有锐利的目光、敏感的嗅觉,既善于合作又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和拥挤的生存空间有关系。一方面,天天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缺少自由和个性。另一方面,远亲不如近邻,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也是整栋楼分享,像大家庭一样。
美国的房子,宽敞得家家可以开个招待所。以每个睡房安两张床计算,我们家里有四间睡房,八张床起码能睡十人以上。厨房和餐厅连在一起,摆个四五桌还绰绰有余呢!但是,住在里面的只有三口人!我喜欢宽敞,喜欢客厅里的玻璃大门,喜欢明亮的洗澡间,喜欢设备齐全的厨房,喜欢在晚上睡觉前把里里外外十几扇门都检查一遍。可是宽敞得有点失落,有点无法定位。我不知道前后左右都住些什么人;做饭时,闻不到隔壁刺鼻的辣椒和香醇的酱油味;外出时,无人招个手,更向谁去高声报个去处?至于互通买便宜货的信息或者推荐一个有本事的医生,至于看个球赛和电影时营造一点捧场起哄的氛围,以及倾听邻居吹牛、传送小道消息等,都一去不复返也。
刚搬来的时候,我简直无法住下去。
“能不能搬去一个连着左邻右舍,有大家庭气氛的地方住?”
美国先生抓抓头皮朝我看,不吭声。我发脾气的时候,大声嚷嚷:“这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吗?”
我怀念和人交流,怀念被人注意,怀念关心别人,怀念……霎时间,上海的“七十二家房客”好像变得如天堂一般美好。
先生不紧不慢地说:“那,就不是这样的房子了。”开始我不懂,后来才知道,那是房式一律、地宅狭小、墙连墙的低价房屋。美国也有“上只角”和“坏地段”之分。可是,居住空间和孤独成正比:房子越大,生活越是乏味。
发现玛丽亚
这里的房子都设计得很简单。如果乘飞机,从上空往下看,我们就像蚂蚁住在一把手枪里。厨房、餐厅连着车库,是枪柄。枪身比枪柄长一些,里面横剖为二,中间是过道,卧室两南两北,余下的就是客厅和厕所。卧室外是宽敞的草坪,铺在马路和住房之间,绿茵茵、厚甸甸的,引来小鸟、蝴蝶,也可供我们打排球。有时候还有无名之犬来凑热闹,在我们的草坪上大小便。屋后是小巧玲珑的花园,松柏、花卉、果树、攀藤,都被围在齐肩高的砖墙里,还有蓝天、白云和涛声。
我在家工作,办公室朝北,抬头便见马路风景。
观察马路上的动静,在过去简直是对时间的亵渎。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从来不知道度假是怎么回事。我的脑子里除了学习就是效率。可是现在,我一边喝茶一边和马路“调情”。
那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天才破晓,就有人陆陆续续地去海滩散步,看不清嘴脸,好像移动的剪纸艺术一般,有的牵着狗,有的头上套着耳机。去时快,小跑的样子。回来时,慢悠悠的,像逛街一样。
天色由灰转白,朝阳升起来。抬头看,上空一半红一半蓝,海鸥穿插其间。金辉从马路的一角慢慢地染过来,弄堂好像脱去了灰色的睡衣。这时,耳边响起了马达声。
窗前出现了一辆辆汽车,如彩色的热带鱼鱼贯而出,一边以锵锵的现代音乐伴奏,一边给我们的弄堂留下一道道速度的烟尘。
这情景与清晨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就在几分钟之间,小巷如倒空了的口袋,安静得要命,好像能把我消化了一样。此时此刻,这条弄堂只属于留守在家的人们。
呵,在美国旧金山南部的一个小城里,有一条叫安彤耐特的弄堂。静下来的时候,我轻声叫着它的名字。安--彤--耐--特,好听又上口!Antoinette,似曾相识!
我陷入了沉思。
斜对面那块蟹青绿的路牌,上面用白色写着Antoinette,总是目空一切地站着。它像高贵的守护神,却又默默无闻。我越看着它,越生出好奇的感觉。
每天,当我拥有整个弄堂的时候,我的思绪涓涓细流。
每天,当我面对路牌的时候,想象的门似被轻轻推开。
美国有许多总统的名字被刻在路牌上,如华盛顿、杰弗逊;有许多著名的城市被用做路名;有早年的开拓者、传教士被人们纪念,留名路牌。那么,谁是安彤耐特?
那是一个法国女性的名字。
也许,当年开发商投资者的女儿或者太太叫安彤耐特。
在美国,路名就像人名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安彤耐特也许是个随便拣来的名字。
种种解释都不对,都和我的感觉不相吻合,直到那天清晨我去海边散步。
天刚亮,水珠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白茫茫,灰蒙蒙。浓雾切断了视线,天地都变得浑浑噩噩。走到路口,我不由自主地向路牌瞟了一眼,它仍旧直挺挺地立着,脸上露出点点暗绿,字迹模糊。我跨进了路边连着海滩的灌木丛,那条弯弯曲曲被人踩出来的小路--此刻,只剩下萝卜头一截,湿漉漉地躺在我的脚底下。世界像收缩了一样,变得那么狭小,我不得不凭着以往对方向的印象往前走去。走了几步,我猛转身,好像要弃路而逃的样子。一抬眼,视线正巧落在路牌的位置上。只见它离地而起,摇摇晃晃地飘在空中。我看见一个长长的东西,披着白纱,远远地被吊在大树上,若隐若现。我大吃一惊,回头就跑,一路踉踉跄跄奔出树林。眼中的天空、大海和沙滩,都朦朦胧胧地闪着白光,哪里才是归家之路?
我把这个梦告诉先生,我说:“安彤耐特,对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符号,只代表了我们居住的地址。它给我联想,给我情感,尤其是在我拼写或者拼读这十个字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赋有生命。”
先生哈哈大笑,说道:“安彤耐特?你是不是在说玛丽亚·安彤耐特,路易十六的妻子,法国大革命被绞死的那位?”
天!美丽的法国皇后,大革命送她上了断头台。
“难道我们的弄堂以她命名?”我伸长了脖子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他凝神望着我,很不明白的样子。
他哪里知道我肩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被大革命处死的人何以上路牌得到纪念?
先生说:“一个路牌,你为什么大惊小怪?上网查一查当时的开发商就知道啦。”
是的,要弄清真相并不难。
不,不,我摇了摇头。
耳旁,涛声不绝,轰隆隆地冲上来又呜咽咽地退下去。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到底谁是路牌上的安彤耐特,有追究的必要吗?与其大费周折,宁可留下一个问号。也许,在我的心底里,早已认定她就是昔日的法国皇后,她是我记忆中唯一的“安彤耐特”。是不是在昔日学习历史的时候,下意识里我对她的结局和死亡深感同情,而没有得到理性的确认。否则,我怎么会做那么一个奇怪的梦呢。
让那个不谙世事的女人--以暴易暴的牺牲品--寄居在美国的一条弄堂里吧!给她一份同情,给她一份原谅,给她一份安抚和关怀,难道不是我想要的吗?
这时,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难道这就是孤独的结果?我是活糊涂了还是活清醒了?独处,真的能打开心灵之门?
每天早晨,弄堂里尘埃落定,人去巷空,我恢复了与路牌的对话。
老兵的思路
于是,我开始给玛丽亚·安彤耐特讲述弄堂里的故事。
隔壁住着一位二次大战的老兵,七十多岁了,曾随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一带痛打日本鬼子。他叫乔治·杰克逊。老兵家的房子和我们一个模样,四个卧房只住两口子。
第一次和他照面是刚搬来的时候,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后院里拔草,我们两家的花园被一道齐眼高的围墙隔开。他家的后院有一棵高大的苹果树。我听见有人叫了声“Hi”。抬起头来,看见围墙那边站着个老头,递给了我一个塑胶袋,里面是红彤彤的苹果。
乔治,他自我介绍说,“I made your wall”,意思是,我家后院的围墙是他砌的。我听说乔治是我们弄堂里的元老,参加了这片住宅区的开发。他说话的时候,用手掌撑住前额挡太阳,像中国的农民,而不是架太阳眼镜的洋人。“谢谢你,乔治!”我没说完,他已经从围墙上撤了下去。
苹果里面是温馨的故事。先生说,乔治原配太太活着的时候,弄堂里逢年过节、婚丧喜庆都由她来张罗。
他还说,乔治本来可以发财的。复员后,他曾经是建筑承包商,凡是乔治承包的工程,尽可闭上眼睛睡大觉。但是,乔治事必躬亲,雇工不多,生意一直做不大。退休后,他继续做,老了,还亲自动手。他的背驼了、腰弯了,工做得慢了,可是从来不马虎。这是士兵的思路。
乔治说话的声音缓慢厚重,走路也如此,如大象的脚步,每走一步好像都包含了完整和负责的意思。他天天一早出门,我总能在窗口看到他。他开那辆老掉了牙的大卡车,柴油电机“腾腾腾”,声音特别响。车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向他招招手,他总是给我一个点头,表示看到了,然后扬长而去。
有一回,我包了几百个馄饨,装了一盒送去给乔治尝尝。第二天,他来敲门,蓝卡其工作服上沾满了白灰,双手抄在身后,撑着一个快要断了的背脊,喘着粗气对我笑。
“嗨,乔治,馄饨好吃吗?还要不要?”我问道。
他还是笑,笑得脸部皱纹里的白灰纷纷散落。他从背后递给我一个白塑胶口袋。
“什么东西啊,乔治?”
我打开一看,里面两条鲜亮硕大的海鱼,鱼尾巴一晃一晃地还在动呢!
“送给你。”说完,他转身就走,迈着大象般的脚步,又沉又稳地走在绛红色的晚霞里。
先生说,他经常在码头上帮人,是渔夫们的好朋友。他们之间没有现金交易,用最古老的方式,以工换工。这鱼就是当天捕来的。
我们怎么能够白吃乔治的鱼呢?就算他吃了我们一盒馄饨,那值什么钱?物物交换要讲公平。第二天,我赶做了些春卷,又给他送去。乔治开了门,没有请我进屋坐坐。他接过春卷,眉开眼笑,谢了谢。想不到,傍晚时分,他再敲门给我们送来了两只沉甸甸的海螃蟹!我说:“乔治,You don"t have to(你没有必要这样做)。”
“知道,知道。”他点着头嘿嘿地笑,也不进门,双手叠在背后,一转身,一摇一摆地走了。从那以后,每次见到乔治的身影,不知何故,我的眼睛里便出现了两个人,另一个是他那已经辞世的原配,那个古道热肠的老太太。
有些故事是听来的,有些是出自我的想象。圣诞节的礼物,感恩节的会餐,孩子们的生日,结婚纪念日的欢庆,就像项链上的挂件,戒指上的宝石一样灿烂绚丽,有声有色地从别人的记忆中走出来,注入我的心田。我送给乔治一张里程回扣的免费机票,他给了后续的太太去东部旅游。
“你为什么不去呀,乔治?你应该给自己一些假期。”“呵呵,她喜欢旅游,我走不开。”
以后,乔治有了好吃的,常常来敲门,一袋一袋地送给我们,并附上了他的理由:“我太太不爱吃。”我则用中国菜回报他。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对弄堂的不公平,十多户人家,应该每家都送一些。我总是感到她的存在,那位素未谋面的老太太。玛丽亚,你在天堂里应该见过她。她的爱是无条件的,就像母亲爱孩子一样,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便多做了几份,让儿子给邻居送去,请大家尝尝中国风味。
去年冬天,乔治有几个星期没有出门。我以为他想通了,终于和太太双双外出,真为他们高兴。以前乔治从不和她同行,太太出门,他留守家里。
那天,我从超市买菜回来,从车上卸下大包小包的食品,抱在胸前,正往家中走去。忽然,看见乔治坐在家门口的草坪上晒太阳,赶紧把东西送回家,兴冲冲地跑出来和他打招呼。
“乔治,回来啦?”我拍拍他的肩膀问道,“你去哪里玩了?”
他斜眼瞅了我好一会儿,像在看陌生人一样。
我难堪地笑了笑,弯腰凑近问:“乔治,你好吗?”
“I am fine (我没事)。”他一字一吐地说,伴着两声“呵呵”的干笑。这时,我看到,他那陷在眉骨下的眼睛像糊上了一层膜似的,光泽微弱。乔治好像苍老了许多。午后的阳光照在他脸部松弛的肌肉上,一道黑,一道白。
难道出了什么事吗?我的心一沉,眼睛顿时酸涩起来。这位邻居是我所见到的现代人中最清醒、最智慧、最干净的一类。他最应该得到上帝的保佑。
我突然发现乔治的椅子后面靠着两个残疾人支撑架。“出车祸了吗?乔治,你的卡车呢?”
乔治说:“在车库里。我的膝盖废了,换了人造的。”原来,乔治去医院动了手术。
这时,我才明白他那大象般的脚步,为什么走起来那么缓慢而沉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乔治?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乔治摆摆手,吃力地说:“谢谢。”
邻居们议论说,这下好了,乔治也该享享福了。据说,他有丰裕的退休金,他的房子一次付清,不含债务。他是一个没有负担的老人。美国人喜欢把坏事变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