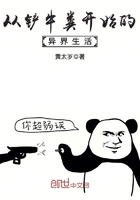淮海在元旦前被判了死刑,程家院门口也不知被谁贴了张宣判书,上面的淮海相片被画了个大红叉叉。枪决之前,程家人可派两个代表去见最后一面,起先说好是孩儿妈和东旗去。东旗只淡淡说一句她不想去看这种戏剧性场面。川南已入预产期,丈夫不许她去。她丈夫现在动不动会对她说:“我看透你们程家人啦!哼!”每当他这样说,川南便收敛哭或闹,像是替程家一大家子赔他不是。最后只有孩儿妈一个去。
院里的人都不知该哭丧脸还是该若无其事。照布告上讲的,那个程淮海百死难赎,死有余辜;除掉如此的恶棍、人民公敌,人们该扬眉吐气。而他毕竟是程家骨肉,人们毕竟听惯了他嘻天哈地,打诨一切,想到就此没了他,心会坠,鼻子会酸。说到底淮海心不那么坏,过年节他总买烟给家里的老厨子呢。院里小保姆在院外受了人欺负,他总帮着打抱不平的。他和警卫兵也混得极好,和他们打球摔跤,存了电影广告全送他们。如今就这么个淮海要被枪决了,多年轻啊,才三十不到五。
孩儿妈忽然决定不去了。她已穿戴好,黑色大“本茨”已敞开门等她。她背上负载着所有人,包括程司令的目光,忽然转身,对大家说:你们让我去,你们不公道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怎么被生下来,从这么点长到这么点,长成个大人,我受不了看他一下子没了。
大家瞠目结舌看着她慢慢蹲下,捂住脸,起初人们以为她在哭,后来见血从两只手缝溢出来。
接下去又是急救,第二天诊断报告来了,孩儿妈已是鼻癌第三期。
不久公安局来人,说他们已调查清楚:程四星已叛逃到香港,程司令的所谓“监外之监”是与法律开玩笑。警察们连前次的外软内硬的“软”也没了,仿佛他们面前赫赫有名、建国元老的程老将军是街头的老流浪汉。
“滚出去!”程司令喊:“给老子滚!”
警察不但不“滚”,并进一步声讨:“身为老党员老干部,目无法纪,搞自己的军事小王国……”
程司令浑身大抖,对他们抡胳膊:“滚!不马上滚我就打电话,叫人来收拾我这院子!我还没死!……”
“中国不是军阀独裁统治!”
“我这里就是军阀独裁!不服不信,试试看,我照样有人有马有枪!逼急了,我拉人上山打游击!就把这话告诉你们头头!告诉登报,明天登报!这就是我程在光说的……”
警察们的吉普毫不气馁地在程老将军的骂声中离去。
老将军在当天夜里被送进医院。他未吃饭,独自坐在院子里,谁劝,他都说他只想静静心,不必管他。他甚至对警卫员也说:过新年了,去玩吧。人们觉得那天晚上他像个顶慈祥的老头儿。他就那样坐在北京的腊月里,直到警卫员发现他头猛往后一栽。
程司令从此就躺在高级干部的特护病房。病房明亮洁净,摆满大棵的龙背竹。上去仔细看,会发现那些郁郁葱葱的绿色生命不是真的。真植物会在每天的一个时辰里与人争气,这样对躺着像植物一样静止的程司令不利。
外间是个会客厅,五张大沙发和地毯都是浅色。孩儿妈端坐在中间的长沙发上,见霜降走进来她抬抬眉闭闭眼。
为着说不清的道理,霜降想来看看老将军。据说他再醒不过来,就这样被人每天灌这个输那个维系着生命,活不多长啦。也许会一直这样活下去,像植物,像百倍地长命于人的树。或许出于好奇心:人怎样变成了树?霜降才来到这间病房的。
霜降对自己连说不怕,一边靠近了病床。当她看见老将军的眼睁着,一眨一眨,东翻西翻时,她还是有些害怕。她甚至想对他笑一笑,像她素来对他那样有点发惧地笑。他眼睛在她脸上稍留,又转向别处,仿佛去好好思考她是谁。他眼睑垂下了,一种羞愧的样子。他对她从未表现过羞愧,不久前他摸霜降的脸蛋,顺脖子往下,她哇一声叫起来,起码蹦开了五尺,说:“首长,您再这样我就再不到您这儿来做活了!”
他吃惊极了,仿佛说:不就摸摸吗?原来你是不可碰的?他由吃惊到气恼,说:你以为我随便让人到我书房来吗?你这个小女子,真有点儿莫名其妙!……
她就那样靠在他写字台边一直哭啊哭啊。她想等泪干了再出门,不然会被人看见。仿佛她有愧她该羞。他不理会她震天动地却无声的哭泣,他还气着呢?她那样多的泪也没让他羞愧。他过几天仍人前人后叫她,大声叫她小懒虫,躲着不干活儿——他书房里的花几天没换水,花瓣落满地毯,也没人打扫。
去年仲夏他要去北戴河疗养,孙管理向他报告随行人员,他说去掉那个随行护士,换霜降去。孙管理一时发蠢,问一句“为什么?”
他答:我喜欢谁就叫谁去。怎么啦?那小女子让我看了顺眼,看了顺眼我血压就不高啦。他仍没有半丝羞愧。
躺在病床上的老将军又一次盯着霜降,一种情深意切的凝视,像他曾经多次命令霜降从浴盆里站起时的那只眼。嗯,好看,怪不得古时人最爱看美人出浴。不要忸怩嘛小女子,为首长服务就是为国家服务,懂不懂?好看好看好看!……他在北戴河也常说这个好看那个好看。太多好看的他顾不上来看霜降了。有两个金头发小女子从早到晚穿着泳衣,他便看她们,看得上下唇啪嗒一声松开。好看的东西就该看进眼里,他理直气壮,他毫不羞愧。
就那么奇怪:仿佛你理直气壮地邪恶,你也能征服人。他就那样征服了霜降(以及霜降之前的女人)。以至霜降怀疑自己错了,不然自己怎会越来越羞愧而老将军却越发理直气壮?……
就是在北戴河吧?老将军的健康再也没见起色。那次的中学生夏令营晚会之后,他就提前结束疗养,起程回北京了。夏令营晚会上,霜降还见到了许多其他知名人士,如作家、演员、歌手。当节目主持人介绍:某某是哪本小说的作者,中学生便长时间鼓掌,而当演员和歌手上台,他们不仅鼓掌,而且跳、叫,喉咙都扯破了。
程老将军是最后一个上台的。他的一身毛料军服熨得挺挺刮刮,白头发梳成很严格的“三七开”,一双新布鞋的牛皮底吱呀作响。他头高仰,目不斜视,当主持人介绍他的名字和职位时,他手闪电一样在头侧一挥,行礼的力度和速度炸响了他几处骨节。但没有任何掌声。中学生们似乎不明白这个老军人干吗出现在这儿,他的出现似乎不合时宜也不合逻辑。嘈嘈切切的议论扬起时,老将军有些不从容了,但毕竟出入大场面多了,他很快稳住自己,换一副风貌,两手将军服袖子一撸,指着下面十四五岁的学生们,亮嗓子道:“小鬼们!细妹子细伢子们!像你们这么大,我已吃了三年红军的南瓜饭了!”
“细妹子细伢子”们静下来,静得叵测,仿佛在捺住性子看老军入怎样逗起他们的胃口,看他怎样察觉自己走错了地方——上这个台上来“说古”。
霜降知道他是不得已这样即兴开头的。照他给学生上“革命传统”课的惯例,他往往从他祖祖辈辈怎样贫穷,旧社会怎样黑暗开始,那样才更有逻辑,更显出他参加革命推翻旧社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那天他一上来便谈起他身上的第一个伤疤:子弹怎样在他皮肉里开花,血怎样流得像匹红布。后来他又怎样在手术无麻醉的剧痛中几番死去活来,再后来伤口怎样化脓生蛆。学生中有人刺耳地倒吸气。
到他讲到长征过草地,他饿得两只耳朵透明,薄如蜡纸,肚子却凸得像面鼓,一敲“嘭嘭嘭”时,下面学生们不安分了,动的,说话的,夸张了声势打哈欠的,终于迫使主持人上台制止老将军的谈兴去了。
“您的故事太精彩了,改天我们专门请您来讲!……”主持人的耳语从麦克风扩散出来:“今天太晚了,考虑到首长的健康……”
“我没事!……”
“这些学生活动了一天,也很疲劳了……”她抓过麦克风对台下:“让我们感谢程老精彩的讲演!”
这次掌声火暴之极,程将军只得离开讲台,步伐别别扭扭地走下来。他军衣兜被个重物坠着,霜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把自制口琴。因为这是个文艺晚会,他提前多天就将这把口琴翻出来,炮弹片制成的琴壳被他拭去锈,露出颇纯的铜色。这把口琴是他五十年前做的,音不准,吹奏者得把握气流。老将军为吹奏一支很短的红军歌练习了许多个早晨,却未得机会表演,甚至连展示它一番的机会也未捞着。
警卫员在搀扶他下台的时候朝霜降看一眼。原来他也懂得老将军此时多么沮丧和挫伤。
待他们离开会场准备启程回疗养院住处时,竟找不着司机了。司机跑去找演员和歌星们签名去了。怪不得学生们那样火急火燎,他们生怕老将军的演讲耽误掉最激动人心的这一刻。学生们尖叫撕打,人仰马翻地热闹。等找回司机,老将军已又累又火,揪住司机前衣襟就要打,被随行的一帮人拽开了。
大黑“本茨”被请求签名的学生堵了,开不出露天会场的门,怎么鸣喇叭也无效。最后人闪出条道,刚要开出,一个中年男人拦住车,两手岔开。
司机把窗玻璃摇下问他什么事。
那人说了自己名字,说自己是个历史教师,读了报上某作家写的关于程司令修建私人游泳池迫使幼儿园搬家的文章,他感到痛苦,既然今天有机会和程司令面对面,请首长回答:那文章是捏造还是事实?
程司令见老师后面跟了一大阵人,包括那些签名或求签名的人,他对司机吼:“死娘啦?还不快关上窗!……”
已有许多手扒到了窗子上,车难以移动。
“回答呀!回答呀!……我们要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