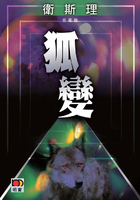九月初的一天,霜降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人的声音,说有人托他带信给她,让她到营门口接应。霜降一路骑车出去,心里巴望别再是那个小赵。小赵自那次在朝鲜面馆遇到她和大江,几番托他在警卫团的熟人带信给霜降,让她在大江面前“美言”他几句,看在他“鞍前马后”保卫过程司令两年的情分上,帮他弄个北京市民户口。信的口气有一点醋意和讥讽:跟你霜降重叙旧情,我是没那份痴心妄想了;既然你霜降已攀上了高枝,啄剩下的果子,也空投给咱救救饥。霜降回信给他,说这事她半点儿忙也帮不上,她与大江仅是主仆关系,连朋友都算不上,千载难逢地出去一趟,既是偶然也是正常。
而营门口站着的却是风尘仆仆的黑瘦小兵,见了她就说自己从云南来。
云南?大江实习的部队就在云南——霜降脑子电一样快地闪一下。
“我送我们副参谋长回来的……”说南方话的小兵说。
“副参谋长?……”霜降想他大约找错了人。
“程大江。”他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封信,封面上写着“烦交霜降”。她从没见过大江的字迹,头次见连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异样了。为什么是我?怎么会是我?……
“他怎么了?”他人呢?他怎么会被人送回来?……
“程副参谋长受伤了——演习的时候出了事故,他的腿炸坏了!派我们几个送他到军总医院的。”小兵说。
那是兆兆工作的医院——霜降脑子里又过一次电讯。
“他伤重不重?”
“重是重,不过没危险。上飞机之前做过一次手术了,今天是第二次手术。”小兵说得很急,离去得也很急。
大江的信不长,只告诉霜降他可能会残废,想尽快见她。还说到兆兆在闻知他受伤的消息后正要动身去日本,去参加一个医科大学的合作项目,他劝她不要等他。他被送到军总医院时,兆兆已经走了。信最后叫霜降千万对他家里封锁消息,他怕父亲吃不消这个消息,也怕一家人到医院去吆五喝六。
霜降第二天下午到了医院。大江睡着了,脸色还好,人却像老了一大截。那是单人病房,白色铁床置于屋中央,一个向来神气活现的大江一下显得那样无依无助。
霜降发现床周围没有一把椅子。的确没人来看望过他。
她从未见过一个男性睡着的模样,因此这一会儿的打量使她感到有些神圣。他原来是这样睡的,嘴抿得那样紧,像一张从来不和父亲耍贫嘴、不和母亲胡应付、不和女孩子们卖俏皮的嘴。很难想象这样的嘴会不负责任不计后果地说:“霜降我喜欢你。”它那样沉默寡言,即便含有一个“爱”字,也该是无声的。
它果真含有一个无声的爱吗?对她这个女佣?别扯了。这张嘴即便启开向她倾吐出一淘箩爱字,她也不会信。它启开的第一个动作将是斜着一边嘴角的笑,那笑从一开始就让霜降警觉,对做热恋梦单恋失恋梦的自己一再喊“醒醒!”
假如真有一天,它向她启开,告诉她他爱她,接下去告诉她他要她。明知那爱是那要的谎花,或那要是那爱的苦果,她也会给。怎么办呢?她爱他。他要,她给,就算够美满了。
这张冷峻紧抿的嘴吻过兆兆,一定长长地、心笃意定地吻过她,那样的吻会使兆兆和他都感到长久、完满、彻底的相互拥有。那么吻过之后呢?他心里可还有一个小极了的角落?那小极了的角落像是人塞行李箱或填仓库,塞填得再满也难免留下的夹角或死角,他若就把那角落给她,她也要。
她眼睛胀起来。她头一次这样哭,泪水持续地蓄积,蓄积了那样长久那样满却不立刻流下来,因为她心里并没有悲伤推动它们流下,有的只是一种复杂的感动。为自己和大江无望燃烧却不肯泯灭的那点情谊。
她仰起脸,似乎想把眼泪倒灌回心里,却不行,它们成熟了,它们自己坠落了。她就这样和自己的眼泪较劲,她将它们仰回去,它们寻着别的途径再流出来。强烈的抵触竟使那饮泣愈来愈难以扼制。她想,连自己的哭也变得这样复杂。她不知它还算不算哭,正如她的笑,是否还有笑原本的含意。她在这以泪洗面的时刻发现她哭出了痛快恰等于她时常笑出了难受;原来它们是可以混淆的,像好孬、美丑、善恶等概念都可以不相互对立,都可以混淆。在程家的院子里,在她这两年中,所有她认为古传的、固有的、长辈们教诲的众观念都被搅拌得你掺进我我掺进你,辨不出反正、是非了。
她的手被捏住了。伏脸,见大江正看着她。她急忙抽手去擦泪。
“哭那么久!”他说。他看了那么久,玩味了那么久。他说他的伤不值她那么多泪。他又一次拉她手,拉得她只得推床边坐下。“哎呀,小姑娘啊小姑娘!”他吟唱一样叹道。
霜降问他的手术。疼得厉害吗?刚下手术台还好,夜里不行了,我骂了一夜。现在呢?你撩开被看看,敢吗?
霜降看见一条白得耀眼的腿,一股药味掖在被子下。那条病员裤被剪掉了一条裤腿。
她忽然意识到她不该这样鲁莽地撩开被子。大江大笑了:“怕呢,还是难为情,脸红了!你可真是个小小姑娘!”
霜降急着转话题,说刚才一个护士硬不让进。今天不是探视日。那护士凶得很!
“后来你怎么进来了?”
“就那样做贼一样进来了,她坐的地方能看守走廊两头。我听她接电话,赶紧贴墙溜过来。”霜降说。现在的笑可算作真正的笑。
大江说她们对他一样凶,要想她们不凶第一,得说他爸是谁,第二,女朋友叫兆兆。不然,她们见的大头兵升成的官太多了。
“兆兆没跟人打个招呼,要他们照顾你好些?”霜降问。
“她打了招呼我还敢扯开嗓子骂人吗?”
“你骂什么?”
“什么都骂,一开口就八辈以上!大头兵受伤都要骂,这是规矩。跟新娘哭嫁,寡妇哭坟一样,规矩。”他笑得一嘴牙又全露出来。一向的,他这笑比所有人的笑都饱满。他恢复了霜降头次见的那个饶舌顽皮的大江。
“总有一天她们会晓得你是兆兆的男朋友:哎呀,那个乱骂人的大头兵原来是赵大夫的男朋友!……”霜降觉得自己快要恢复成最初的自己了。尽管有个兆兆。
“她们恐怕永远不会知道了。等兆兆三个月回来,我们说不定各归各了!”他说。
霜降很高兴自己的心没跳乱。没这个兆兆,会有另一个兆兆,哪个兆兆都没了,也轮不上你霜降。轮不上你,心乱也白乱,不如安分守着他给的夹角死角、无论多小的一个角落。你命里该的,就是那个谁也占不去,想填也填不满的小极了的角落。
大江以为霜降在专注听他讲兆兆。他一个劲肯定兆兆的长处,说她从不否认自己的优越感,为什么否认呢,她该优越,她不像程家子弟那样空洞地优越、不学无术地优越。而正因为她太优越她学不会爱别人。爱情是种双方都表示谦恭才能产生的感情。“对吧?”他问霜降。
霜降赶紧点头,实际并没真听懂他。
“我想我和兆兆不应该结婚……”他很没主意似的看看霜降。手一直握着她手。
“你们不是十月就举行婚礼吗?”全院人都在传说程司令准备订饭店,趁机请请平日不太走动的上级和同僚。讨厌铺张的程司令这辈子是头一次和最后一次铺张。
“兆兆告诉我,她可能留在日本。不留,十月她也不会为结婚回来的。她对我没那么热。”大江心平气和地说。
“那你对她呢?”霜降急问。似乎不是急自己而是急大江,有点为他抱不平。你这么好看这么有前途这么要强这么不凡夫俗子,她凭什么不对你热?她不热,让她有一天也剩成川南,末了捡个姨里姨娘的小行政干部也嫁了,还见他眼色行动举止。
“我对她?”大江想一会儿:“她是个值得人尊重的女人。别看她平时小孩儿脾气,进了病房像男人一样果断沉着,看了就让人尊敬。但结婚是男人和女人的事,需要热,说丑些,需要热去刺激荷尔蒙。人说到底还是动物。动物间的异性相吸是很原始,也很美的。因为它没有功利性,也不掺有社会因素。”
霜降想,他的意思是他对我有这种热吗?噢,大江,别来惹我。我有那个角落就挺好。有那热而没有尊重一样是不成的,我知道。你更知道,不然你为什么握着我的手从来不给我解释呢?我们说点别的吧。霜降问他要不要喝水,她带来了他喜欢的可口可乐。
她将他床头摇得高些,一面回答大江对家里人的提问。你妈?她还好,前阵流了次鼻血,现在她在看一个新医生。川南胖了,怀孕嘛。东旗不常回来,回来总是为她的大猫。川南把她的猫打了。
“老样子,世界上竟有这么无聊的一帮人!”大江笑着恼,笑着愁。“不是听说六嫂出事了吗?怎么个前后?”霜降生怕他把她也归到无聊的“那帮人”里,便简短讲了经过:六嫂有天到学校直接领走孩子,三天后程司令叫人把被藏的俩孩子找了回来。川南从此找六嫂的行踪,不久六嫂就被警察抓了。罪名是跟外国人非法同居。霜降没加评论和形容,没说当时程家人怎样倾巢出动,到宾馆去看被“捉双”了的六嫂。六嫂披头散发,口红抹得满脸,浓妆融得那张标致脸蛋成了油画调色盘。东旗的话:是个地道的妓女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