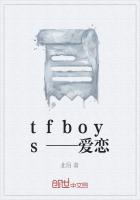镇上的茶楼酒楼前挂了红灯贴了门画守卫着紧闭的门框,街上寥寥无几的人烟与樊城此时的热闹不可相提并论,玉清河畔不见了往日嬉戏的虫鸟,片片的雪花在这一寂静中翩然而落。
文工团后院的大门铁链绕了好几个轮回,上了锁,门画上贴了张纸条,“芝茹姐,我去监狱陪乐大哥了,新年快乐”,这字迹未被雪花浸湿,似乎依旧透着余温。她回首对罗顺笑了笑,回家吧!
客厅里,博文单手扶撑在沙发椅背上,悠然自得地接听着电话,不时“嗯”两声,见她回了来,一句“年后我会安排”,没有结束语,“啪”地一声挂了。
不敢过问是不是林太太的电话,不敢过问是不是送走了张晋良,她浅浅一笑,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心无旁骛,安静地依靠着他,看窗外繁繁点点潇潇而下。
他抚着她的肩,问怎么回来了?她回答说,扑了空,那丫头找心爱的人去了。他开怀地捏了捏她的下颚,说既然如此,今天,她可是彻彻底底属于他了,谁也不能陪?她往他怀里钻了钻,笑了。
出门的片刻,常妈听罗顺说少奶奶没有吃早餐,非拦着她吃些营养麦片又要逼着她喝牛奶。她胃口奇差,刚吞咽了两口又吐了出来,很是辛苦难受的样子。他在一旁看得心痛极了,让常妈下次备些合胃口的。她解释说,不怪常妈,是自己的原因。他倒又慌张地说要去看医生,她忙制止了,不用麻烦,开服药,吃过便会无碍。
该怎么跟他说呢?
他知道了肯定会眼笑眉飞,可他更会忧心忧虑,不仅仅担心她,还要牵挂另外一个。
蜷缩在后车排,她枕靠在他的怀里,幽幽的神色几乎脱口而出,却忍了住,直到听到他的声音。
“晚茹,去南洋的商船封航了,林家二月中旬有货船去东瀛,你随常妈过了正月先去昌平住些日子,母亲会安排好你的一切。”
去昌平,去见林太太,去跟林家上上下下几百号陌生人一起生活。上次,林家老太爷们已经对她有诸多不满…
身子不自觉一震,这林家长辈有谁能容得下她?
似乎觉察出她的惊恐,他安慰着说,“老家来了好多次电话,母亲她很担心,怕我这段时间工作太忙照顾不周,亏待了你”
林太太不该挂念自己的,念叨的似乎应该是张家小姐。
她疑惑了,抬起额头,映入眼帘的是他放松了紧张的眉宇,林家至少可以让他安心,不是吗?她轻轻“嗯”了一声。
车在崇山峻岭前停了住,四周一片洁白,天地浑然一色,一草一木,一枝一叶都凝聚着洁白无瑕的晶体,如披银叠叠,似挂珠串串,山风拂荡,盈盈作响,犹如进入了琉璃世界仙山琼阁。
烟峰山?!
虽来过一次,这里的一切早已铭记心底,风雨摇曳的白杨树,青色的鹅卵石石阶,寒水寺岔路口的凉亭,还有张晋良喊过她的“宛莹”,还有她毫不留情的一巴掌响声…
迎着白色天阶缓缓而下的行人,心弦顿时弯成了整装待发的猎弓,箭头不是指向他人却是自己。
她挽着他的胳膊,低垂着头,直盯着脚下的白路,随着他的步子向前,终牢牢地钉在了石板上。明知是偶遇,仍是微微一愣,她撩起眼帘,正好与他的眸子相撞,默默地装着不经意,她唯有嫣然一笑。
他简洁地问候道,“走了?”
张晋良略微醉熏,沉沉地“嗯”了一声,不愿多说。
他亦没有再问。
两人似乎很是默契,如此擦肩而过,只听得最后的异口同声,“明年见”
原来是淡淡地。
在博文的面前,他待自己只能如浮云流水,淡淡地。
淡淡地遇见。
淡淡地分离。
那些惊慌失措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脑袋瞬间如这茫然的白色,空洞又装不下任何风景。
她只知道寒水寺的匾额很是简陋粗糙,阁楼大殿是抑郁的灰色,袅袅升燃的香火透着殿门飘荡出来,缭绕在石墓周围,粉色的腊梅傲雪盛放,与墓碑前黄色的菊花相互辉映,碑上飘逸的宋体字写着“谢婉莹之墓”。
沉默地哀悼了片刻,他牵着她的手如此离开了,未有一句问候,一句短小的语言,哪怕仅仅是一次恋恋不舍的回眸。
重新坐在车上,她才回过神。
刚才是去拜祭宛莹了?
依稀记得那个坟墓是用千块石头堆积的,一层层环绕而上,每一层种植了绿色常青的花草,在冰封的天气开着不败的紫蓝色。
在寺庙是不是烧过香,捐过公德?是不是对着她说了几句知心贴心的话?
她全然没有记忆,甚至连博文当时的表情都是模糊一片,只觉得一切竟是这般突然,突然地来到了烟峰山,见了他,又见了她,又突然地分手离开。
他抚着她两鬓的发丝,挽至耳后,柔声问“怎么不说话?”
她把头深埋在他的腿上,“博文,我似乎只认识了你半年,若是有一天我们分开了,我不知道这半年的记忆,够自己回味多久?”
他的手突然顿住了,“最后一次来这里。”
以为她是为来看宛莹生了气。
“不是,只是觉得弹指一挥间,什么都没记住,什么最终都会成为遗忘。”她起了身,怔怔地盯着他,“博文,我喜欢大海,喜欢听海浪的潮起潮涌,若是有一天,我不在这人世了…”
很不愿她继续说下去,他猛然堵住了她的嘴角。
良久。
他在她的耳边如轻风般述说,“我会在园子的荷花池下建一座大大的冰窖,每天晚上陪着你,听池水的静谧”
不是埋入三尺土地化为乌有。
不是随风散尽找不出一丝痕迹。
他会继续伴着她。
她忽然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