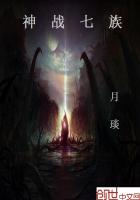“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来了。”
朱成璧眉心微蹙,放下手里的绣样,只拢一拢身上的锦被道:“这几日皇后来得越发勤快。”
竹息温然笑道:“皇后娘娘有心,况且,成嫔有孕,安小仪荣宠日上,她们二位撒娇撒痴正斗得厉害,皇后倒也怠懒去计较,却一门心思往这儿跑呢!”
朱成璧轻轻一嗤:“安小仪这么快就复宠了,又晋了一级位分,可见也是个抓尖要强、不肯低头的。让皇后进来吧,外面风大。”
竹息抿一抿嘴,朝竹语微微示意,收起床头的几件婴儿衣裳与针线,似是不经意道:“成嫔与皇后亲近,安小仪与娴贵妃亲近,如今她们两个争风吃醋,皇后与娴贵妃倒好像没事一样、只顾着看热闹,只怕这出戏,落在旁人眼里,又是另一回事了。”
竹息语音刚落,朱柔则扶着徵蓉的手翩然入殿,着一袭家常浅月白色罗裙,微微一福:“母后万福金安!”
朱成璧微微支起身子,蓄着宁和的笑意道:“这么晚了还特意过来?”
朱柔则从徵蓉手中取过一只描金雕花食盒,笑吟吟道:“儿臣再三问过了顾太医的意思,拿了红枣、参须滚了乌鸡熬汤,最滋阴养颜,又能补血益气。”
朱成璧点一点头:“你有心了。”
朱柔则取了一只素三彩花口碗,舀了半碗汤,先用银汤匙试过了,又亲自饮了几口,确认无碍后,方恭敬端到了朱成璧床边。
朱成璧微露赞许之色:“如今看来,你行事愈发的妥帖了。”一语未必,清风拂窗而入,朱柔则裙袂翩飞间,似有淡淡的香味逸散开。
朱成璧皱一皱眉头,只觉得心里隐隐有些发闷,问道:“是什么味道?”
朱柔则忙道:“是御膳房的金司药研制的九匀千步香,香若空谷幽兰,还是端妃推荐给儿臣使用的。”
朱成璧淡淡哦了一声,就着朱柔则的手,一口一口饮完了那碗汤。
入夜,朱成璧辗转反侧,只觉得心里一阵一阵闷得难受,连那清水一般的月光都是灼人的疼痛,迷蒙间,窗外婆娑的树影在掐金银线的云纱帐上投落,变幻莫测,如鬼怪的魅影。
朱成璧难以入眠,索性定定盯着那树影看,恍惚间,似乎看到了昭宪太后寒若冰霜的面容,她歪倒在这张床榻上,恨恨瞪向自己,是了,就是在这里,她吐血而亡,夏氏一族的富贵荣华恰如朱楼坍塌、灰飞烟灭;怔忪的瞬间,朱成璧又似乎看到了夏梦娴狠狠逼视自己的神情,她的目光那样尖锐冷冽,似乎要将自己贯穿。
许是看得久了,想得久了,迷迷糊糊之间,朱成璧似乎沉沉睡去,却又觉得周身凉风不断。待到睁眼一瞧,不由是大惊失色,自己,竟然是在永巷行走,只着一身单薄的藤紫色长裙,裙袂微微飘着,如逐风的紫蝴蝶,一匹青丝则柔顺地铺散及腰,如藤萝瀑布。永巷的夜那样宁静,路却又那样漫长,几乎望不到终点。
朱成璧下意识抱紧双臂,缓缓走着,且惊且疑地望向四周,却有一队着白色宫装的宫女一路而来,朱成璧疑惑地停下脚步,想要唤住她们问一究竟。话未出口,朱成璧却又震惊地捂住自己的嘴,为首提着宫灯的宫女,正是废后夏梦娴,后头的则是玉厄夫人林若瑄,密贵嫔宋素琬,妍贵嫔韩雅洁,睦嫔姜敏仪……那样长的队伍,逶迤似从浓云薄雾中行进而出,不寻一丝声音,只安静地兀自行走。朱成璧惊惧失色,紧紧靠在墙上,却有什么在不断撕扯自己,那样真切的痛苦,仿佛一寸一寸割在肌肤。
朱成璧低头一看,不知何时,红墙之中伸出无数血淋淋的手,紧紧抓住自己,那藤紫色的长裙已被染得鲜红,朱成璧挣扎着,却又看到夏梦娴径直向自己走来,目光黑洞洞地幽深,她倏然开口,声音若钢刀一般生生地剜向自己:“朱成璧,今时今日,贵为太后,是否格外得意?”
朱成璧惊恐交加,只竭力不去看夏梦娴惨白的面容,压着颤抖的嗓音道:“很好!夏梦娴!你阴魂不散多年,如今托梦给哀家是要做什么!”
玉厄夫人“咯”的一笑,缓缓转至朱成璧面前,端着一只碧玉酒杯,粉面含春、玉颈如雪:“你赐我的甘州青真当是甘冽,你不如也尝一尝,也好知道当日我失去父兄,在宓秀宫是如何孤苦伶仃地等着被人赐死。”
妍贵嫔不知何时,已悠然立于朱成璧身旁,她靠的那样近,近得连咽喉处渗出的鲜血的血腥气都那样真实,妍贵嫔的笑意空洞:“你有两个孩子,如今又有了孩子,为什么我就不能有孩子?”
朱成璧极力避开妍贵嫔狠烈欲噬人的眸光:“你的孩子不死,哀家就得死!是你技不如人!你没了孩子,自去向夏梦娴诉说!”
妍贵嫔淡淡微笑,面上的哀伤如积聚数年不得消融的坚冰,她缓缓抚摸着朱成璧微有隆起的腹部,笑意深深:“这个孩子不能生下来,他的命太硬,已经克死了那样多的人,更会克死亲生父母,除非……”妍贵嫔杏眼微扬,一字一顿冷冷道,“你先克死他。”
朱成璧一愣,妍贵嫔手里赫然握着一支白羽利箭,电光火石之间,狠狠刺向朱成璧的腹部。
“不要!”朱成璧猛地从床上坐起,大口大口地喘气,一丝剧痛从腹部猛地冲入四肢,那样尖锐的痛楚,自己仿佛是被一把锋锐的刀厉厉划过,朱成璧双手颤得厉害,她猛然掀开锦被,月华流转之下,一滩鲜血,正慢慢蜿蜒而开,闻声赶来的竹息与竹语亦是大骇。
朱成璧怔怔地望着面前的鲜血,只觉得心头有一个沉重的念头缓缓碾过,直到那颗本就千疮百孔的心面目全非。
朱成璧机械地转头,望着竹息,从她的眼里看到了从所未有的震惊与惶恐。
朱成璧双唇微颤,轻轻吐出几个字:“新疾旧病,复发……”
语毕,朱成璧的身子虚弱地如枝头上瑟瑟的黄叶,软软地倒了下去。
半昏半醒之间,只觉得浑身上下是百般的疼痛,耳边乱糟糟的一团,只听见有人喊着“掐人中,掐人中”,又有人喊着“参片,参片”,浑浑噩噩间,有人舀了一勺又一勺苦涩的汤药,从自己嘴里灌入,那样苦,吊得整个胃都紧了起来,朱成璧一口一口呕出,那人却又倔强地一勺一勺灌入。蓦的,却似有温热的液体落在自己面上,那人一句一句地说着“我不该逼你”。是谁?朱成璧已无力去想,只想永远地睡下去,不愿再留在这朱墙红锁的宫里。
即便走到如今这一步,即便再位高权重,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甚至,痛苦加身,远胜于彼时摄六宫之事的时候。
朱成璧紧紧合着双眼,只觉得太累太累,累到不愿去想,甚至连从前那仅剩的美好时光都不愿再想了。
整整两天两夜,朱成璧才醒转过来,彼时正是午后的时光,奕渮静静地趴在床头,许久不见,他仿佛消瘦了不少,唇上胡子拉碴,让人心生怜惜又忍不住好笑,他曾是那样玉树临风的男子,竟也有如今这样狼狈不堪的时候。
朱成璧微微合起双目,下意识摸一摸自己的腹部,这一摸,却如同被电光劈中,心里瞬间一疼,几乎是要滴血断筋的痛到极点,朱成璧直挺挺地坐起来,奕渮也一下子惊醒过来,眼里满是血丝,且惊且喜地望着她。
“奕渮……”朱成璧怔怔地望着奕渮,眼里满是不可置信与剧烈的痛楚,喃喃道,“我们的孩子……”
奕渮心里一酸,极力收住眼角泛起的泪水,将朱成璧拥入怀中:“没关系,没关系……”
朱成璧紧紧抓着奕渮单薄的衣裳,整腔心肺里都是狂热的伤心欲绝与痛不欲生,几乎是要嚎啕大哭:“我的孩子!”
竹息与竹语匆匆入殿,眼见此情此景,亦是免不了暗暗垂泪。
奕渮拥着朱成璧,只觉得一颗心沉入湖底,几乎再也收不住了,须臾,他轻轻转过朱成璧满面泪痕的脸,用力握着她的手,一字一顿道:“璧儿,你别哭,你知道吗,徐徽音没了,她是前天晚上走的。”
朱成璧一怔,只定定望着奕渮,奕渮低低道:“璧儿,她走的时候,很安详,她跟我说,希望我与你,都好好的,她自己被误了一生,她不想你跟我也是。璧儿,你昏过去两天两夜,我好害怕,好害怕你也会离我而去。我不该逼你,你身子那样虚弱,怎能怀着孩子?”
朱成璧眼中的泪水再度汹涌而出,想起怀着孩子的时候,常常想着,这个孩子,会是更像自己多些,还是更像奕渮多些。虽然,自己完全被架空了权力、对朝政不能置之一词,虽然,奕渮极少来颐宁宫看望自己,虽然,想起当时太极殿的场景依然会难过、会落泪。但是,那些已经不重要了,自己一辈子都在谋算、都在疲于应对,为何不能好好静下心来,抚养肚子的孩子呢?
但是,即便自己欲平静下来,即便自己再如何小心翼翼,孩子,依然是没了。
朱成璧缓缓抬起双眸,泪眼朦胧间,连午后温润的阳光都是寒霜一样清冷决绝的颜色,她突然明白,自己走到如今这一步,都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累累的报应。
所谓报应不爽,直到这一日,才真正正正是明白了,痛彻心扉地明白了。
朱成璧伏在奕渮肩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