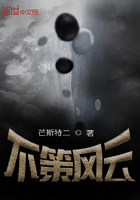或许早该预料到会有一场暴风雨的,画画的生活麻木而疲倦,我们每天像机器一样超负荷的工作着,画画,画画,画画,除了它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的脸上出现一丝欢乐抑或悲伤,如果这样一直下去可能在日后我就不会对它充满辛酸的回忆了,我只能说在所有人的精力都处在临界点的时候,安瑞一脚踹过来,这一脚不仅使我们麻痹的心恢复了知觉,而且大家都自虐似的纵容着他疯狂的举动,我们好似一群即将归西的老人,在咽气之前一道炽热的闪电打过来,不得不背上行囊忍痛活下去。
以前衷爱的素描被安瑞当着全班的面撕得粉碎:“这都是一些什么垃圾书啊你们就瞎买,这书上画的还没有你们自己的水平呢,以后再买参考书的话过一下脑子,概念,概念,都******概念。”
他反复强调着概念与深入,局部与整体,可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概念,如何才能深入。他的脾气随着考试的到来一天天急躁起来,与此同时我们的疲惫也是无法掩盖的,特别是早上五点半画速写的时候,所有的人脸上都带着熬夜的血丝和一脸的委屈,联考就在前方悄无声息的向我们走来让我们这群毫无准备的战士如何面对?作为军师的安瑞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来振奋军心,而他仅用了一招便降服了所有的人,摔画板。
画室里女生偏多,而三位主讲老师都是男的,平日里偶尔偷懒偶尔趁他们不在出去他们都不太计较,况且都是年龄差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有些事他们看见了也当没看见了。而那一天安瑞显然觉得自己的默许有些过分,他说,“你们女孩子没事就别老是来请假,来不来就肚子疼,你们周期那么短吗?画画不是给我看的,考学是自己的事,以后在我的课上最多休息二十分钟,休息完了赶紧给我回来画画。”他说完就走出了画室,我和可心没怎么注意,继续对着前面棱角分明的男青年写生,不一会他又回来了,边晃悠边说,“今天以后要好好画画,我想了一个很好的惩罚制度,从这一张画开始实施。”
“什么制度啊?”有人问。
“画完了就知道了。”他说。
那天我大胆尝试了另一种绘画方法,和色彩构成一样从一个局部开始入手,第二节课结束后我终于画好了模特的左眼,放到远处看还算满意,顾不上休息便开始着手画另一只,直到快下午放学时我的画也仅完成了一双眼和半个鼻子,这没有什么,画画需要时间和耐心。
安瑞开始一组组的检查每个人的作品,当时我在中间的一组,安瑞没过来时大家仍有时间默不作声的画,像往常一样,他把整组的画都靠在墙上,一张一张的点评,我在余光里看到那一组围成一个圈,安瑞在中间指指点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画能被他举起来当成典范说给大家,哪怕是某个点的错误也好,因为你不知道他一针见血的字眼对我们这种不开窍的脑袋有多重要,只要他稍微给点建议,就能使在下一张画里少浪费一些不必要的时间,我们慢慢的等待着,等待着第一组讲完他来我们这一组。
忽然,一声巨响从旁边传来,我们纷纷扭过头去,在人群的缝隙里,两块破碎的画板扔在地上,还没来得及多想,又是一声,这下我们明白了,他折断了部分人的画板,接着又是一声,两声,第一组一共碎了四块画板。屋子里安静极了,除去第一组其他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们默默地坐在原地不敢有别的动静,他就像一头残暴的狮子,而我们就是他手中可怜的小猎物,不一会他走了过来,笑眯眯的看着墙面已摆好的二十张画板,点点头,“你们这组要比前一组好很多啊,”他说。然后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回了肚子里听他一张张的讲,我站在人群的后面,自己的画还没完成,如果是以前在同样的时间里我肯定也画完了,可是画完之后他总是说不够深入,我想今天会好些了吧。
“整体的概念很重要,考试时只要把大的层次表达出来,那些小细节稍微处理一下就行,怕的就是局部,太局部,和周围的没有一点关系,”他说着拿起了我的画板,“这是谁的?”他环顾一下四周,问道。
“我的,”我小声的说,举起了手,同学们纷纷朝后向我看过来,然后又转身回去看那张画。
“怎么跟你说的?”他问,“你下午干什么去了只画了这么一双眼睛?你以为你画的很不错吧。”我不敢说话,其实我很害怕跟他讲,讲我不懂,我不知道该怎么画,我不知道什么是整体什么是局部,怎样才是不概念,每一张画我都在随着大规律摸索,但结果总是差强人意。他看着我低头没说话把画板摔在了一边,那边只有两个画板,那是班上一对小甜蜜旷课出去玩只铺了一层颜色留在那里的,安瑞对此特别生气,他们的画板必断无疑,而我的放在他们中间也会和它们一起断的吧,要不他怎么会把它扔在了那一堆里而不是和别的一样靠在一边呢?
我呆呆的站着,心突突的紧张起来,害怕他讲完,害怕他讲完后会蹂躏我的画板,我感觉胸口有一样东西在紧紧的堵着使我喘不过气来,我看着他在讲完后放下最后一张画转过身来看着那堆在一起的三张画板更加紧张起来,“和前边那组一样,”他说,从身边拖过来一把椅子并把它放倒,他过来了,他拿着我的画板搭在椅子的横面上,另一边靠着地板,我感到心都要跳出来了,“哐”的一声心也碎了,他坚硬的军旅靴子把它踩成了两半,我再也控制不住,穿过杂乱甬道跑到了宿舍里。
我趴在床上不住的颤抖,那一幕不断地重复着,我在努力了我只能做到那个程度了,可天知道为什么我总达不到老师的要求,我不喜欢画画,我讨厌画画,我尽力了!
我胡乱想了一会,努力地想等调整好情绪就去再买一块画板回来,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那颤栗的心慌,我抱起枕头蜷缩在墙角,把被子盖到了双腿上随手拿起一本书,那是姐的摇滚心灵史,我快速的翻了几页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可我一句话也看不下去,我想珍珍一天到晚把它当宝贝似的捧在手中肯定有一定的价值,于是干脆打电话给她好了,想到那,我已经拿出手机拨了过去,“小诺是吧,找你姐?”竟然是孟勇的声音。
“恩,我找她,”我说。
“有什么事啊?”他问。
“找我姐,我姐,珍珍,珍珍,珍珍,”我冲着手机大喊,我可没有心思再和他贫嘴。
“小诺,怎么了?”姐马上接了电话。
“什么都别问,”我匆忙的堵住了她的嘴,我怕她问起我学习的情况,那样事情就又会转到画板上来,“给我推荐几首歌吧,我累了,需要东西支撑一下。”
“好啊,”她说,“歌我有的是,你等着,我现在就放给你听,Gala《追梦赤子心》。”
我在电话着头等着,没一会,一阵清澈的吉他声传来,接着典型的英伦唱腔想起来,“不,能来点别的吗?”我说,“我不想要那种阴柔的满是女人味的声音,我想要一些积极向上催人上进的东西,”我想我都快哭出来了。
“你继续往下听啊,”她没有停止,我扔下手机开了免提,忽然哭了出来。
“虽然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那个主唱在顾及优美旋律的同时近乎呐喊似地唱出了对梦想的追求,“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说。
我被他深深地震撼了,最后那几句高亢的嗓音将“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直到变老。”径直的插入我颤动不已的心脏,激起了我心灵深处最后的一丝愿望和激情。
“其实你知道我总是喜欢听摇滚听的是什么吗?”她说。
“是什么?”我问。
“是一种精神,摇滚精神,是一种不怕辛苦,永不妥协的生活态度。即使所有人都在沉沦,自己也要坚强,即使活在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世界里,仍不放弃对美好的渴望,即使身在肮脏的环境里,也要开出美丽的花来。”
“我懂了,”我说。
我下载了那首歌,听着它跑出画室去旁边的商店里买了新的画板,回来后翻开床头那久久未动的两本书认真的读起来,关于音乐,关于摇滚,关于梦想。
其实集训那段日子里陪伴我的不仅仅是姐推荐的一些歌曲,最主要的还有佳佳,我们在深夜里长时间的通电话,他总是不厌其烦的陪我聊天,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我总觉得自己很任性,那时他在实习,实习能做什么轻松的工作啊?他一天到晚累的不行半夜还得耐着性子安慰我这个急躁的考生,我们无所不谈从天南扯到地北,有一次不知怎的说起了韩剧《蓝色生死恋》,我说我没看过,听别人说挺好的,他说他也没看完,不过挺感人的,里面有个人说要在死后做一棵树,因为树一旦种在一个地方以后就不会换地方了,这样就不会和家人分开了。我问他,那你死了想做什啊?他想了一会说,做个工程师吧,我挺向往这个职业的,我说要是我的话,我就做一块石头,就在湖边静静地躺着,无所谓悲喜,只是单纯的存在着多好,他说,要是你做一块石头,我当一个工程师的话,我就在湖边把你捡回去,把你当宝贝,我想着一个人一辈子和一块石头呆在一起就哭笑不得,他可能以为我没听到又说,把你当宝贝。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里,他的话就像一缕阳光,照亮了心中压抑的阴霾。
还有一次班上的女生买了好多毛线趁着下课的空当回宿舍织围巾,我们都知道那些围巾是要送给心仪的男生的,我看着她们买的花花绿绿的毛线也想给他织一条,他以为我在开玩笑就说好啊,天冷了正好我缺一条呢,而正当我决定挤着时间去市场挑毛线时,他严肃的说,不行,一个人在外边考学首先就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担心我,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没有跟风和大家一起忙手工,其实我知道的,他不想浪费我的课余时间,那仅有的一点空隙是用来休息的。可爱的人儿,你就是天使,带着慈爱和善良的翅膀来到人间,给孤独痛苦的心带来春天般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