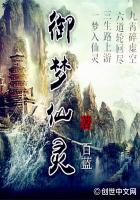刘保直直瞅着她,虽是不说话异常安静,可是一双眸子却透着疑惑之色,月琴撇了一眼月隐怀中的刘浩,不安上前一步:“贵人还是最后看一眼小皇子吧。”
她侧过身去,狠狠闭眼,叹道:“走吧。”只觉体内力气全部瞬间抽离。
玉儿示意月琴走,月隐泪眼迷离瞅着她,泣泣唤道:“贵人,您不看看小皇子,将来指不定没有机会看了。”
她无力坐到台阶上,看一眼又如何?想起母亲送别时,曾经也是不忍再送的模样,突然间更深刻理解了那不舍,却又强压不舍的感受。
玉儿不安扶着她,又瞅了一眼月隐怀中的刘浩,上前将刘浩搂在怀里,一想到母子分离,即便是在这宫里,可是许多事就在转眼之间,正如月隐讲的,将来指不定没有机会了,瞅着她盈盈含泪,却又知道她心中所想,失声道:“小姐,即便您不要伤离别,怕舍不得小皇子,可——您还是看一眼吧。”
她心下微酸,将头靠在了旁边的石柱上,闭眼眼泪落下,无力道:“走吧。”
玉儿咬了咬下唇最后做罢,将刘浩放入月隐怀中,这个时候熟睡的刘浩醒了过来,一双灵动的眸子来回在玉儿脸上瞅,突然呵呵一笑起来。
月隐将浩儿抱正,浩儿恍然不晓世事,抓着月隐的发梢玩耍,而刘保在月琴怀里,却突然瞅着她唤:“娘。”她微怔,瞅了一眼刘保,就见刘保直直瞅着她,似乎已经瞅了她许久,又听刘保在唤,“娘。”
她拭掉眼泪,摆了摆手:“走吧。”
刘保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突然:“哇——。”的大哭起来,嘴里直唤,“娘——娘。”
谁也没想到刘保会如此,玉儿瞅着刘浩不安道:“你们还是快走吧。”说罢过来掺扶她,刘浩也不知是听到刘保大哭,还是因为也感觉到了什么,突然也哇的大哭起来。
月琴与月隐不安互望一眼,遂后屈礼:“贵人保重。”她随玉儿往殿内走去,直到哭声越来越远,似乎已经到了宫门口时,她停下了步子。
玉儿见她不动,只伴在她身侧不语,渐渐哭声消失在城墙的另一头,她只觉疲惫不堪,转而坐到一侧红木椅上,叹道:“太后临终前是思子不见子,如今我是有子不在旁。”玉儿过来不安搂着她,她将头靠在玉儿身上,闭眼失声道,“玉儿,我好累。”
玉儿垂眸,拭掉后笑说:“小姐还有玉儿在身边,玉儿会一直守着小姐。”
她眼泪落下,失声念道:“从今往后在这宫里,小姐也就只有你了。”
玉儿将眸中的眼泪迂回去,笑笑说:“小姐不在陛下身边,也好。”她思及刘肇,心间笑意苦涩,紧了紧玉儿后,从此再也不言其它。
承制徘徊在殿门外,玉儿搂过着她沉声唤:“进来吧。”
承制灿灿不安进殿,垂着头小心提醒:“贵人,巢美人的小皇子找到了,但是那寒子琪并未抓到,怕是早已准备好了后路,此时消失得已是无影无踪了。”
她搂紧玉儿,闭眼道:“你也走吧。”
承制不安又道:“贵人,承制并非对贵人——。”
她沉声打断道:“邓绥明白,如今邓绥已是失宠,你也没有必要留在邓绥身边了,去侍奉陛下才是更好的前程,此前之事不会与你计较的,你且放宽心就是了。”
承制内疚咬了咬唇,垂头回:“谢邓贵人体谅,那——那奴才告退,邓贵人好身保重。”殿内的人紧跟着走了一大半,就如人走茶凉,人心冷暖她早已看透,也不觉得有什么可叹的了。
次日,听闻巢美人醒了过来,吕盖因在宫内极时找到了巢璃的皇儿,所以吕家因此保住了全家,可吕梦音却悄然无声离去,吕梦音只是一句宫人,因而并未大葬。不多久,宋贵人之事也得以尘冤,宋家还活着的人也被刘肇招回了京,与此同时烧当退敌投降。
徐子杰因武功被废早就已是形同死人,所以刘肇留了徐子杰一命,连着云晴也一同放过,毕竟韩漫儿没出事同时又是缺人之迹。听闻徐子杰家中一百八十口,全是死在明帝的命令之下,明帝被下方官员欺上瞒下,一个命令让一家余二百口人倾毁。
权力之下误断虽是常有,可是权高者是非分、黑白不明,定是弱者怨声载道,百姓苦不堪言。奸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前途,做过一件恶事就会继续做恶,甚至越来越恶。
他们习惯了欺骗、玩弄、算计对手,玩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群,而正直之人为表自己无愧于心,往往摆出一由刚正不讹,也绝不向恶者低头之色,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歪,一味认为正不压邪,其实那样的话不过是正道之人,为鼓励自己的一句话,往往世道皆多是正压不了邪。
有一句话叫百年正道是沧桑,因为不明之人辩不了是非,识不了黑白,更分不清大是大非,谈何不让对变成错?谈何不易被恶倾天?谈何不易好人做好事,最后恶者用个简单的计谋,便让其毁于转瞬之间?甚至被世人所骂?因为无知之人素来就多,因为不明真相的人由来也多。
真相往往在人们认为对的时候,却在下一秒某人一巴掌拍过去,吼了一句白痴,所以人们为了不让自己当白痴,渐渐就都认为对也是错,错也是错的,最后人们开始麻木不分真假,有的甚至开始用一句不要较真,劝自己适应谎言即可,最后好人不说话,对的事不再加以宣扬,恶人也越是如鱼得水所向披敌。
朝中官员之事她一直有耳闻,也是朝中官员之事让她明白静默之余明白这些,转眼已是永元十三年秋八,这四年朝中官员死的死,免的免,一直想要抓住寒子琪的刘肇,却也一直没有抓到寒子琪,好在这四年他与几位兄弟齐心同力共治朝纲。
只是这四年来刘肇却从未来看过她,这四年她与玉儿在嘉德宫虽是吃穿都不愁,可是就如被困在牢里的人般没有一点自由;这四年她虽过得平静,可是她已经快忘了浩儿的模样;这四年她在无数个夜里醒来,可往往便是后半夜从此无眠。
她从来不知道,原来四年可以这么漫长,曾经守孝三年,她天天除了哭便是哭,那个时候是活生生的人,她懂得痛懂得内疚。可这四年她感觉自己像木偶,感觉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白,感觉这四年就像在做梦,因为她是真的没有想过,刘肇可以四年都不来见她,可以四年都不管她。
失宠是两个字一个意思,只是被人遗忘原来也会迷失自己,如果不是玉儿陪着她,她或许疯了也不一定。日光四射,她穿着单薄睡衣,拖着地板走出,委身坐到一旁的摇椅上,扫了一眼天迹的耀光,仍是觉得刺得眼睛痛疼。
玉儿手里捧着一束花,见她醒来后迎了上来,蹲在她身侧笑问:“小姐,这花是奴婢刚采的。”
她无心看花,瞅着上空喃喃问:“浩儿今日有喊着找母亲吗?”
玉儿心下沉,将花收回放到地上,握过她手劝道:“小姐放心,小皇子好好的,没事。”
回忆就像一条伽锁,如果能像秦子英一样,可以忘却所有发生的事,或许她不会痛苦,更不会记得浩儿,可是她偏偏就记得,空洞只问:“浩儿是不是在找我?”
玉儿泛了泛眸中的泪,勉强笑说:“小姐,即便您心里再如何不肯承认陛下给小皇子安排了其它妃嫔当母亲,可是这早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对,她一点也不想承认此事,她从来没有想过,刘肇会在夺走浩儿后,在下一秒就给浩儿安排了其它妃嫔当母亲,她从来没有想过,母子离别在刘肇身上发生后,刘肇却要让她也来体会,这个曾经说爱她的男人,在她一直告诉自己再体谅体谅他的同时,反过来给的却依是残忍。
明明她才是浩儿的母亲,明明浩儿在她怀里十个月,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明明曾经那个说爱她的男人,对她说,你放心,有朕在这里,朕绝不允许别人伤你,旦凡敢伤你的人,朕就要了他的命。
明明曾经那个爱她的男人,为让她伴在身边想尽了法子,可是为什么可以这等绝情?以前他没有这么绝情,喃喃问:“听闻宫里现下很是热闹?”玉儿垂眸不语,她转而问,“过几日应是新宠程美人生辰吧?”
这四年她以为刘肇会不近女色,弃了她后会一心只管朝政之事,这事她同样的错了,这四年刘肇纳了不少妃嫔,听闻个个是貌美如花、才艺双绝,她隐约记得刘肇曾经吼着对她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朕少了你就不能活?原来这样的话在转眼之间,也是成为了事实。
宫里依旧相争相斗,可是大家现下即便是争宠,也是在皇后面前争宠,为皇后的喜欢而费尽功夫,而不争刘肇喜欢而费尽心思。
如今巢美人的父亲巢堪已为司空,冯婉婵有了自己追随的一批人,与阴婧之间素有暗里相斗,却也并未太过过火,仿佛只提醒着皇后,冯婉婵也不是好惹的,冯婉婵可以尊重皇后,但绝不像她这般低声下气,更不像宫里其它人一样,摆着一幅唯皇后独尊之色。
玉儿心下沉重,紧了紧她的手,只道:“是程美人生辰。”
她出神只道:“生辰好。”
玉儿瞅着她担忧道:“曾经小姐即便不得宠,可是却也没像现下这般,让人看着只是空躯壳,可现在的小姐——。”
她喃喃念道:“曾经陛下对我用情至深,千方百计设局让我入宫,曾经陛下说——。”
玉儿不安打断:“小姐,别再说了。”
她喃喃续道:“这四年我日盼夜盼,盼得肝肠寸断也无人理会,心底却总幻想着他想我忍不住来看我,可最终迎来的消息却是他新宠一个又一个,我以为从今往后他会不近女色,以为——。”侧过眸来不明问,“玉儿,陛下曾经待我之情,难道全都是假的吗?”
玉儿垂眸沙哑回:“这个世道女子从来就只是玩——,情再真都会有变质的时候,何止是小姐这般疑惑,就连玉儿都分不清楚,陛下此前待小姐之情是真是假。”笑了笑后擦掉眼泪,转而带着努力的微笑,宽劝道,“明明那么真,可是为何绝情时会是如此绝情?小姐不明白玉儿不明白。”
她狠狠闭眼,这情本该她来绝,痛本该他来受,她一再原谅他,原来原谅换来的,是自己永不翻身?如今盼早已没了,可心底念着一个人,那人便是从她身上掉下去的一块肉,她的孩子,拉过玉儿手无助乞求道:“玉儿,我想见浩儿。”
玉儿不安提醒:“可陛下——。”
她眼泪无肋落下,泣声问:“你帮我好不好?我想见浩儿,想听浩儿叫我娘。”玉儿瞅她这般顿时再次落泪,她喃喃续道,“我还未听他叫我一声娘,我才是他的娘啊。”说罢思及浩儿之心,已是挤入胸腔之内,紧紧搂住玉儿痛哭,“我才是他的母亲啊,啊啊,浩儿,我才是啊。”
玉儿搂着她眼泪直掉,缓下后硬咽道:“小姐,别哭,玉儿想办法。”
她紧紧搂住玉儿,心间如被夹在门缝之内来回冲刷,刺痛得五脏六俯间仿佛已碎成尘土,随时可随风而去,除了痛哭发泄外已是别无他法。每当她思及浩儿唤着别人为娘时,她只觉心间痛疼异常,仿佛某个位置不属于自己,她明明还活着,明明就在这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