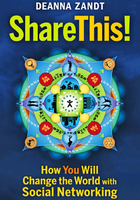玉儿忙提醒:“所以关健还是在婉清,那咱们借着孩子之事,让婉清好好想想,毕竟这个孩子不仅是陛下的,也是她的对不对?”
她头疼回:“她不一定会听咱们的,陛下之前都是无功而返,她自从走上这条路以来,咱们每每苦说,可她的态度一直就是不肯回头,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把握能劝回她,所以这才令我头疼啊。”
玉儿何尝不知,面露不安沙哑自问:“那如何是好,难道咱们真要看她去死吗?”
她转而一想,来了主意,笑说:“不如这样,咱们明日先想办法去瞅瞅婉清,她如果不听咱们的,咱们就将她姐姐与母亲请出来,她母亲说过让她一定要好好活着,只要她现下肯服软,陛下终是会念着她是孩子的亲娘,这十个月的时间总是有变数,只要她能除了心魔,陛下到时候也不一定真会杀她。”
玉儿似看到了希望,点头如小鸡啄米,瞅着她定定问:“咱们一定能劝她回头的,小姐,你说是不是?”
她知道玉儿希望她回答是,可是她心下却没底,忧忧道:“即便是她不仁咱们也不能不义,何况她并没有真的对咱们不仁,咱们更是不能看她誓死如归的陷进去。”玉儿再次狠狠点头,她缓回神来笑笑,起身道,“好了,回屋休息吧,不早了。”
天迹月光如瀑泻下,一缕明黄色飘于拱外,似宣告入秋时节快至。
她与玉儿回了屋,玉儿还未关上门,她细听之下发现走廊外有脚步声,微怔,转过身来一看,就见刘肇走到了她房门口,玉儿缓下初惊后忙屈礼:“奴婢参见陛下。”
她缓回神,慌忙上前屈礼:“邓绥见过陛下。”
刘肇并未瞅她,只是凝眉深思着,听后摆了摆手道:“都起来吧。”她起身打量刘肇神色,见他脸色怆白无力,心疼之下不由得一丝难过,她该怎么对待这个男人才好?他是一国之君也是她的夫君,可国君是国君,夫君是夫君,这两者之间是微妙的。
刘肇余眼瞅见她如此忧心的神情,却是微微一笑,上前拉过了她的手,拉着她往寝屋里走去,坐下后不温不火说,“朕累了,实在没地方睡,就来你这里了。”
她跟着坐下听后不由得一乐,笑说:“陛下还有开玩笑的心思,可宫里众人都担心陛下担心得要命。”
刘肇将头靠在了椅子上,闭眼保持着嘴角笑意说:“不用担心朕,朕没事的,朕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这点事怎么会难倒朕。”
她起身,走到刘肇身侧,瞅着刘肇受伤的位置,不安问:“陛下今日吃药了吗?”
刘肇笑说:“吃了。”
她续问:“风寒药、伤痛药都吃了?”
刘肇睁开眼,笑回:“都吃了。”
她细想了一下,又追问:“那补气养神的药吃了没?”
刘肇失声一笑,神色有几分无奈:“你真是比郑众还要啰嗦,这又不是什么重伤死不了的。”
她眼框一红,泣声道:“陛下不把自己当回事,也该想着宫里不少人,可是为陛下的身子担心得紧。”
刘肇拉过她手,笑说:“好,朕答应你,一定让自己快点好起来,不再让你担心了,好不好?”
她点头,擦掉眼泪,刘肇动了动身子,她伸手去扶,刘肇一用力却扯到了伤口,她发现刘肇神情不对,一怔,忙问:“陛下是不是扯到伤口了?”
刘肇痛苦点了点头,她稳下神来伸手去解刘肇衣裳,刘肇抓住她的手,忙问:“你要做什么?”
她忙回:“检查一下陛下的伤口是否裂开了。”
刘肇失声一笑说:“你把朕衣裳给解开,才当真会让朕伤口裂开,你不要碰朕身体,朕怕痒。”她疑惑,瞅着刘肇暧昧的笑意,脸砰的一声,立即飞红,刘肇却转而说,“不如你亲朕一口,让朕缓解一下痛疼的感觉。”
她本是羞涩不已,听后顿时哭笑不得,嗔道:“陛下,都什么时候了。”
刘肇认真盯着她:“你要不要亲?”她又窘又羞,刘肇却打着商量说,“朕这样跟你说吧,你亲了有二个好处,一来朕会觉得不那么疼,二来朕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何?”
她低声嘀咕:“这个时候还不正经,活该疼死你才好。”缓下神来笑说,“陛下有心思说笑,看来当真是病得不重,倒是让人白担心了一回。”说罢准备起身。
刘肇拉着她手不放,郑重其事道:“朕是真的觉得很痛,”
她红着脸坐下,瞅着他额头道:“好,亲了一下后陛下早些休息,明日还够陛下忙的。”
刘肇笑说:“二下。”
她失声一笑,不由得无语:“哪有陛下这样,先前说一口,现在又讨价还价。”
刘肇却笑意满说:“朕发现原来跟绥儿讨价还价,又能将一向淡定自若的绥儿弄得哭笑不得,很有一种成就感,如果绥儿不介意,咱们继续讨价还价,如果同意就开始吧。”说罢闭上了眼。
她咬了咬唇,扶开脸上的碎发,俯下身去在他额头亲了一下,正准备亲第二下时,刘肇却不温不火问:“换个位置成不成?”她转而在脸侧又亲了一下,刘肇却大失所望道,“绥儿大胆起来大胆得可以,害羞起来却也害羞得可以,又不是没亲过朕该亲的地方。”
她脸上再度飞红,缓了缓脸上的神情,笑问:“陛下今日是特地拿绥儿寻开心的是吧?”
刘肇望向她笑问:“朕现在告诉你一件事,你要不要听?”
她是又喜又气又急,一喜他心情如此大好,二气被他连翻戏弄,三急他这兴至何时能完,侧过身去低声说:“陛下要说就说,不说就算了。”
刘肇瞅见她神气后闷声一笑,撑着身子要起来,在她身后笑说:“朕今年的生辰,朕决定让你给朕办。”
她微怔,从刚才刘肇跟上来的时间,还有步伐与路程来看,她疑惑问:“陛下听到绥儿刚才讲的话了?”
她凝眉回想,之前应是没说什么大不敬的话吧?刘肇似知她心中所想般,突然扑赫一乐,笑说:“放心,你刚才没说朕的坏话,也没说让朕生气的话,你办好这次生辰之事,朕还会重重赏你。”
她想了想,却略感不安,忙屈礼道:“陛下,万万不可。”
刘肇微怔,疑惑问:“什么不可?”
她抬眸提醒:“往年的生辰都是皇后娘娘为陛下办的,何况贱妾只是一名小小采女,陛下的这等大事再怎么轮,也轮不到贱妾来插手。”
刘肇浅浅一笑说:“生辰之事的操办朕会亲自与皇后说,要不然你怎么向朕讨恩典,朕又怎么借口替你饶了婉清。”
她一愣,方才明白过来,心下感动,失声唤,“陛下。”反映过来欣喜屈礼,“谢陛下。”
刘肇拉她起来,笑说:“朕也不能总来禅风阁,借着朕这次生辰,朕也想宣布你贵人的身份,再给你找个好一点的去处,虽说现下后宫大多宫殿都是空的,可朕还是觉得新造一个宫殿给你比较好。”她凝眉不安,刘肇转而笑说,“好了,即然你还是有所顾虑,那朕就不折腾了,朕再想想有无别的地方。”
她点头,垂眸想了想说:“不如就嘉德宫吧。”
刘肇垂眸细想,忧说:“嘉德宫离桐宫太近,而且桐宫此前出了不少怪事,那个地方实在是不好,再来嘉德宫离朕太远,朕有时要是累了,也有不想动来动去的时候。”
她提议道:“那不如就选个偏殿吧。”
刘肇沉声道:“一个贵人怎么能住偏殿,没有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