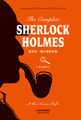上半夜,月黑星稀。下半夜,星星渐渐发亮,月亮逐渐代替星星,把大地照得熠熠生辉,那些树、坎、丘拖着长长的影子,似乎在向苍天展示它们那活力四射的身姿。此时正是农历的下半月,下弦月显示出了它有的。
大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那遗址和它的周围。
遗址出奇的平静,周围也没什么异样。
几个小时过去了,除了偶尔刮过几阵轻风,遗址周围的灌木婆娑,轻风摇曳之外再没看见能动的东西。
东方渐渐发白。
这一夜一无所获。
接下来的几天,专案组夜间埋伏早晨撤出,连续蹲坑。
在罗莎的红外线望远镜里,除了有几个小动物月明星稀的时候在那遗址周围转悠过之外,其他什么情况也没获得。
大家有些沉不住气了。
罗莎把同志们召集起来,语气坚定地说:“闹鬼这件事不可能空穴来风,麻雀飞过有影子,正因为有过影子,人们才会说有麻雀飞过,虽然我们还没有捕捉到‘鬼’的行踪,并不完全说明就是老百姓谎报军情,我们不能埋怨老百姓,应该先从自身找不足,是不是我们的行动走漏了消息,被嫌疑人察觉了?”
大家在陈渝的启发下,从前到后认真回忆了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程序,都没有发现什么差错。
问题出在哪里呢?
罗莎肯定地说:“既然我们主观上没有出现差错,那就找一找客观上的原因,或者是嫌疑人太狡猾,我们与嫌疑人比耐力、比韧劲不够。”
大家决定继续蹲坑。
罗莎非常明白这个世界上肯定没有鬼,所谓的“闹鬼”多半是有人装神弄鬼,或者是谣言。近百年来,形形色色的谣言传遍中华大地,小到剪辫子会夺去人的灵魂,大到改朝换代。
罗莎曾经听说过,在乾隆时期,一贝关于妖术的谣言竟然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影响波及数千万人。当时的人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他的灵魂为妖术师服务,而灵魂被盗者会立即死亡,以至于全国上下都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闹得乾隆皇帝都寝食不安,力图弄清盗魂恐惧背后的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罗莎想,无论是有人装神弄鬼还是谣言,都必须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但方法上可能要有所改变,不能只在一棵树上吊死。
这天晚上,弯弯的月亮很快就挂在了天空,下半夜,刮起一阵凉风。宁静的夜色飞过阴风惨惨,让人汗毛耸立。
一只夜鹰不知是什么时候飞过头顶,在天空中盘旋着,发出“呱哇一!”“呱哇一!”“呱哇一!”的鸣叫,这种声音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环境响起,让大地颤抖,让黑夜恐怖。
夜莺的鸣叫令人烦躁不安,蹲坑的人们耐着性子,毫无办法地认真听着。那家伙并不管你能不能忍受,一声接着一声“欢快”地叫着,没完没了。过了很大一阵,似乎因为没有找到“知音”,才极不情愿地。
周围的气温跟着渐渐消失的月光一起“嗖嗖”地直往下沉。月亮走了。没多会儿,星星也走了,留下一片漆黑。
侦破小组的人们经过夜莺的折腾,已经有些疲,感觉到了蒙昽的睡意。又是一阵凉风刮起,凉意蹭过鼻尖,让人不禁抖了一个寒战。
夜很深了,蹲坑的人却能感觉到黑暗中山顶的松林顺着风势一起一伏,林叶交错的当口发出一种撕裂般的啸吼,在空旷的山间显得格外绵长而萧瑟,人们情不自禁地又是一阵寒战。
忽然,远处响起了“孤啊一!孤啊一!孤啊一!”的吼叫。那声音沧桑桀骜,由远而近。
那一声接着一声的凄楚哀号,让人觉得天空了、地旷了,脑袋大了,毛骨悚然了……
“孤啊一!孤啊一!”声音越来越近,很快由东向西一团白色飘来……
那东西飘飘然然、晃晃悠悠、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伴随着声音,近……
白的不大,有。
“白色”在遗址里面转了个圈,吼叫着“孤啊一!孤啊一!孤啊一!”向西;决速飘去……
罗莎觉得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睁大眼睛,一声命令:“出击!”带着陈渝和十几名武警战士呼啸而下,直奔“白色”。“白色”似乎听到了响声,突然加快速度,斜刺着向南急转,变成曲线闪动,速度之快,非一般人所能及。
罗莎大吼:“开枪示警!”
“哒哒哒……”一梭子弹从枪膛滑脱而出,声首划破夜空,清脆,悠远……
那白色受到枪声的刺激,孤注一掷,飘得更快了。
罗莎带人奋力直追,但根本不是那白色的对手,眼看距离越拉越……
罗莎再次大吼:“开枪击毙!”
十几条火龙冲着那白色一阵点射,白色终于矮了下来,在前方几十米处不动了。侦破小组的全体成员一阵猛跑来到白色面前,迅速合围,一齐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原来是一只狗,嘴里含着一段骨头,眼睛突出,鲜血横流,已被子弹打成了筛子。
罗莎觉得奇怪,这狗怎么会在漆黑的夜里浑身闪烁着白光呢?既然嘴里含着骨头,为什么还会发出那样恐怖的声音呢?狗会不会只是一个傀儡,背后会不会有人操纵?一连串的问号在她脑子里翻腾。她让小组成员立即灭了手电,迅速散开,盯住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同时监视现场,等待它身后的“主使”现身。
经过这番折腾,大家已没了睡意,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高昂呢。
天渐渐亮了,“主使”却迟迟没有现身。
罗莎让武警战士仍然守着那个战利品,自己带着陈渝沿着那狗昨晚来的方向向前搜索。他俩一直向东,走了两三公里,来到一个公众墓地,原来这里就是有名的杨家嘴墓地。
在墓地北侧他们发现有新鲜的狗脚印,沿着那脚印进入到一个墓堆。墓堆的右侧有个不深不浅的坑,坑壁上明显地印着四脚动物的抓痕,有可能是狗爬上爬下留的痕迹;坑中有动物滚沙的迹象,还乱七八糟地摆着一些白骨。罗莎跳进墓坑,仔细观察,发现动物滚沙的迹象中,夹杂着不少动物毛,毛的颜色与被打死的那只狗一致。
真相大白了,那狗是在这坑里蹭痒痒或滚沙取乐,狗毛粘上不少的磷,月光照耀下看不出来,在漆黑的夜晚却能释放出耀眼的磷光。
后来,罗莎又向一些有经验的老农请教,他们说,毛狗衔着人骨头,奔跑喘息的时候就会发出“孤啊——!孤啊——!”的怪声。闹鬼的事情可以结案了,装神弄鬼的就是那只狗,与“第一美”造型发屋的血案毫无关系。
马王槽闹鬼的案子破了。
回过头来,罗莎把注意力放在了刘海身上。
按她的推测,如果张洪利真的遇害,凶手有可能是刘海,而不应该是李向东,李向东充其量是个幕后指使。
罗莎此时并不想惊动李向东,她让巧巧费点神,一定稳住李向东。待她这边有了重大进展后,巧巧再配合他们收网。
刘海救了试图自杀的白领郑甜,郑甜向他发起了不折不扣的爱情总攻。刘海也是人,并且是一个未婚男人,他哪里经受得住郑甜那么软磨硬缠的严厉攻势,当天晚上就与郑甜住在了一起。
郑甜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或失败的同居恋爱,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这一次,她十分看重和刘海这个救命恩人的关系,她不想再经历只有花儿红、没有果子涩的爱情,她要和刘海去登记拿证,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婚姻,组建法律认可的合法家庭。
刘海也真是奇怪,每当甜甜提到结婚的事,他总是拿话岔开,或是找借口推三阻四。郑甜急眼了,问刘海是不是看不起她,不愿和她过曰子,不愿承担今后的家庭责任。刘海却堆满笑地说,?P有不想之理,与甜甜终身厮守,是他求之不得的人生第一乐事。
刘海说这样的话,完全出于真心。
想想看,人家是城里的大学生,要文化有文化,要能力有能力,今后生个儿女也是一个“高智商”。还有郑甜的模样,诚如她的名字,的确甜美清秀,郑甜是属于温柔敦厚型女人,脾气很好,比起李向东家那老板娘来要强好多倍,老板娘常常很霸道,厉害着呢。年龄上也胜过老板娘,郑甜才20多岁,老板娘已经40挂零了。郑甜活力四射,青春照人,老板娘却是徐娘半老,少有风韵。划海想自己只是一个从朱山里走出来的粗人,哪一点比得上人家,要不是人家刚刚经历过一场爱情的波折,自己遇上一个填补空白的机会,上哪儿去找这个“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没准人家一旦醒豁过来就反悔了。刘海也想用法律来保护他的既得利益,否贝煮熟的鸭子可能还会飞。但刘海也有他真实的难处。
要结婚,首先得去街道登记。谁是已婚,谁是未婚,总得拿出个凭证吧,不然有的男人同时娶几个或十几个妻子,有的女人同时嫁几个或者十几个男人,这个社会不就乱了套吗?因此,在办理结婚登记时,男女双方都得出示户口簿或身份证。
这就把刘海难住了。
户口簿,刘海是有的,而且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他是未婚。可那东西放在老家,因为他命案在身,不敢回去。通过邮局快递,他又不能暴露藏身的地点,看来,出示户口簿,不现实。出示身份证,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个真实的身份证,无论如何是不能拿出来使用的,只要那东西一亮相,警察就会找上门来。
当今科技这么发达,信息这么快捷,一个在逃的有命案的犯罪嫌疑人,人家能不利用网络追逃吗?那网络就像一张真实的大渔网,随时悬挂在空中,只要你一露头,网就会从天而降,扣在你头上,这就是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那么,花一百元钱买来的那个身份证呢?
那是一个不值一提的玩意儿,那东西在普通市民面前晃一晃还可以对付对付,比如租个房子,进个“y”网吧什么的,谁会留意你那玩意儿的真假呢?私人小老板只认钱。因为他们不可能花钱去置办一个身份证鉴别真伪的机器,才使假东西能蒙混过关。
可是要拿假东西去住酒店或搞婚姻登记,你就该倒大霉了,人家会逮住你不放,直到查个水落石出。
该怎么办?记得第一天晚上不是告诉过郑甜,自己是逃婚离家出走的吗?干脆就对她说,离家时走得匆忙,连身份证都没来得及带,那东西与户口簿放在一起被母亲扣下了,自己出来干什么都不方便,只好花100元钱在街上做了个假身份证,如果将假身份证拿去登记办理结婚证,是会出问题的。
本来,刘海这半真半假的话有许多疑点。可是,一个被爱情蒙上眼睛的女人智商低到了极限。听刘海这么一解释,反而吊起了郑甜的胃口。在郑甜看来,刘海光明磊落,坦坦荡荡,说话合情合理,这不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男人吗,她觉得真的不能失去他。
“哦,好吧!”她叹了口气。
既然事情都说到了这个份上,去街道领取结婚证书的事只好放一放了。不过婚还是要结的,人生就这么一次,她要举行一个隆重的婚礼,不怕花钱,那东西花了可以挣,她相信自己和刘海的实力。
婚礼要有品位和规模,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高兴,最重要的是要让前男友看一看,是不是离了他那颗芝麻就榨不出油。她要证明自己的魅力,虽然被前男友抛弃,不仅没有倒下,而且还风风光光地嫁了一个健康、帅气的棒小伙作丈夫。事情就这样定了,刘海也没啥话好说。
只要不拿假身份证去领结婚证,干什么事他都听郑甜的。况且,办婚宴又不要他给钱,一切费用都是郑甜自己挣来的。
事实上,这个婚礼也就一个说法,并不是想象的么回事。比如请客赴宴,由于他们都不是当地人,没有太多的熟人和朋友。所谓宴请,也就是郑甜在本市的同事和请来的几个人,不足两桌,根本谈不上什么气势。又如结婚仪式,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传统意义上的仪式也就没了用场,“闹房”不过就是谈谈恋爱经过,或者新郎、新娘当着这两桌人回答客人提出的几个关于山盟海誓、海枯石烂、不离不弃之类问题。接下来就是客人吃饱喝足之后,上小两口的洞房参观参观,坐一坐便拍屁股走人,剩下是小两口关起门来自己乐乐。郑甜的同事、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人,很注意礼节礼仪,并没有出格的要求和过分地为难这对“新人”。
婚纱照在前几天就完成了,花了一大笔钱,大大小小拍了好多张,也就是自娱自乐。结婚的日子也请人看过,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日子,不管是升官还是求财,那日子都很靠谱。迎亲是交由婚庆公司的,租了三辆小车,一辆是劳斯莱斯,一辆奥迪,一辆宝马。劳斯莱斯坐了刘海和郑甜,然后就是伴娘伴郎曾超和曾超的男朋友,其他两辆车上便是吃婚宴的人,在万州城区转了一圈就进了办席的酒店。
按照郑甜家乡的习俗,婚礼的前一晚,新郎和新娘是不能住在一的。
郑甜与刘海商量,刘海住在郑甜早已购置的现在装扮一新的新房里。郑甜住到刘海刚来时暂住的那个房子里。幸亏这一阵子忙于结婚的事,那房子还没来得及退租,要不然这一夜郑甜就没住处了,总不能上宾馆去迎亲吧。当然,她也可以住到闺中密友曾超的出租房里,但曾超同居的男友就得住宾馆了。
郑甜觉得已经麻烦打扰不少曾超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给曾超增加更多的麻烦。
第二天是黄道吉日,郑甜大喜的日子。
这一夜她怎么也睡不着觉,像一个失眠患者偏偏在上床前喝了咖啡或浓得发苦的青茶,辗转反侧,兴奋不已。
躺在那张床上像是在晒沙鱼干,不停地翻动身子,弄得那张陈旧的柏木床发出吱吱的响声。郑甜在想,这张床要是睡两个人,响声会更大。此时才想起曾超白天对她说的那句话:“甜甜,明晚别把床铺弄得太响,别人听了会吞口水的。”说完,嘻嘻地怪笑。
当时她没在意,因为她与刘海现在睡的那张床根本就没有什么响声。
已是凌晨1点了,还睡不着,与其这样耗下去,还不如早点起床准备准备。她轻脚轻手地下了床,打开床头那盏小灯,微弱的灯光一下子刺破了黑暗。然后,她悄无声息地走出房门,径直来到洗浴间。她尽量放轻脚步,生怕惊动了左邻右舍。
洗浴间是利用阳台的一端隔出来的长不过1.5米,宽不过1.2米的小隔断房,顶部和墙体上部粉刷的白色涂料已经泛黄,下部的墙体是用劣质的黄色瓷砖镶嵌而成,地面是那白色搪瓷蹲便器,一个简易的淋浴喷头挂在墙的壁杆座上,灯光下墙体和地面黄白相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郑甜想起了钱的作用,有钱自己可以买房,想怎么装修就怎么装修,没钱就只能住这样的出租房,还是很掉价的,一种寒酸的感觉。她觉得把刘海从这样的环境中,请到她的自购房,应该是一种帮助,当然与救命之恩是不可相比的,但多少是对他的一点偿。这样一想不觉增强了一些信心,似乎更拉近了一些与刘海之间的感情距离。
郑甜打开热水开关,门外燃气水箱里的电子打火器发出嗞嗞嗞的撞击声,不一会,一股水从喷头夺路而出,开始还是冷水,慢慢地就了。
她把手伸进那向下喷洒的水帘,心暖了,全身都有了燥热,使她想起第一次与男人干那事儿。她献身的第一个男人就是她的前男友,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悔。当时为什么就么冲动,有一种义无反顾的冲动,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交给前男友了。
此时想起来又觉得有点对不住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