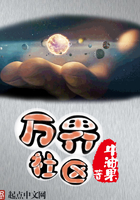“阳 痿病又称勃 起功能障碍,指男人那个痿弱不用,不能勃 起或……”谢坚歪歪扭扭的斜身趴在电脑桌上,斜眼看着倒立的《谢氏针灸》手抄本。牛头不对马嘴的乱念。念了一半,被门口的声音打断了。
“阿坚,你是不是耳朵又痒了?”谢军当门而立,双颊比平时长了两倍,抬腿进了房间,大步走到电脑桌前,伸出右手抓过《谢氏针灸》手抄本,发现书是倒着的,气得直咬牙,左手扣指弹向谢坚的右耳。
谢军和王梅结婚快二十年了,只有谢坚一个儿子。而且是九代单传。谢家是中医世家。谢军虽然是远近闻名的中医高手。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天赋,没有能力发扬谢家的中医,只能保持先辈之风。
一直以来,他希望他们惟一的,而且智商不低的儿子可以发扬谢家的中医,尤其是《谢氏针灸》术。这是谢家出色的绝学之一。可是,针灸术一直不能超越先辈的成就。他一直寄托谢坚可以发扬谢氏中医。
但遗憾的是,谢坚从小就不喜欢中医,甚至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有的时候,他气极了,想打谢坚,却总是被王梅拦着。不管怎么说,谢坚是谢家九代单传的独子,更是王梅的心头肉,坚决不准谢军打他。
事实上,谢军也舍不得打他,但是,他是恨铁不成钢。他们只有谢坚一个儿子。如果他不学中医,谢家的中医就会失传了。他死了之后,也没有脸见谢家的祖祖辈辈。
因为王梅的关系,他不能打谢坚,只有想方设法的诱 惑谢坚,让他喜欢上中医,甚至是爱上中医,并心甘情愿的学习中医,更希望他发扬谢氏中医。
随着年龄的增长,谢坚也渐渐明白了谢军的苦心。但是,他真的不喜欢中医。但又不能一直和谢军唱对台戏,为了应付谢军,有时就敷衍几下。刚才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过,他上高中之后,对中医的抵触情绪渐渐消失了,而且还起了一点好奇之心。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他偶尔听到村子里的女人私下聊天,说她们的男人在床上不行。
当初,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男人身强力壮,平时做农活样样在行,为何到了床上就不行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知识的增加,还有生理课学到的知识。
渐渐的,他终于明白那些女人说的“不行”代表着什么。听的次数多了。他的好奇心越来越重。偷偷的,背着谢军看中医书。当然不是一般的中医书,主要是有关男人肾虚方面的书。
关于男人肾虚方面的知识掌握多了,谢坚的好奇心更重了。不停的研究,男人怎会肾虚呢?肾虚之后,为什么在床上不行?为什么不能满足自己的女人?
他心中的困惑越多,越想弄清楚这些问题。所以,时常偷看这方面的书。刚才,他以为谢军又出诊去了,所以放心大胆的看男人肾虚方面的书。
但他没有想到,谢军还在家里,还被抓了一个正着。惟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动作比谢军快。在谢军进门之前,他已经把男人肾虚的书藏好了。
他在匆忙之间拿出《谢氏针灸》手抄本,本想应付谢军,可惜放倒了。而且还被谢军发现了。知道又要受惩罚了,不过,上当的次数多了,他已有经验对付了。
“老爸,你这招不灵了,换一招吧。”谢坚蹬脚滑动电脑椅,顺利避开谢军的弹指之刑,扮个马脸诡辩,“我叫谢坚,当然要研究坚或不坚的知识。谢家的针灸术,以后慢慢学。”
“你……你……”谢军放下《谢氏针灸》手抄本,疾扬右手,扬了一半突然放下,两眼一转,计上心头,“儿子,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谢坚滑动电脑椅靠过了去,两眼却盯着谢军的右手,担心他突然偷袭,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了,他上过当,吃过亏,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儿子啊,老爸给你取名一个坚字,不是指男人那个坚或是不坚,而是希望你坚强。不管遇上什么事,都要坚强、勇敢。”谢军拉过藤椅紧靠他坐下,伸出右手轻抚他的睡平头短发。
“这个……老爸,我们既然是中医世家。研究一下男人坚或是不坚。属于最常见的中医知识。难道不对吗?”确定他不会偷袭了,谢坚暗自松了一口气,侧身把头靠在谢军的肩上。
“我要告诉你的秘密和这个有关。”谢军扶正他的脑袋,挪动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谢氏针灸本有一篇专治男人那个的。遗憾的是,在你曾祖父那一代失传了。”
“失传?怎会失传呢?”谢坚突然从椅子上跳起,两眼瞪的比核桃还大,细细打量谢军的眼神,有失落和伤感,不像编的,说明真有这码子事,用力握紧右手,在空中挥了几下,“曾祖父太那个了,岂不成了谢家的罪人?”
“不许这样说你曾祖父。”谢军瞪了他一眼,拉他坐下,耐心解释,“你曾祖父出夜诊,回来的时候遇上暴雨。被崩塌的山石砸死。他不但不是谢家的罪人,反而是谢家的楷模。”
“哦……真的太可惜了。”谢坚竖起右手大拇指比了比,瞄了电脑右下角的时间一眼,快到十点了,想起和刘二娃的约定,知道该溜了,“哎哟……老爸,我肚子有点疼,去楼下解决解决。”
“懒人屎尿多。”谢军伸手想拉,却慢了半拍,谢坚已经溜了,眼浮失望之色,起身收好《谢氏针灸》手抄本,“难道谢氏针灸会在我这一代失传?”
谢坚下了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堂屋大门。穿过门前的水泥地坝子,转眼消失在菜园子中间的林荫小道中。石头小道的尽头,刘二娃正眼巴巴的探头张望。
“二娃,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快入戏了?”谢坚伸出右手抓住刘二娃的右肩转过他的身子,发现他有点紧张,“别怕。出了事我顶着。”
刘二娃是乳名,他的真名叫刘勇。是谢坚的死党之一。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刘勇十二岁那年,在田里捉黄鳝【鳝鱼】。意外的被田里的水蛇咬了。
水蛇有毒,刘勇当时就昏了过去,幸好谢坚路过救了他。当时的谢坚年龄也不大,要背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人跑两里多路回家,真的不容易。到了他家里,他累得抽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
经过谢军的抢救,刘勇的性命保住了。知道经过之后,刘勇感动极了,加上谢坚的智商比他高。从此之后,他死心塌地的跟着谢坚,做了他的跟班。不管大小事情,只要谢坚说向东,他绝不会向西。
“老大。那丫头比朝天椒还辣。万一知道我们偷看她洗澡,你是不怕,我就死定了。”回想这段往事,刘勇还是有点怕,缩了缩脖子,扭头看着安欣家的房子。
“怕个鸟。我和她斗了十八年了。她只赢过我三次。上次是她使诈。别开这次不谈。她只赢过我两次。”谢坚张开左臂搂着刘二娃的肩膀,沿着弯曲的石头小路,大步向安欣家后院走去。
“老大,你一个人去吧,我在旁边给你放风。”快到安欣家的房子了,刘二娃两腿发软,想到安欣的野蛮和泼辣,真没有勇气偷看她洗澡。
“我 日。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兄弟啊?”谢坚收回左手松开刘二娃,甩腿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从明天起,你别叫刘勇了,干脆叫刘懦。胆小鬼!”
“老大,别开那丫头不谈,我们家也惹不起她老头。再说了。她老头好像想和你家结亲。假设军伯和梅婶同意了。她就是你的那个了,我能看她洗澡吗?”刘二娃反手拍去裤子上的泥巴,还没有勇气过去。
“算了。只能说明你没有眼福。眼睛瞪大点。我不怕别人发现,但千万不能让我老爸知道。否则,我又要背谢氏针灸了。”谢坚拍拍刘二娃的肩膀,放轻步子向安欣家的后院走去。
“老大,小心点。”刘二娃从脖子上取下自制的望远镜,凑近双眼四处打量,确定附近百十米内没有别人,钻进草丛趴下,举着望远镜扫视四周。
“你不能亲眼看,到时看她光屁股的相片,一样刺激。”谢坚抬腿脱了土黑色的塑料拖鞋,顺脚踢进旁边的草丛内,探手抓树,躬身爬到房子后面的柏杨树上。
他喘了一口气,弯腰坐在树杈之间,伸直右腿从裤兜里掏出双镜头的手机,左手抱树,伸长脖子向二楼的气窗望去,见里面开着灯,估计安欣已经进厕所了。
他向上爬了爬,发现位置正好合适,目光透过气窗口,发现安欣已经进去了,水龙头也拧开了,正在脱上衣。可惜是背对窗口,看不到前面的风光。
不过,只看看她背部的肌肤,也能让谢坚不停的流口水了。安欣虽是农村女孩。可是,她从没有做过农活。从小到大,在家里像公主一样。
在别人的眼中,她真的像公主。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她一直是无可争议的班花、校花,当然也是他们村里的村花。也是乡花,更是镇花,是不是县花,他不能断定。不但脸蛋美,气质更迷人,身材也不错。
不管是手脚或是身上的肌肤,每处都是又嫩又白,如脂似玉,水灵灵,比刚出锅的豆腐还嫩,轻轻的一掐,似乎就可以掐出水来,迷人极了。看得谢坚不停的吞口水。
她是安阳和罗丽的独生女儿。家里的情况,和谢坚大同小异。都是独生子女。惟一的不同。安阳和罗丽对安欣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她用心念书,将来考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找一分好工作。
“臭丫头,拍不到你的前面,拍背部也能报仇了。”谢坚咕的一声吞了一口口水,抓着手机伸出右手,把镜头对准安欣的背部,尽量拍裸 露的部分。
“汪!”谢坚刚取好镜头,准备按手机快门拍安欣的祼背,树下突然响起狗叫声。赶紧停止,低头打量,发现是安欣家的大黑,准备吹口哨哄它。那家伙却不停狂叫。
“老大,快跑啊。那狗东西六亲不认。只有安家的人能镇住它。听到狗叫。安老头肯定会出来查看。”刘二娃从草丛里爬起,撒开两腿拼命逃了。
“大黑乖,别叫。”谢坚额头冒汗了。不管安阳是否出来查看。大黑一直守在树下,他无法离开。迟早会惊动安家的人。甚至惊动其它的左邻右舍。
说实话。他不在乎村里其他人的想法和看法。却不能不顾及谢军和王梅的面子。不管怎么说。谢家在村里是有头有脸的。谢军更是村里德高望重的名中医。
“阿坚,你躲在树上做什么?”他还没有想妥如何蒙混过关,树外五米处响安阳的声音,与此同时,刺眼手电光照在自己脸上。
“安叔……我在树上抓知了。”谢坚心里一急,没有时间深思,此话脱口而出,转念一想,即使不能取信安阳,至少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
“阿爸,别相信他。”安阳还没有时间思索此话的真假,二楼的窗子突然开了,露出安欣微显扭曲的天使脸庞,“他躲在树上肯定想偷看我洗澡,树下有大黑守着,他下不来。阿爸,你去叫军伯来,看他怎么说?”
“姓安的,有必要做这样绝吗?”谢坚真急了,他可以骗安阳,却无法骗谢军,不管说什么,都无法取信谢军,明明是说上厕所,却爬到了安欣家后院的树上。有十张嘴也无法解释清楚。
“欣儿,算了吧,阿坚也许真的上树抓知了。”安阳站着没有动,显然不想让谢军知道这件事,他清楚谢军对谢坚的期望。
如果这事闹大了,谢军放不下面子,一定会重惩谢坚。到了那一步,谢坚一定会恨安欣。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不管怎么说,他们俩人不但同年出生,而且是同月同日,只差不是同时了。
“阿爸,你不去,我去。”安欣伸手关了窗子,跑步离开厕所,顾不上换鞋子,穿着火红色的塑料拖鞋下了楼,经过后面的草坪时,对谢坚吹了一声口哨,“下流胚子,你等着。这次看你怎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