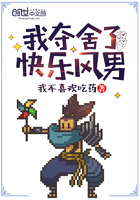一
夜色渐浓,浓重的雾气中蕴含了无尽的寂寞。玉真公主在观里静坐着想:“王维啊!你这小冤家,我帮你改变了命运,你为何不来看我?几天了,张说应该能让你过来,为何不见你的影子?”正这么想,紫燕进来道:“公主殿下,王维求见!”玉真公主大喜道:“请进。”紫燕应声出去。玉真公主想:“他来见我是什么原因?要是有求于我,事情就好办了。要是别的原因,我必须数落他一番。”
王维进来施礼道:“参见公主殿下!”玉真公主看着眼前思念的人,不无嘲弄地道:“哎哟,真是你呀。怎么人一当官,就忘了别人的举荐之恩?看来,你可真是世上最有品德之人。”王维不敢去看公主的表情,低着头道:“惭愧!自公主殿下给了下官前程,下官只想着怎样报效朝廷,所以忙于应酬,今特来请罪。”玉真公主冷笑道:“你有何罪?”王维还是不敢抬头,只是道:“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不能常来看望公主殿下,心中有愧。”
玉真公主心中一暖,好像多年的委屈当下消失,立刻起身问:“你真这样想?”王维抬起头道:“这次陛下命下官以凉州判官的身份前往凉州,却又被追回,让下官负责史籍编纂,要不然能否回到长安参见公主殿下,还真难说。”玉真公主想:“看来这是张说用计,由此看来张说倒是言而有信,值得信赖。”因见王维站着,微微一笑道:“坐吧,不管你咋想,能来看我,我就感到欣慰。”王维拘谨地道:“多谢公主殿下宽谅。”说完坐下。
紫燕在王维面前献上茶水、果品,立刻退去。王维感到气氛沉闷,又道:“公主殿下一向可好?”玉真公主笑道:“本公主一向喜欢游山玩水,道友极多。我想你是个大忙人,定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又有什么荆棘阻道了,这才想到了我?”王维立刻起身施礼道:“下官确实对不起您,请恕罪。”玉真公主见王维十分惶恐,觉得已经使他十分难堪,只能见好就收,便道:“都是过去的事了,知道忘恩负义就好。说吧,有什么难处?本公主还是愿意为你扫平障碍。”
王维再次施礼道:“多谢公主殿下!如今腾格里沙漠中有一伙悍匪行踪诡秘,已经使丝路北线再次中断,请公主殿下尽早向陛下进言,早日发兵剿匪,确保丝路北线通畅。”玉真公主道:“我以为是你个人有什么事,原来竟是朝廷大事。这丝路是大唐与河西、西域诸国以及葱岭以西各个国家实现经贸、文化往来的过道,怎么能随便中断?你应该面见陛下说明,陛下最重视丝路,必然发兵!”王维道:“陛下不肯见下官,只是让下官潜心编纂。”玉真公主道:“他今天或许很忙,但总有一天会见。”
王维着急地道:“可这事紧急,每耽误一天,就不知有多少商人和来自各国的使者死于非命。”玉真公主从心里敬佩他的官品,便道:“看来你倒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官。”心念一动,想知道他是不是张说让他来的,因此道:“这是朝廷大事,你应该去见张说,他是宰相,让他奏报是职责所在。”王维道:“此话不假,但公主殿下有所不知,下官来到此地,正是张大人让前来求您。”
玉真公主不由怒道:“原来,你心里根本没我!要不是张大人让你来,你是打算再也不来了?看来,你是忘恩负义的人!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脸面见我?!”王维忙施礼道:“公主殿下教训得是,王维知错了。虽是张大人让下官亲自求见公主殿下,但其实也是下官真心来见公主殿下。一则借机向公主殿下表达当年的举荐之恩;二是表达多年来疏远您的失礼之罪;三则为了朝廷,求您以国家大局为重,早日向陛下进言。”
玉真公主像是看透了王维似的冷笑道:“呵,你倒是很会说话呀。好吧,我先不追究过去的事,只说现在。本公主一直期盼你能陪我,若是今晚你能使我快乐,我明天就去面见陛下,保证让陛下发兵。”王维为难地道:“这……”玉真公主当下恼怒,愤愤地道:“怎么?你是要让我对你失望?”王维忙低下头道:“不敢!公主殿下不但冰清玉洁,而且还是道家高人,下官怎敢玷污公主殿下的清白名声?”玉真公主冷冷地道:“说得漂亮!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王维装糊涂道:“莫非公主殿下是在试探下官的品行?”玉真公主再次大怒道:“谁试探你了?你别装糊涂!”王维道:“可公主殿下应该知道,我有妻子,不能对不起她!”玉真公主恼道:“我没说让你休她,也没说要还俗嫁你,只要你今天陪我一晚,以后有空过来,我就是你的人;将来你有什么为难事,我都尽力为你扫清障碍。”王维犯难地道:“公主殿下,您是修道之人,应该洁身自好,下官大小也是朝廷命官,不能让世人议论。”
玉真公主道:“好!看来你是一个谦谦君子,独我玉真是个放荡女人。你走吧,以后不管你是一步登天,还是被打入地狱,都与我无关!”说完此话,长袖一甩,作出一个逐客的动作,背过身去不再看他。王维当下急了,忙道:“公主殿下不要生气,这是道门,要的是干净。据说金仙公主一心向道,已经跨鹤升天。下官希望您也早登仙界,永享快乐,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丢失累劫修来的道行。”
玉真公主猛地转过身来,愤愤地道:“不用你管!本道姑要走什么样的路,那是我的选择,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也许过不了多久,你还真可能进入十八层地狱受苦!而我,却活在逍遥的天堂里!”王维更加急了,忙道:“公主殿下,下官这是为了您好,下官所求之事,也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公主殿下万莫因我而坏大节。”玉真公主再次背过身去道:“你走吧,今生今世,我再也懒得理你!送客!”紫燕立刻走了进来,对王维作出一个手势道:“请!”王维叹了一口气,走了出去。
二
在长安大街上,李静钧到处打听着钱丰的家,从饭馆里出来一人高喊道:“大哥!”李静钧扭头一看是三弟李静安,意外地道:“是你?”李静安道:“怎么连亲兄弟也不认了?”李静钧道:“几年不见,我还真不敢认,你在长安做什么?”李静安道:“进去说吧,这是我开的饭馆。”李静钧抬头看了一下门面道:“看来,你是做大了?”李静安道:“还算不错。”
两人进了饭馆,小二以为是老板招揽来的客人,忙上前热情地道:“客官,想吃什么?”李静安忙道:“进雅座,你去叫我老婆、孩子过来,说我大哥来了!”两人进了一间雅座,李静安说了自己的经营情况,强调刚来时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如果不是二哥在长安帮忙,自己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李静钧吃惊地道:“这么说,你二哥在长安?”
李静安道:“对!他深得宁王信任,也结交了很多官员。在他的庇护下,常有他的朋友关照生意。”李静钧纳闷地道:“不是朝廷在缉捕他吗?”李静安道:“但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与朝。如今,他已经改名了,成了李林甫大人的外甥,名叫李护国。”李静钧道:“这家伙不愧是在官场混的,竟然瞒过了很多人。”
三
王维来到钱丰家,得知钱万贯正在练武场练武,便向钱丰先简单地说了情况,钱丰吃惊地道:“连你都见不到陛下,这该怎么办?”王维叹着气道:“要说见陛下,那是迟早能见的,但剿匪这事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不能耽误啊!”王淑娟问:“你觉得什么时候可见到陛下?”王维道:“这很难说,近期陛下很少坐朝,也许半个月,也许一月。”
钱丰摇着头道:“不行!别说半个月,就是几天都不知要死多少人。”王淑娟看了一眼丈夫的表情,犹豫着道:“要不,我去见陛下?”钱丰果断地道:“不行!这是男人的事,与你无关,你不能再见陛下。”王淑娟白了钱丰一眼,生气地道:“小心眼,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么多?”
这时,钱万贯与杨茹一起进来,钱万贯拉着王维的手道:“王维哥,莫非陛下答应剿匪了?”王维不无惭愧地道:“唉,哥哥无能,连陛下的面都没有见到。”钱万贯纳闷地问:“他既然召你回来,为何不见你?”王维道:“这很正常,陛下不可能随便什么时候都能见到,也不是谁都能见到。”钱万贯道:“剿匪是朝廷的分内事,又不是求人,你应该去找宰相。”
王维道:“我已经预感到,张大人之所以不向陛下进言,是受了玉真公主之托,我已见到玉真公主了,很不愉快。”钱万贯看了一眼王维的表情,不解地道:“怎么这样啊!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怎么弄复杂了?不就是剿匪吗?还说朝廷重视丝路,就是这样重视吗?那个宰相是怎么当的?”王维道:“有些事确实原本简单,但一旦跟有些事搅在一起,自然就复杂了。”
王淑娟忙道:“说到玉真公主,我倒是跟她有些投缘,要不我去求她?”钱丰犹豫了一下道:“好吧,为了家仇,你去吧。”王淑娟道:“家仇?难道死了那么多人,不该报仇?”钱丰觉得有理,当下大气起来道:“我和你同去求她。”钱万贯道:“我也去!”王淑娟看了一眼儿子想:“去了也好,这样玉真公主看到他,也许会更尽力。”便拉着儿子道:“行,我和你去,你爹爹就不要去了。”
杨茹忙道:“带上我?”王淑娟道:“不!那里虽是道观,但也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见她。”杨茹道:“我不是见她,是觉得万贯哥一走,感到没意思。既然是道观,除了不见她,去拜神像总可以吧?”钱万贯看着母亲道:“妈妈,带上妹妹吧?”王淑娟不无顾虑地道:“这是去求人办事,又不是去玩。”钱丰看着杨茹道:“茹儿,我看咱俩就别去了,你不是想学武吗?我教你!”
四
王维离开钱丰家后,心中很是自责,觉得小兄弟第一次求自己,而所求之事又是朝廷本来就重视的,到现在连皇上的面都见不上。忽然旁边有人喊道:“王维兄!”王维转脸一看,高兴地道:“李颀!”李颀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忙道:“是我,你这是上哪?”王维走上前去,微笑着道:“刚去了朋友家,正准备回家。哎呀兄台,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长安?”
李颀道:“我是奉旨来京,可等了三天也没见到陛下。”王维道:“原因呢?”李颀道:“据说陛下已厌政,整日与妃子寻欢作乐,众大臣也是无可奈何,忧心不安。”王维向旁一看,看到了李静安的饭馆,便道:“兄台,我们何不进饭馆一叙?”李颀高兴地道:“正想与兄台好好聊聊。”两人进了饭馆,小二笑着迎接,王维需要小雅座,但小二道:“雅座已满。”
王维看着李颀征求意见道:“要不我们换个地方?”李颀见这里环境不错,又见东北角空着,便道:“就坐那儿吧,反正只是叙旧,外面没多少人,倒也清净。”王维道:“好。”说着做出一个潇洒的手势道:“请!”李颀笑道:“你太客气了,咱们一起过去。”两人向东北角走去,立刻有小二宋三上前,微笑着倒好了两杯茶,并问:“二位想吃什么?”
在雅座里,李静安不解地道:“大哥,听你这口气,好像是希望他倒霉?”李静钧愤愤地道:“像他那样的人,纯粹就是咱家的败类。”李静安道:“哎哟大哥,你咋这么说?我们是小老百姓,能有个在朝廷里混的人,也是一件好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更何况,我们本来就活得艰辛,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也不需要品行。”
李静钧道:“胡说!像他那样的人,早该死了!”这时李静安的老婆李氏、女儿李侠进来,李静安忙道:“快来相见,我大哥来了,你们多敬几杯酒。”李氏要敬酒,李静钧愤愤地道:“今天的酒,我一杯都不喝!”李氏与李侠坐了下来,李侠道:“哎哟,怎么刚见面就不愉快?咋了?”李静钧道:“我们家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外面,王维听到雅座里的气氛不好,纳闷地道:“像是吵起来了。”李颀道:“不管他,我们说我们的。”王维道:“好!兄台前不久中进士,不知何处为官?”李颀道:“兄台应该知道,我是东川(今四川三台)人。少年时,曾寓居在河南登封。前不久刚中进士,现做新乡县尉。”王维道:“哎,陛下这次召见你,莫非要升你的官?”
李颀摇着头道:“不可能!我才为官,没什么政绩,哪能这么快?哎,不知兄台现居何职?”王维叹着气道:“前不久我升为凉州判官,却又被追回编纂史籍,却又见不到陛下。”李颀道:“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倒明白了。传旨官透露,好像就是让我来长安配合收集史料。”王维喜道:“如此说来,我们倒是在一起了?”
李颀点头道:“有可能。哎呀,能和兄台共事,实乃人生快事。兄台的诗才,令我十分欣赏。记得你有一首诗,让我回味了很久。”王维端起一杯酒来,示意李颀饮下,却问:“是哪首?”李颀喝下酒道:“是送高适的那一首,我倒是经常吟诵回味,现在吟给你听。”于是吟道:
少年客淮泗,落魂居下邳。
遨游向燕赵,结客过临淄。
山东诸侯国,迎送纷交驰。
自尔厌游侠,闭户方垂帷。
深明戴家礼,颇学毛公诗。
备知经济道,高卧陶唐时。
圣主诏天下,贤人不得遗。
公吏奉纁组,安车去茅茨。
君王苍龙阙,九门十二逵。
群公朝谒罢,冠剑下丹墀。
野鹤终踉跄,威凤徒参差。
或问理人术,但致还山词。
天书降北阙,赐帛归东淄。
都门谢亲故,行路日逶迤。
孤帆万里外,淼漫将何之。
江天海陵郡,云日淮阴祠。
杳冥沧洲上,荡漭无人知。
纬萧或买药,出处安能期。
王维感动地道:“多谢兄台!其实,我对兄台的诗也是非常欣赏的。”又与李颀对饮下一杯酒后道:“你的那首《古从军行》,就非常有意境趣味,令人高看。”于是吟道: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这时,李护国从门外进来,宋三一看是老板的哥哥,忙殷情地上前道:“哟,是您来了?这边请!你三弟正与你大哥在雅座里。”李护国猛地愣了一下道:“哦?”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满怀心事地走了进去。王维在他进入时,抬头看了他一眼,觉得好像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李护国一进雅座,李静钧愤怒地站了起来道:“是你?你还活着!”李护国不自然地道:“大哥怎么这样说话?”李静钧愤愤地道:“像你这样的人,就不该活在世上!”李护国道:“大哥,我和你可是亲兄弟,无冤无仇,为什么对我这么恨?”李静钧咬牙切齿道:“无冤无仇?还说亲兄弟?可你把我当大哥了吗?”李护国道:“哎哟喂,大哥为何要这样说?”
王维虽听不清里面说什么,但知道里面不快,便道:“怎么这人一进去,就越吵越凶了?”李颀边说话边倒出两杯酒来道:“看样子都是一家人,我们还是说我们的事。我先敬兄台一杯!”两人敬来敬去,很快就把舌头喝麻木了。两人本来神交已久,后来曾见过一面,现在相见,自然彼此欣赏。因此,两人天南地北地胡喧乱侃,不过无论怎么胡喧,倒是头脑还保持着清醒。
雅座里,李静钧怒道:“你以为你做的见不得人的肮脏事我不知道吗?”李护国故作糊涂道:“何事?”李静钧猛地一拍桌子道:“装啥糊涂?!你不但与杀人越货的沙匪勾结,还害死了不少丝路商人!不仅如此,你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做了数不清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李护国道:“哎哟大哥,你怎么胳膊肘子向外拐?不错,我是跟土匪勾结了,可我不那样做怎能发家?我不弄虚作假,又怎能做官?”
李静钧道:“可结果怎样,你照样成了钦犯!”李护国心虚地道:“小声。”说着拉开门向外看着,只见雅座外的客人都喝起酒来,猜拳行令,喊声一片,没有人注意这边。他装作若无其事,见旁边是王维与一个人聊天,立刻缩回头将门关上,压低声音道:“大哥,你有啥不满可以对我说,但不要大声,毕竟隔墙有耳。”
李静钧愤愤地道:“你若是心中坦然无愧,何必怕隔墙有耳?”李护国道:“大哥,你知道我是钦犯,当然要小心。我知道我做了缺德事,但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啊,你何必……”李静钧更加愤怒:“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晚的事。我女婿杨成泰就是被你派人装作土匪杀了,你还杀了我后来女婿的父亲,并因为你养匪为患,害得我这个女婿几次险些送命,你说你还是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