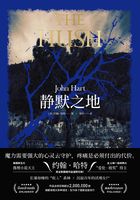一切的生命都在自然地繁殖、发达、死亡,或再生而延续,或沦亡而灭种。而人这种有着思维方式的特殊生命,却梦想根植万代,源远流长,成为永恒的血脉之河。
你的背景就是生命之梦灿烂繁衍的期冀,你背负着两个姓氏的希望,这希望是如火如荼的。这使你的生命有了异常复杂的内容。
你父亲你母亲切切地盼望着你媳妇为他们养个孙子,特别是你父亲老憨,梦想你媳妇生个双胞胎,你母亲眼光常常如柔柔的阳光,在你媳妇肚腹上扫来扫去,但你媳妇瘪瘪的肚腹不见丝毫的膨胀起来,这越发使你母亲着急了。
三月初八是三圣庙的年祭日,村里不例外地要给三圣母唱三天大戏的,庙里自然香烟如雾霾,传遍遐迩,你母亲心里勃然一动,领了你媳妇到三圣庙去乞神求子。庙殿里早已香烟如云,烟波在庙宇里发酵似的渤涌着。
殿地上跪满了粉黛如花的少妇。你媳妇推搡了一下一个胖得有些发肿的女人,那女人转过恶劣得出奇的胖面孔,很肥的嘴巴正要喷出什么脏话来,见是你媳妇,脏话便如口液咽下了肚里,恶险的脸孔瞬间变成一朵黑牡丹。你媳妇说:“满堂嫂子,你早来了。”满堂媳妇石女嘿嘿笑着说:“噢,是绪儿家的,你也来了。快,向前跪。”说着把胖身子向一边挪了一下,撞得身边那个瘦女人趴在了地上,见她气壮如牛,也就未敢说也未敢骂。石女给你媳妇挤出一方空地来,你媳妇挤了进去,给三圣母焚烧香表,嘴里轻轻说着连自己都听不见的话语,这话语是你母亲教给的乞神求子的表白。
云烟氤氲里,你媳妇看见两边立着的众娘娘都手里牵着个白胖的小男孩,小男孩赤裸的腿裆里都长着令人动心的小物儿,你媳妇偷偷地掐了个小物儿,忙装在花裹肚里,和满堂媳妇石女一块挤了出来。
回到家里,你母亲叫你媳妇倒了碗开水,将那小泥物儿冲服下去。你媳妇用水冲服时,口舌觉着那泥物木木的,有着河边泥腥物,咽到肚里很不舒适。她想呕吐,但在母亲面前只好强抑制住。
你媳妇没去庙院看大戏,你母亲却去了,你媳妇独自在炕上想满堂媳妇石女,想她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生下个娃儿,倒是越活越胖了,整天和野男人乱来,却不见生效。她想她好可怜。
日头正旺白的时候,大门外的老狗吠叫了起来。你媳妇出门去看,见你大舅来了。你媳妇忙迎了你大舅进去。回到老窑里,你媳妇忙给你大舅端了碗开水说:“大舅,走热了,喝些水。”你大舅一边接水碗一边贼溜溜地看你媳妇,没防碰落了碗,开水洒到腿腕上,你大舅被烫得如挨刀一般号叫起来。
你媳妇心里很歉疚,觉得太对不起大舅,忙说:“大舅,你坐着缓会儿,我给你做饭去。”说着她去了屋窑。你媳妇正在面盆里和面,你大舅笑嘻嘻地走进来说:“今日家里人都去看戏了?”你媳妇说:“都去了。”你大舅说:“你一人蹲在家里怪难受的。”你媳妇觉着这话难回答,没说什么,向你大舅笑了一下。你大舅给你媳妇这一笑,迷了心窍,色胆包天地从身后搂住了你媳妇。你媳妇忙说:“不敢,我把你叫大舅哩。”“不怕,没人知道。”你大舅毛蓬蓬的嘴脸像老叫驴啃桩一样直啃你媳妇的脖颈儿和脸孔,你媳妇急了,忙用面手来打你大舅,打得你大舅的脸面像大戏上的丑角脸子,滑稽可笑极了。这时你父亲老憨挑着山柴回来了,你大舅慌忙跑回老窑里,倒睡在炕上,用吐沫濡湿衣服内襟偷偷揩擦脸上的面粉。
正午,戏终了。你母亲回到家里,见你大舅来了,半是高兴半是生气。她知大哥不务正道,整天耍赌,怕到这庙会上又要玩赌的。
你媳妇端了饭盘来,先给你大舅双手懒懒散散地递了一碗。碗里丝丝细面条,线一般的细长,上面漂浮着红红绿绿的油辣炒汤菜,色彩鲜美极了。你母亲和你父亲礼让你大舅快吃,你大舅用筷子在碗里捞了一下,碗底泛上一堆黄黄的谷草节儿,这是喂老叫驴的。你大舅放了碗,说他小解一下去,出了大门仓皇地逃遁了。
你大舅逃得狼狈,脚步匆匆颠颠,脑里眼里尽是黄黄的谷草节,黄黄的谷草节渐而变得粗大起来,像一柄节节钢鞭,劈头盖脸地向他砸来,他身子一斜闪,“啊———”地掉下了塆南的红胶泥崖。正是日午,日头将旺旺的日光浇到红胶泥崖上,使红胶泥崖飘荡起旺红的雾翳,像你媳妇披的红盖头巾。你大舅掉下红胶泥崖的时候,他只觉身子一斜闪的瞬间,他如鹰鹞走于空中,身子很轻,轻得没了重量,像浮在红雾里,他在瞬间思忖他赴仙境了,他要去有仙女的界域去……在他失去知觉,未听得任何声息的同时,他的身躯像炸弹一样在红胶泥崖下轰起訇然的巨响,震动了庙院,庙院里的人们在震惊之余,都涌向红胶泥崖下去看你舅这个有炸弹一样轰动效应的人物……
你父亲和你母亲四眼斜斜地瞅着你大舅碗里的谷草节,好像都明白了什么。你母亲几乎晕倒,一种冷惨的感觉直入骨头缝里,使她浑身战栗不止。她颤颤抖抖地去了老窑里,见你媳妇伏在被卷上唧唧地哭,这愈发使你母亲气恼了,她恨不得将她这畜生般的大哥用刀宰了,你母亲走到你媳妇跟前,用手去抚摸你媳妇。你媳妇感到你母亲的手颤抖得厉害,震动得她心跳,她知母亲气恼非常,也就极尽了控制力,止息了哭泣,下炕去屋窑洗涮锅碗去了。
你父亲气恼得没法了,闷在地上抽烟,忽听门外老狗吠叫,以为你大舅回来了,便提了根棍子赶了出去,一看并无你大舅,是拴在老槐树下你家的那头黑得生辉的老叫驴起了性儿,将那长长的怪物一抖一甩地磕打着肚腹,惹得老狗汪汪地直扑咬吠叫。老狗似乎不知这长长粗粗的黑物是什么,或者觉得驴子用这东西向它挑衅,便狂狂地向老驴进攻。
你父亲老憨见这景象,将老驴的这骚情劲和你大舅的兽性在概念上统一起来,他愈发恼怒了,提起了棍子照着老驴肥肥的屁股狠狠地打了几下,棍子落在驴身上的声音很响亮,在山崖里反射出沉闷的回响,老叫驴经这鞭打,惊恐地绕着木桩跑了一圈,那长长的粗粗的怪物像条黑蛇龟缩了进去。老狗见老叫驴挨了揍,幸灾乐祸地回到石狮身边卧下去了。它见老叫驴没了怪物,感到很奇怪,用红红的狗眼不住地瞅老叫驴的胯裆。
你父亲在鞭打老叫驴的时候,恶狠狠地骂道:“我打死你这个老驴日的!我打死你这个老驴日的!”你母亲听见你父亲的骂声,神经灵敏地反应了一下,她自觉跟了她大哥受了奇耻大辱,便一头倒在炕上,泪水潸然地流泻下来。
你媳妇见一家人都未吃饭,便在灶洞里添了河捞柴,一扯一推地拽起了风箱,又重新做起饭来。青灰灰的炊烟又从你家屋窑外的烟囱上冒了出来,在晴和的天空上袅袅上升,如云如雾如纱如丝如梦如幻散发出一股泥腥味。
这刻儿,有人在大门外焦急地喊,说你大舅掉下了红胶泥崖。你父亲老憨听了这喊声,若无其事,在地上蹲着抽闷烟。你媳妇一听,吓得瘫坐在了灶窝里,颤抖的手,拉不动了风箱。你母亲慌了,
这时她忘记你大舅的一切不恕之罪,神情慌慌地向外跑去……
走向夏天。时序如飞鸟倥偬飞过,蝉的琴音骤骤切切,鼓荡着铿锵喧闹的音符。山野已是麦子波涛汹涌和果木结实微垂头颅的季节,收获向庄稼人蹒跚着走近。你母亲的眼睛依然盯着你媳妇的肚腹,你媳妇吃了三圣庙神孩儿那泥物已经几个月了,肚腹还是瘪瘪的,无丝毫地膨大。于是你母亲在乞神无济的时候想到了人,想到了妙手回春的陆九少。
你母亲领了你媳妇去陆九少家,走在河湾一片宁静、丰腴、散发着母体乳水味儿的绿草地,见一头母牛垂着沉甸甸的美丽乳头,在草滩上疯疯地吃草,活泼得像个孩子的牛犊在母牛的身边蹦来蹦去。你母亲眼里发痒,心里想你媳妇该像这头母牛一样,一样地给她养个像这牛犊一般活泼可爱的孙子。她怔怔地瞅着你媳妇的肚腹,蓦地见你媳妇的肚腹在一时之间如充气的气球一般,迅速地凸圆起来。她用耳朵贴近你媳妇圆大得像颗熟透的西瓜的肚腹,聆听胎儿的蠕动,她仿佛听到了胎儿叫奶奶的声音。她感激得老泪川流……你母亲身子一闪,倒在了绿草地上,她给一块石头绊倒了。你媳妇肚腹还是瘪瘪的,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你媳妇对你母亲的举动越来越感到神秘微妙,莫可理会,总觉她饥渴的眼睛里放射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光芒,刺向她的肚腹,使她生出隐隐的疼痛。她只懵懂地意识到母亲盼她给生个孙子。
到了陆九少家,陆九少正给你堂叔于孔礼把脉。你堂叔又黑了瘦了,黑瘦的身影显得很陌生很遥远,眼珠似乎陷入了深深的眼眶,有种空洞的感觉。他时不时地打嗝,每一打身体都要颤动一下,好像喉咙里塞堵着什么。他的脸孔黑黄,有着死亡的色相。他苦苦地巴望着陆九少,瞳孔中放射出痛苦的求生欲望。
你堂叔见了你母亲和你媳妇,冷冷地绷住脸孔上的悲痛,陡然脸色变得无丝毫血色,如蜡之白,眼里迸出仇恶的光焰。心里毒毒狠狠地咒骂:“你这个老婊子,你儿子弄掉了我的那物,你还想要孙子?!我咒你们断子绝孙!……”一阵心理发泄之后,他才稍微平静了些。陆九少微闭了眼目正在给他把脉,觉着他的手臂剧烈地颤跳,忙睁了眼目瞧他,见他嶙嶙瘦骨的脸上阴云涌动,知他怒火中烧便叫他静一静。他静了,静得像一具死人的骨骼。
你母亲自知你家和你堂叔家不和,怕讨了没趣,就缄口没招呼你堂叔。你媳妇出于小辈对长辈的尊敬,向你堂叔恭谨地说:“叔有病了?”你堂叔说:“好着哩,死不了。”顺手抓了陆九少开的药方,直直硬硬地走了。
陆九少也知事的由理,不生你堂叔的气,望了眼你母亲,问:“谁有病了?”你母亲说:“给绪儿媳妇看看,媳妇身子咋一直空着?”陆九少觑了一下你媳妇,说先把下脉。你媳妇有些忸怩,怯怯地伸出手去。陆九少竹节似的手指按住你媳妇的手腕处,半闭梦眼,把了会儿脉,睁大眼看了一会儿你媳妇的脸孔,说:“啥都好着哩,怕是这媳妇解怀迟。”你母亲说:“能吃啥药吗?”陆九少说:“不必的。”
这期间,你去了北山里讨了一次债务,却给你带来了烦恼非常的事体。
你去北山是你这生里第一次远行,你去的时候是带着你母亲啰唆不止的叮嘱和你媳妇绵亘无垠的目光而去的。去北山的官道儿,是脚户的骡子蹄子拓出来的,是盘着山脚转着河湾或绕着山峁的灰灰白白印着斑的骡马蹄印。山里尽是天然林木,繁茂的青翠苍绿。你行走匆匆,听着林阴里呖呖的鸟叫和野丛里偶然发起的兽啼,这使你益发地感到恐惧,索性脚步更快了。八十里山道,你早早地行完了。半后晌你就到了债家。
债家住在半山坳里。山里多木柴,债家自然是木柴篱笆院,三孔土窑。债家只有三口人,老者是债主的老父,女的是债主的女人,你见债主的老父成一根朽木,风吹就会倒的。老汉见你想说什么,可一张口就是不住声的咳嗽,咳嗽毕也未说出什么,弯着瘦骨萎缩的腰子走回北边的窑里去了,进了那窑,也未听见有丝毫的声音,你疑虑他怕死了。
那女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少妇,虽不如你女人漂亮,却浑身圆实,极富有生命力,能给人感召的诱惑。债主四十多岁了,是个态度极其诚悫的山里憨汉。他谦恭、惶恐地说:“再没出山,债欠久了,又劳了你跑趟山里。钱不够,我到邻家借去。”转身对她女人说:“你给客人做饭去,把客人招待好,我明日早晨就回来了。”说罢,扛了把镢头匆匆地去了。你问他女人:“去邻家,晚上咋不能回来?”那女人说邻家在山峁那面,十五六里路,很近。”你很诧异,这山里住户稀少,十多里还是近邻呢。
夜的黑影,鬼祟祟地从沟里爬了出来,用它掩盖一切的黑影笼罩了山野。夜,融入幽深寂静的黑色质体里,被风动,像梦的摇篮,晃动着,悠荡着。
你躺在黑色的夜里,想债家女人。
那女人对你特别客气,用特异的眼光看你,显得极其诚恳和朴实。傍晚她早早地喂了猪圈了鸡,早早地给你烧客窑里炕。在烧炕的当儿,你见她弯腰在炕洞口吹火,沉甸甸的乳房美丽地垂在胸前,仿佛乳香四溢。她的屁股高高地翘起,高高翘起的屁股,是非常的丰腴、浑圆,有着极其丰富的诱惑。在你眼里,她的屁股比你小表姨和毛胡小女人的都要美,虽然她不比她们娇艳。你真想上去摸一下她的屁股,你想摸一下的感受一定很动人。那女人回目向你憨笑了一下,好像发觉你的探密行为,你惶惶地转移了目光,向她很拙劣地笑了一下。她烧好了炕,给你铺了被褥,又向你憨憨一笑,说:“晚上睡了,掩上门,别插关了。”你当时只是急于应付,嗯了声,没来及思想什么。这时候,你躺在黑色的静谧里,解谜一样地思索起那女人的话来,为啥别插关呢?
在你苦苦思索的时候,你异常平静的心突然被一种美丽轻捷的声音困扰了,这是债家那女人的脚步声。脚步声径直向客窑里走来,仿佛走进你的心坎。门轻轻地推开了,在一瞬间的亮度里,你瞧见那女人的身影,你的心怦然一动,你好像感知了什么,激动不已。那女人掩上门,插了门关,又用烧炕的捅火棍顶了门。她在地上静寞地站着,像是一种等待,她用黑色的眼睛看着你。而后,她很快地脱了衣服,一下扑上炕,重重地压向你。你感到了一具柔轻如蛇的女性躯体的压力,使你浑身上下莫名地蹿跳着火辣辣的晕热,你急急用手去摸那柔美浑圆的屁股,你的手感到极其美妙,有多种无法意喻的内容,丰富着你的想象,诱惑着你雄性剽悍的蓬发,使你无法遏制地翻起身,将她赤裸的身子压在身下。她深深地吸吮着男人的气息,尽情地感受着男人粗野的威力和强悍的刺激……突然门外咚地响起一声撞击门的声音,你一阵急剧的战栗,脑里瞬间闪过一个非常的意念:债家两口合谋害你,想用奸计完了你的债。你听见那声音是债家扛的镢头击出的,一下慌了神,从那女人的肚腹上跌滚了下来。溘然,门外响起了母猪的哼叫声,你方知那咚的声音是母猪用头撞的,可你悟知迟了,那一声给你留下了难以治愈的顽孽症。
从你离开北山的那日起,你开始迎送一个又一个使你苦恼非常的日子。你回归家里,已是鸟雀归巢的黄昏,一家人见你讨了债早早地回来,都很高兴,你媳妇喜悦得脸上开放了花朵。你却心里很悲苦,好在夜里没有人发觉你脸上的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