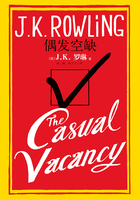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喀目老爹的故事,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是失落、同情、钦佩,还是别的什么,真的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夜已经很深了,我一个人躺在炕上,让自己的思想漫无边际地乱跑,从克孜老人满是褶皱的脸上,到一两百年前的图瓦人村落、失踪的孩子、一百多岁的喀目老爹,还有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踪影的可怕的东西……最后,我努力让自己的思想集中在多玛老师身上,想象她那双迷人的黄眼睛,还有挂在她漂亮脸蛋上的那一丝谜一样的微笑……我努力让自己陶醉其中,在陶醉中迷迷糊糊地走进只属于我自己的梦境……
吃过早饭,哈图骑马出去了,说是去湖边办点事儿。半晌午的时候,他骑着马兴冲冲跑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开始大声嚷起来:“湖里的怪兽出现了!”
“什么,怪兽?你看见了?”我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抓住哈图坐骑的缰绳。
“我没看见。是几个画画的人,和你一样从自治区来的,他们看见了。”哈图说着从马背上下来,把马往马圈那边牵过去。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拍到照片了吗?”我跟在哈图牵的马后面。
“那些笨蛋,吓坏了,都没来得及照相。”哈图把马拴到马圈门口的柱子上。
“他们说是什么东西呀,长什么样?”我不住地追问。
“他们说光看到一个头伸出水面,有小汽车那么大,黑黑的,样子有点像狗的脑袋。”哈图边说话边干活。他从马背上卸下鞍子,放到旁边的木架子上去。
“不说是大鱼吗?怎么又变成狗脑袋了?”我跟在哈图后面,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哈图向我伸手:“给支烟抽。大鱼是你们自治区来的大知识分子说的。我们这儿从来没人这样说过。”
我把烟和打火机掏出来放到他手里,说:“不叫大知识分子,叫科学家、专家,他们拍到过照片,我看过,像大鱼,红红的,一条一条。”
他抽出一支香烟放嘴里,点着抽了一口,把烟和打火机还给我,说道:“鱼和青蛙不一样,鱼不会跑到岸边上来。你也听说过吧,以前,有一群马在湖边上吃草,结果被湖里的东西抓走吃掉了几匹。”
“这是真的吗?我总觉得那都是传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看着哈图问。
“是真的,湖边上都能找到它啃剩下的骨头。”哈图十分肯定地说。
这话不假,我也见过一些动物的白骨。不过,湖怪这件事情比较复杂,谁也没法说清楚。就像不明飞行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管怎么样,我倒很想见见那几个画画的目击者,问问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我打电话给畅河,讲了刚才听到的事情。畅河反应平淡,说这样的事情在喀纳斯湖一年不知道发生多少次,听听就算了,别太认真。他还提醒我别忘了正事儿,尽量想办法把巴勒江那儿的石头人头搞到手,也不枉来趟喀纳斯。
这天下午,天气突然变了,乌云像黑色的毛毡一样遮住了天空,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雷声在厚厚的云层上面滚动,一道一道的闪电,像刀子一样“刷刷”地劈向地面,恨不能把屋顶劈开。随之而来的雨点,足有拳头那么大,眨眼的工夫把整个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我和克孜老人躲在他的木屋里,静静地望着窗户外面,谁也没有说话。雷声渐渐远去,雨还在哗哗哗地下着。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递给他,他接过去咬到嘴里。我用打火机给他点上。他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溢出来。他看了看我,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这个季节,不该有这样的天气。什么都变了,人也一样,世界也一样。”
“我都担心雷把房子劈了。”我说时抬眼看了看屋顶。
“那倒不会。雷该劈的地方、该劈的东西很多,还轮不到咱们。”克孜老人十分坦然的样子,对我摆摆手说道。
也就在这天、这个下午,也许就在克孜老人说上面这句话的时候,在喀纳斯湖东岸那个叫老爹谷的山坡上,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一棵足足活了几百年的高大的红松,被雷电从树顶到树根齐刷刷地劈成了两半!就像用利斧劈开一根柴火一样,干净利落。巧合的是,那块让自治区的人拉走的石板还是石头人,就是在这棵红松旁边找到的。还听说那棵红松身上流出了很多红红的血一样的水,把周围的草地都染红了。
“今天早晨湖面上露出一个黑色的大脑袋,长得像狗一样。”我看看老人,说。
“有时候眼睛也会欺骗人。”老人并不看我,只管抽烟。
“好几个人一起看到的,我想应该不会有错的。”我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
“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人是看不到的,难道看不到的东西就是错的吗?”
老人说话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得我都心虚起来,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老人的话。
是啊,老人说得没错。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所谓“暗物质”的存在。“暗物质”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但它们占据了差不多整个物质世界的四分之三。不过我相信,老人所说的“看不见的东西”与科学家界定的“暗物质”不是一个概念。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说得清楚一点,或者说,让人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说实话,我也没完全弄明白老人的意思。同样,对我来说,图瓦人村子里的孩子失踪是个谜,喀目老爹的失踪也是一个谜……
天黑的时候,突然“呼呼”地刮起了西风,风把天上的云像赶羊一样赶跑了。
天气一下变冷了,到处都是阴阴湿湿的,跟秋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