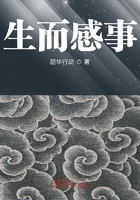)第一节 [外婆的旱烟管]
所谓念想,时时刻刻念着想着的,大都有一定的痴迷。苏青的外婆,可爱的老太太,把一根旱烟袋当了她的魂灵儿和精气神儿。
梁实秋从小吃到大的早餐,到了日后,不管是去了美国,还是台湾省,都心心念念着想着它的滋味,寻着它。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村子里的戏班子还是活生生的:台上紫云班,台下都走散。连连关庙门,东边墙壁都爬坍。连连扯得住,只剩一担馄饨担。
苏青
苏青自小是被寄养在外婆家里的,外婆家在距城五六十里的一个山乡。因为外公已经去世,舅舅在城里,家里只有她与外婆,还有一个姨婆、一个老妈子、一个奶妈,共5个人。外婆很疼爱苏青,在断奶后,常叫姨婆抱着她到处串门,苏青,是在很多爱的包容中长大的。
外婆有一根旱烟管,细细的,长长的,满身生花斑,但看起来却又润滑得很。
几十年来,她把它爱如珍宝,片刻舍不得离身。就是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也叫它靠立在床边,伴着自己悄悄地将息着。有时候老鼠跑出来,一不小心把它绊倒了,她老人家就在半夜里惊醒过来,一面摸索着一面叽咕:“我的旱烟管呢?我的旱烟管呢?”直等到我也给吵醒了哭起来,她这才无可奈何地暂时停止摸索,腾出手来轻轻拍着我,一面眼巴巴的等望天亮。
天刚亮了些,她便赶紧扶起她的旱烟管。于是她自己也就不再睡了,披衣下床,右手曳着烟管,左手端着烟缸,一步一步的挨出房门,在厅堂前面一把竹椅子里坐下。坐下之后,郑妈便给她泡杯绿茶,她微微呷了口,马上放下茶杯,衔起她的长旱烟管,一口一口吸起烟来。
等到烟丝都烧成灰烬以后,她就不再吸了。把烟管笃笃在地下敲几下,倒出这些烟灰,然后在厅堂角落里拣出三五根又粗又长的席草来把旱烟管通着。洁白坚挺的席草从烟管嘴里直插过去,穿过细细的长长的烟管杆子,到了装烟丝的所在,便再也不肯出来了,于是得费外婆的力,先用小指头挖出些草根,然后再由拇食两指合并努力捏住这截草根往外拖,等到全根席草都拖出来以后,瞧瞧它的洁白身子,早已给黄腻腻的烟油沾污得不象样了。
此项通旱烟管的工作,看似容易而其实烦难。第一把席草插进去的时候,用力不可过猛。过猛一来容易使席草“闪腰”,因而失掉它的坚挺性,再也不能直插到底了。若把它中途倒抽出来,则烟油随之而上,吸起烟来便辣辣的。第二在拖出席草来的时候,也不可拖得太急,不然拍的一声席草断了,一半留在烟管杆子里,便够人麻烦。我的外婆对此项工作积数十年之经验,做得不慌不忙,恰能如意。这样通了好久,等到我在床上带哭呼唤她时,她这才慌忙站起身来,叫郑妈快些拿抹布给她揩手,于是曳着旱烟管,端着烟缸,巍颤颤的走回房来。郑妈自去扫地收拾——扫掉烟灰以及这些给黄腻腻的烟油沾污了的席草等等。
有时候,我忽然想到把旱烟管当做竹马骑了,于是问外婆,把这根烟管送了阿青吧?但是外婆的回答是:“阿青乖,不要旱烟管,外婆把拐杖给你。”
真的,外婆用不着拐杖,她常把旱烟管当做拐杖用哩。每天晚上,郑妈收拾好了,外婆便叫她掌着烛台,在前面照路,自己一手牵着我,一手扶住旱烟管,一步一拐的在全进屋子里视察着。外婆家里的屋子共有前后两进,后进的正中是厅堂,我与外婆就住在厅堂右面的正房间里。隔条小弄,左厢房使是郑妈的卧室。右面的正房空着,我的母亲归宁时,就宿在那边;左厢房作为佛堂,每逢初一月半,外婆总要上那儿去点香跪拜。
经过一个大的天井,便是前进了。前进也有五间两弄,正中是穿堂;左面正房是预备给过继舅舅住的,但是他整年经商在外,从不回家。别的房间也都是空着,而且说不出名目来,大概是堆积杂物用的。但是这些杂物究竟是什么,外婆也从不记在心上,只每天晚上在各房间门口视察一下,拿旱烟管敲门,听听没有声音,她便叫郑妈掌烛前导,一手拐着旱烟管,一手牵着我同到后进睡觉去了。
但是,我是个贪玩的孩子,有时候郑妈掌烛进了正房,我却拖住外婆在天井里尽瞧星星,问她织女星到底在什么地方。暗绿色的星星,稀疏地散在黑层层的天空,愈显得大地冷清清的。外婆打个寒噤,拿起旱烟管指着前进过继舅舅的楼上一间房间说着:“瞧,外公在书房里读书做诗呢,阿青不去睡,当心他来拧你。”
外公是一个不第秀才,不工八股,只爱做诗。据说他在这间书房间,早也吟哦,晚也吟哦,吟出满肚牢骚来,后来考不进秀才,牢骚益发多了,脾气愈来愈坏。有时候外婆在楼下喊他吃饭,把他的“烟土批里纯”打断了,他便怒吽吽的冲下楼来,迎面便拧外婆一把,一边朝她吼:“你这……这不贤女子,动不动便讲吃饭,可恨!”
后来拧的次数多了,外婆便不敢叫他下来吃饭,却差人把煮好的饭菜悄悄地给送上楼去,放在他的书房门口。等他七律两首或古诗一篇做成了,手舞足蹈,觉得肚子饿起来,预备下楼吃饭的时候,开门瞧见已经冰冷的饭菜,便自喜出望外,连忙自己端进去,一面吃着,一面吟哦做好的诗。从此他便不想下楼,在书房里直住到死。坐在那儿,吃在那儿,睡在那儿,吟哦吟哦,绝不想到世上还有一个外婆存在。我的外婆见了他又怕,不见他又气,气得厉害,胸痛起来,这次他却大发良心,送了她这杆烟管,于是她便整天坐在厅堂前面吸烟。
“你外公在临死的时候,”外婆用旱烟管指着楼上告诉,“还不肯离开这间书房哩。又说死后不许移动他的书籍用具,因为他的阴魂还要在这儿静静的读书做诗。”
于是外婆便失去了丈夫,只有这根旱烟管陪她过大半世。
不幸,在我六岁那年的秋天,她又几乎失去了这根细细的,长长的,满身生花斑的旱烟管。
是傍晚,我记得很清楚,她说要到寺院里拜焰口去哩,我拖住她的两手,死不肯放,哭着嚷着要跟她同去。她说,别的事依得,这件却依不得,因为焰口是斋闲神野鬼,孩子们见了要遭灾殃的。于是婆孙两个拉拉扯扯,带哄带劝的到了大门口,她坐上轿子去了,我给郑妈拉回房里,郑妈叫我别哭,她去厨房里做晚饭给我吃。
郑妈去后,我一个人哭了许久,忽然发现外婆这次竟没有带去她的几十年来刻不离身的旱烟管。那是一个奇迹,真的,于是我就把旱烟管当竹马骑,跑过天井,在穿堂上驰骋了一回,终于带了两重好奇心,曳着旱烟管上楼去了。
上楼以后,我便学着外婆样子,径自拿了这根导烟管去敲外公书房的门,里面没有声响,门是应掩的,我一手握烟管,一手推了进去。
书房里满是灰尘气息,碎纸片片散落在地上,椅上,书桌上。这些都是老鼠们食剩的渣滓吧,因为当我握着旱烟管进来的时候,还有一只偌大的老鼠在看着呢,见了我,目光灼灼的瞥视一下,便拖着长尾巴逃到床底下去了。于是我看到外公的床——一张古旧的红木凉床,白底蓝花的夏布帐子已褪了颜色,沉沉下垂着。老鼠跑过的时候,帐子动了动,灰尘便掉下来。我听过外婆讲僵尸的故事,这时仿佛看见外公的僵尸要掀开床帐出来了,牙齿一咬,就把旱烟管向前打去,不料一失手,旱烟管直飞向床边,在悬着的一张人像上撞击一下,径自掉在帐子下面了。我不敢走拢去拾,只举眼瞧一下人的图像,天哪,上面端正坐着的可不是一个浓眉毛,高颧骨,削尖下巴的光头和尚,和尚旁边似乎还站着两个小童,但是那和尚的眼睛实在太可怕了,寒光如宝剑般,令人战栗。我不及细看,径自逃下楼来。
逃下楼梯,我便一路上大哭大嚷,直嚷到后进的厅堂里。郑妈从厨下刚棒了饭菜出去,见我这样子,她也慌了。我的脸色发青,两眼直瞪瞪的,没有眼泪,只是大声干号着,郑妈抖索索的把我放在床上,以为我定在外面碰着了阴人,因此一面目念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一面问我究竟怎样了。但是我的样子愈来愈不对,半天,才断断续续的迸出几个字来:“旱烟管……和尚……”额上早已如火烫一般。
夜里,外婆回来了。郑妈告诉她说是门外有一个野和尚抢去了旱烟管,所以把我唬得病了。外婆则更猜定那个野和尚定是恶鬼化的,是我在不知中用旱烟管触着了他,因此惹得他恼了。于是她们忙着在佛堂中点香跪拜,给我求了许多香灰来,逼着我一包包吞下,但是我的病还是没有起色,这么一来可把外婆真急坏了,于是请大夫啦,煎药啦,忙得不亦乐乎。她自己日日夜夜偎着我睡,饭也吃不下,不到半月,早已瘦得不成样子。等到我病好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
郑妈对我说:“阿青,你的病已经大好,你现在该快乐了吧。”
她对外婆也说:“太太,阿青已经大好,你也该快乐了吧。”
但是我们都没有快乐,心中忽忽若有所失,却不知道这所失的又是什么。
不久,外婆病了。病的原因郑妈对她说是劳苦过度,但——她自己却摇摇头,默不作声。于是大家都沉默着,屋子里面寂静如死般。
外婆的病可真有些古怪,她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哼,沉默着,老是沉默着……我心里终于有些害怕起来了,告诉郑妈,郑妈说是她也许患着失魂症吧,因此我就更加害怕了。
晚上,郑妈便来跟我们一个房间里睡,郑妈跟我闲谈着,外婆却是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郑妈说:这是失魂症无疑了,须得替她找着件心爱的东西来,算是魂灵,才得有救。不然长此下去,精神一散,便要变成疯婆子了。
疯婆子,多可怕的名词呀!但是我再想问郑妈时,郑妈却睡熟了。
夜,静悄悄地,外婆快成疯婆子了,我想着又是害怕,又是伤心。
半晌,外婆的声音痛苦而又绝望地唤了起来:“我的旱烟管呢?我的旱烟管呢?”接着,悉悉索索的摸了一阵。
这可提醒了我的记忆。
郑妈也给吵醒了,含糊地叫我:“阿青,外婆在找旱烟管呢!”
我不响,心中却自打主意。
第二天,天刚有些亮,我觑着外婆同郑妈睡得正酣,便自悄悄地爬下床来,略一定神,径自溜出房门。出了房门,到了厅堂面前,凉风吹过来,一阵寒栗。但是我咬紧牙齿,双手捧住脸孔,穿过天井,直奔楼上而去。
大地静悄悄,全进屋子都静悄悄的。我鼓着勇气走上楼梯。清风冷冷从我的颈后吹拂过来,像有什么东西在推我驾雾而行似的,飘飘然,飘飘然,脚下轻松得很。到了房门口,我的恐怖的回忆又来了,于是咬咬牙,一手推门进去,天哪,在尘埃中,在帐子下面,可不是端端正正的放着外婆的旱烟管吗?
带着颗喜悦的心,我一跳过去便想收拾,不料这可惊着了老鼠,由于它们慌忙奔逃的缘故,牵得帐子便乱动起来。我心里一吓,只见前面那张画着和尚的像,摇晃起来,瘦削的脸孔像骷髅般,眼射寒光,似乎就要前来扑我的样子,我不禁骇叫一声,跌倒在地。
等我悠悠醒转的时候,郑妈早已把我抱在怀里了,外婆站在我的旁边低声唤,样子一些不像疯婆子。于是我半睁着眼,有气没力的告诉她们:“旱烟管……外婆的……,魂灵,我已经找回来了。”
外婆的泪水流下来了,她把脸贴在我的额上,轻轻说道:“只有你……阿青……才是外婆的灵魂儿呢。”
“但是,和尚……”我半睁的眼瞥见那张图像,睁大了,现出恐怖的样子。
外婆慌忙举起旱烟管击着那光头,说道:“这是你外公的行乐图,不是和尚哪,阿青别怕,上面还有他的诗呢!”但是我说我不要看他的诗,我怕他的寒光闪闪的眼睛。于是外婆便叫郑妈快抱我下楼,自己曳着旱烟管,也巍颤颤地跟了下来。于是屋子里一切都照常,每天早上外婆仍旧坐在厅堂前面吸烟,通旱烟管,晚上则叫郑妈掌烛前导,自己一手牵着我,一手拿旱烟管到处笃笃敲门,听听里面到底可有声音没有。
外婆与她的旱烟管,从此便不曾分离过,直到她的老死为止。
)第二节 [村里的戏班子]
周作人
孙郁先生说:“绍兴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沿革所留下的旧迹很多。且不说传说中的大禹,以及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王羲之、陆游等文化名人,单是乡间的目连戏、社戏,以及各种节日的礼仪、习俗,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那些恬淡的、神秘而高古的乡间戏曲、街市小调,”它们“给周氏兄弟带来的快慰是长久的”。
去不去到里赵看戏文?七斤老捏住了照例的那四尺长的毛竹旱烟管站起来说。
好吧。我踌躇了一会才回答,晚饭后舅母叫表姊妹们都去做什么事去了,反正差不成马将。
我们出门往东走,面前的石板路朦胧地发白,河水黑黝黝的,隔河小屋里“哦”的叹了一声,知道劣秀才家的黄牛正在休息。再走上去就是外赵,走过外赵才是里赵,从名字上可以知道这是赵氏聚族而居的两个村子。
戏台搭在五十叔的稻地上,台屁股在半河里,泊着班船,让戏子可以上下。台前站着五六十个看客,左边有两间露天看台,是赵氏搭了请客人坐的。我因了五十婶的招待坐了上去,台上都是些堂客,老是嗑着瓜子,鼻子里闻着猛烈的头油气。戏台上点了两盏乌黮黮的发烟的洋油灯,咵咵咵地打着破锣,不一会儿有人出台来了,大家举眼一看,乃是多福纲司,镇塘殿的疍船里的一位老大,头戴一顶灶司帽,大约是扮着什么朝代的皇帝。他在正面半桌背后坐了一分钟之后,出来踱了一趟,随即有一个赤背赤脚,单系一条牛头水裤的汉子,手拿两张破旧的令旗,夹住了皇帝的腰胯,把他一直送进后台去了。接着出来两三个一样赤着背,挽着纽纠头的人,起首乱跌,将他们的背脊向台板乱撞乱磕,碰得板都发跳,烟尘陡乱,据说是在“跌鲫鱼爆”,后来知道在旧戏的术语里叫作摔壳子。这一摔花了不少工夫,我渐渐有点忧虑,假如不是谁的脊梁或是台板摔断一块,大约这场跌打不会中止。好容易这两三个人都平安地进了台房,破锣又咵咵地开始敲打起来,加上了斗鼓的格答格答的声响,仿佛表示要有重要的事件出现了。忽然从后台唱起“呀”的一声,一位穿黄袍,手拿象鼻刀的人站在台口,台下起了喊声,似乎以小孩的呼笑为多:
“弯老,猪头多少钱一斤?……”
“阿九阿九,桥头弔酒……”
我认识这是桥头卖猪肉的阿九。他拿了象鼻刀在台上摆出好些架势,把眼睛轮来轮去的,可是在小孩们看了似乎很是好玩,呼号得更起劲了,其中夹着一两个大人的声音道:
“阿九,多卖点力气。”
一个穿白袍的撅着一枝两头枪奔出来,和阿九遇见就打,大家知道这是打更的长明,不过谁也和他不打招呼。
女客嗑着爪子,头油气一阵阵地熏过来。七斤老靠了看台站着,打了两个呵欠,抬起头来对我说道,到那边去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那边是什么,就爬下台来,跟着他走。到神桌跟前,看见桌上供着五个纸牌位,其中一张绿的知道照例是火神菩萨。再往前走进了两扇大板门,即是五十叔的家里。堂前一顶八仙桌,四角点了洋蜡烛,在差马将,四个人差不多都是认识的。我受了“麦镬烧”的供应,七斤老在抽他的旱烟——“湾奇”,站在人家背后看得有点入迷。胡里胡涂地过了好些时光,很有点儿倦怠,我催道,再到戏文台下溜一溜吧。
嗡,七斤老含着旱烟管的咬嘴答应。眼睛仍望着人家的牌,用力地喝了几口,把烟蒂头磕在地上,别转头往外走,我拉着他的烟必子,一起走到稻地上来。
戏台上乌黮黮的台亮还是发着烟,堂客和野小孩都已不见了,台下还有些看客,零零落落地大约有十来个人。一个穿黑衣的人在台上踱着。原来这还是他阿九,头戴毘卢帽,手执仙帚,小丑似的把脚一伸一伸地走路,恐怕是《合钵》里的法海和尚吧。
站了一会儿,阿九老是踱着,拂着仙帚。我觉得烟必子在动,便也跟了移动,渐渐往外赵方面去,戏台留在后边了。
忽然听得远远地破锣咵咵地响,心想阿九这一出戏大约已做完了吧。路上记起儿童的一首俗歌来,觉得写得很好:
台上紫云班,台下都走散。
连连关庙门,东边墙壁都爬坍。
连连扯得住,只剩一担馄饨担。
选自《看云集》
)第三节 [烧饼油条]
梁实秋
梁实秋在读过唐鲁孙的《中国吃》后说:“中国人馋,也许北平人比较起来最馋。”他对北平的吃食充满了感情——“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各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北平的‘豆腐脑’,异于川湘的豆花,是哆哩哆嗦的软嫩豆腐,上面浇一勺卤,再加蒜泥。”
烧饼油条是我们中国人标准早餐之一,在北方不分省分、不分阶级、不分老少,大概都欢喜食用。我生长在北平,小时候的早餐几乎永远是一套烧饼油条——不,叫油炸鬼,不叫油条。有人说,油炸鬼是油炸桧之讹,大家痛恨秦桧,所以名之为油炸桧以泄愤,这种说法恐怕是源自南方,因为北方读音鬼与桧不同,为什么叫油鬼,没人知道。在比较富裕的大家庭里,只有作父亲的才有资格偶然以馄饨、鸡丝面或羊肉馅包子作早点,只有作祖父母的才有资格常以燕窝汤、莲子羹或哈什玛之类作早点,像我们这些“民族幼苗”,便只有烧饼油条来果腹了。说来奇怪,我对于烧饼油条从无反感,天天吃也不厌,我清早起来,就有一大簸箩烧饼油鬼在桌上等着我。
现在台湾的烧饼油条,我以前在北平还没见过。我所知道的烧饼,有螺蛳转儿、芝麻酱烧饼、马蹄儿、驴蹄儿几种,油鬼有麻花儿、甜油鬼、炸饼儿几种。螺蛳转儿夹麻花儿是一绝,扳开螺蛳转儿,夹进麻花儿,用手一按,咔吱一声麻花儿碎了,这一声响就很有意思,如今我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有一天和齐如山先生谈起,他也很感慨,他嫌此地油条不够脆,有一次他请炸油条的人给他特别炸焦,“我加倍给你钱”,那个炸油条的人好像是前一夜没睡好觉(事实上凡是炸油条、烙烧饼的人都是睡眠不足),一翻白眼说:“你有钱?我不伺候!”回锅油条、老油条也不是味道,焦硬有余,酥脆不足。至于烧饼,螺蛳转儿好像久已不见了,因为专门制售螺蛳转儿的粥铺早已绝迹了。所谓粥铺,是专卖甜浆粥的一种小店,甜浆粥是一种稀稀的粗粮米汤,其味特殊。北平城里的人不知道喝豆浆,常是一碗甜浆粥一套螺蛳转儿,但是这也得到粥铺去趁热享用才好吃。我到十四岁以后才喝到豆浆,我相信我父母一辈子也没有喝过豆浆。我们家里吃烧饼油条,嘴干了就喝大壶的茶,难得有一次喝到甜浆粥。后来我到了上海,才看到细细长长的那种烧饼,以及菱形的烧饼,而且油条长长的也不适于夹在烧饼里。
火腿、鸡蛋、牛油面包作为标准的早点,当然也很好,但我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接受了这种异俗。我心里怀念的仍是烧饼油条。和我有同嗜的人相当不少。海外羁旅,对于家乡土物率多念念不忘。有一位华裔美籍的学人,每次到台湾来都要带一、二百副烧饼油条回到美国去,存在冰柜里,逐日检取一副放在烤箱或电锅里一烤,便觉得美不可言。谁不知道烧饼油条只是脂肪、淀粉,从营养学来看,不构成一份平衡的食品。但是多年习惯,对此不能忘情。在纽约曾有人招待我到一家中国餐馆进早点,座无虚席,都是烧饼油条客,那油条一根根的都很结棍,韧性很强。但是大家觉得这是家乡味,聊胜于无。做油条的师傅,说不定曾经付过二两黄金才学到如此这般的手艺。又有一位返乡观光的游子,住在台北一家观光旅馆里,晨起第一桩事就是外出寻找烧饼油条,遍寻无着,返回旅舍问服务小姐,服务小姐登时蛾眉一耸说:“这是观光区域,怎会有这种东西,你要向偏僻街道、小巷去找。”闹哄了一阵,兴趣已无,乖乖的到附设餐厅里去吃火腿、鸡蛋、面包了事。
有人看我天天吃烧饼油条,就问我:“你不嫌脏?”我没想到这个问题。据这位关心的人说,要注意烧饼里有没有老鼠屎,第二天我打开烧饼先检查,哇,一颗不大不小像一颗万应锭似的黑黑的东西赫然在焉。用手一捻,碎了。若是不当心,入口一咬,必定牙碜,也许不当心会咽了下去。想起来好怕,“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粥”,这话不假,从此我存了戒心。看看那个豆浆店,小小一间门面,案板油锅都放在行人道上,满地是油渍污泥,一袋袋的面粉堆在一旁像沙包一样,阴沟里老鼠横行。再看看那打烧饼、炸油条的人,头发鬅鬙,上身只有灰白背心,脚上一双拖鞋,说不定嘴里还叼着一根纸烟。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使老鼠屎不混进烧饼里去,着实很难。好在不是一个烧饼里必定轮配到一橛老鼠屎,难得遇见一回,所以戒心维持了一阵也就解严了。
也曾经有过观光级的豆浆店出现,在那里有峨高冠的厨师,有穿制服的侍者,有装潢,有灯饰,筷子有纸包着,豆浆碗下有盘托着,餐巾用过就换,而不是一块毛巾大家用,像邮局浆糊旁边附设的小块毛巾那样的又脏又粘。如果你带外宾进去吃早点,可以不至于脸红。但是偶尔观光一次是可以的,谁也不能天天去观光,谁也不能常跑远路去图一饱。于是这打肿脸充胖子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烧饼油条依然是在行人道边乌烟瘴气的环境里苟延残喘。而且我感觉到吃烧饼油条的同志也越来越少了。
)第四节 [说书]
叶圣陶
因为是家中独子,叶圣陶从小就被寄予厚望,三岁时开始识字、练字,六岁时已经识字三千。父亲叶仁伯不主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常带叶圣陶去茶馆听说书、听昆曲。小书像《描金凤》、《文武香球》、《三笑》、《珍珠塔》,大书像《三国志》、《水浒》、《英烈》,他最多的听过三四遍,常常陶醉其中。
因为我是苏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谈谈苏州的说书。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如《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如《三国志》《水浒》《英烈》《金台传》,都不止听一遍,最多的听到三遍四遍。但是现在差不多忘记干净了,不要说“书”里的情节,就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说不齐全了。
“小书”说的是才子佳人,“大书”说的是历史故事跟江湖好汉,这是大概的区别。“小书”在表白里夹着唱词,唱的时候说书人弹着三弦;如果是双档(两个人登台),另外一个就弹琵琶或者打铜丝琴。“大书”没有唱词,完全是表白。说“大书”的那把黑纸扇比较说“小书”的更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诸葛不离手的鹅毛扇,赵子龙手里的长枪,李逵手里的板斧,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都是那把黑纸扇。
说“小书”的唱唱词据说是依“中州韵”的,实际上十之八九是方音,往往“ㄣ(en恩)”“ㄥ(eng亨的韵母)”不分,“真”“庚”同韵。唱的调子有两派:一派叫“马调”,一派叫“俞调”。“马调”质朴,“俞调”婉转。“马调”容易听清楚,“俞调”抑扬太多,唱得不好,把字音变了,就听不明白。“俞调”又比较是女性的,说书的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人,勉强逼紧了喉咙,发出撕裂似的声音来,真叫人坐立不安,浑身肉麻。
“小书”要说得细腻。《珍珠塔》里的陈翠娥见母亲势利,冷待远道来访的穷表弟方卿,私自把珍珠塔当作干点心送走了他。后来忽听得方卿来了,是个唱“道情”的穷道士打扮,要求见她。她料知其中必有蹊跷,下楼去见他呢还是不见他,踌躇再四,于是下了几级楼梯就回上去,上去了又走下几级来,这样上上下下有好多回,一回有一回的想头。这段情节在名手有好几天可以说。其时听众都异常兴奋,彼此猜测,有的说“今天陈小姐总该下楼梯了”,有的说“我看明天还得回上去呢”。
“大书”比较“小书”尤其着重表演。说书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半桌,偶然站起来,也不很容易回旋,可是像演员上了戏台一样,交战,打擂台,都要把双方的姿态做给人家看。据内行家的意见,这些动作要做得沉着老到,一丝不乱,才是真功夫。说到这等情节自然很吃力,所以这等情节也就是“大书”的关子。譬如听《水浒》,前十天半个月就传说“明天该是景阳冈打虎了”,但是过了十天半个月,还只说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冈子去。
说“大书”的又有一声“咆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阔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张飞喝断灞陵桥就是这么一声“咆头。”听众听到了“咆头”,散出书场来还觉得津津有味。
无论“小书”和“大书”,说起来都有“表”跟“白”的分别。“表”是用说书人的口气叙述;“白”是说书人说书中人的话。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说书人自己的声口,而“白”的部分必须起角色,生旦净丑,男女老少,各如书中人的身份。起角色的时候,大概贴旦丑角之类仍用苏白,正角色就得说“中州韵”,那就是“苏州人说官话”了。
说书并不专说书中的事,往往在可以旁生枝节的地方加入许多“穿插”。“穿插”的来源无非《笑林广记》之类,能够自出心裁的编排一两个“穿插”的当然是能手了。关于性的笑话最受听众欢迎,所以这类的“穿插”差不多每回可以听到。最后的警句说了出来之后,满场听众个个哈哈大笑,一时合不拢嘴来。
书场设在茶馆里。除了苏州城里,各乡镇的茶馆也有书场。也不止苏州一地,大概整个吴方言区域全是这批说书人的说教地。直到如今还是如此。听众是士绅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农民。从前女人不上茶馆听书,现在可不同了。听书的人在书场里欣赏说书人的艺术,同时得到种种的人生经验:公子小姐的恋爱方式,吴用式的阴谋诡计,君师主义的社会观,因果报应的伦理观,江湖好汉的大块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间,无法抵抗……也说不尽这许多,总之,那些人生经验是非现代的。
现在,书场又设到无线电播音室里去了。听众不用上茶馆,只要旋转那“开关”,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弦索声或者海瑞、华太师等人的一声长嗽。非现代的人生经验利用了现代的利器来传播,这真是时代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