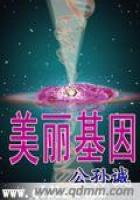我哭劲才刚刚过了些,却听见外头有不正常的脚步声,急切而有力,我抬起头去看,只见窗外人影攒动,看影像,根本不象是内侍的打扮,倒像是侍卫。我一惊,精神立刻清醒了些,意识到温融仍未回宫,心中便一紧。肃鸢这时进来,面色苍白,见了我与母后,立刻上前来道:“王后、世子妃,外头似乎不好了!”
母后依旧不闻不问的样子,我便着急问道:“何事?!”
肃鸢答:“奴婢见外头侍卫在大批换班,来守成阳颠的似乎不是原来的大内侍卫,看着衣服佩饰,眼生得很!”
母后这才有了些微动,眼神也恢复了,转头看向肃鸢,没言语,但是周身溢发出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魄。思忖片刻,她对跪在地上的首领内侍道:“你出去,以发丧为由,看看外头是何动静。”又对肃鸢道,“你机灵些,从殿后头出,绕到南宫门,那里的守卫应该换得最迟,你拿着我的掌印出宫,速见殷赞,叫他入宫勤助世子。”
二人领了命立刻出去,看此状况,母后是在防范温涟逼宫。而我念及温融如今在十里外的小沅城,哪怕即刻收到丧讯,赶回来也迟了,不禁心急如焚,思锄在旁边提挈我,叫我冷静。
可这样争权夺位、血雨腥风的大事,我如何冷静得下来。我怕温融不及进宫就被温涟拿下,姜华文昶如此狼子野心,难保不会除掉温融而后动啊!我愈发紧张起来,先前忍下的泪,如今都化成一滴一滴豆大的汗,从额上淌下来。
见我心思不定,在房内踱步,母后终于出声叫我,道:“你冷静些,融儿不会有事。”
母后一眼瞧穿我的心思,可我却依旧没出息,手脚发抖。
不一会儿,出去探风的成阳殿首领内侍回来,禀道:“成阳殿内外的守卫都已被撤换,世子的近卫队被圈在二宫门外进不来,诸葛队长虽正在和这班守卫的首领交涉,不过目前尚无起色。”
“……”这些话一听,我的心更是沉到谷底,这不是意味着,我与母后被软禁在这成阳殿了吗?!温涟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可以瞬间就将成阳殿换成自己的人马?!还有,他的人是如何进的宫、这大内兵马与京城守卫的兵权,不都掌握在殷赞手中吗?殷赞再不察,这样大的举动,怎可能逃过他的眼睛呢!难道……难道殷赞也被控制了……?不……不可能……温涟的封地远在华西苏地,兵力若要调动,不可能不动声色,既如此,他无兵马,就不可能掣肘殷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正思绪混乱,外头忽报公子殿下入宫奔丧。我一惊,立刻退身站到母后身旁,便见温涟一身孝衣,眼睛红肿,进来跪倒在了君上的遗体前。
我看着默默流泪的他,真的很难想像,他刚刚才冷静地发号施令调换了所有的兵马,就在他父亲尸身未凉的情景下,他要掀起一场弟夺兄位的宫廷争斗。
母后冷冷地看着他,讽刺道:“公子的紫薇宫离这成阳殿还真是远啊,丧钟敲了这么久,公子才姗姗来迟。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温涟不理会,在床前跪了快半个时辰,才起身,对我和母后道:“夜已深了,王后与世子妃今夜便在这成阳殿睡吧。”又问首领内侍道,“父王走时,你一直守在身边?”
那内侍还未回答,母后便冷道:“怎么,想知道你父王的遗诏放在哪里了?”
温涟亦冷笑,回头看了母后一眼,道:“是,想知道。哦……温涟倒忘了,这半年来,日日守在父王身边的是您,那么遗诏在哪儿,您应该是最清楚的?”
母后啐道:“你休想!”
温涟不痛不痒道:“王后可以不说,等世子的血流尽了再说,也不迟。”
“你说什么?!”一听见温融有不测,我像被谁用力捅了一刀,却不流血,只是冷汗涔涔。我什么都顾不上了,冲上来抓着温涟的衣袖问道,“你把温融怎么了?!”
温涟看着我,眼神竟有些木讷。末了,拉下我的手,道:“他出了小沅城便被围了,你说我把他怎么了?”
“你——!”
“不可能!”我方寸大乱,母后却镇定地厉声道,“他去小沅城有殷赞的人马护着,你和姜华文昶的那些散兵游勇,根本近不了他的身!”
温涟笑道:“那您认为殷赞是谁的人?”
殷赞……殷赞是……我如遭受晴天霹雳,说得通了,都说得通了,殷赞是他的人,就都说得通了……我腿下微软,可不敢倒,因为遭受震惊比我更大的人,是母后。她惊得往后连退三步,手撑在我的手臂上,刮出几道血痕。
我懂她的绝望,殷赞可是岭南杉门最大的一派军系啊,手握重兵,势力强大,岭南一带,除了东陵氏,就是他杉门殷氏了,更何况,这半年来,温融动手提拔,许他驻京,势力更是北延……这是温融自己养大的一只老虎,到头来却咬了自己!难怪,难怪这样重用,温涟与姜华文昶也没有相对举措,原来不是另有别招,而是请君入瓮!
温融……温融该怎么办……?!想完这些,我脑子已经冻结了,唯一还能考虑的问题,就是温融如今怎么样了。
却又听见温涟道:“他把诸葛良迎留在宫里头照应你二人,可那诸葛良迎不过一个护卫队长,丧钟一敲,他连二宫门都进不来!世子手谕算什么,若这天下将是我温涟的,您以为那些墙头草不知道该朝哪边摆吗?!”
又道:“我给您一个时辰考虑,一个时辰后若不见遗诏,休怪温涟无情!”
说完拂袖离开,我提起来的一口气忽然就掉了下来,我没有功夫去想其他,心心念念,只是温融的安全。
我小声问:“遗诏……要给他吗……?”
母后不出声,退身瘫软在了木椅上。
我心智全无,看着母后,眼泪又开始不停地流。
思锄这时上来,先告了罪,后回话道:“奴婢为旁观,说的话可能不好听,但一定比您与世子妃冷静。公子要遗诏,是要毁遗诏,只要遗诏被毁,他要争天下便名正言顺,而对世子殿下而言,遗诏在手,更胜千军万马,哪怕这一环输了,他日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所以,遗诏不能给;至于世子殿下的安全,奴婢想,殿下并没有落到公子手上,您想想,君上才才驾崩,他便动手阻世子的驾,天下人看来是什么?他不会这么傻,非但如此,他还会让殿下完好无缺地回宫,不过在此之前,他要做的便是夺遗诏,得到与殿下相等的王位继承权,如此一来,他可凭武力即位,却又不落个欺兄上位的名,纵使他位侯爷王族想讨伐,亦师出无名,若世子殿下欲召他位勤王,没了由头,谁还会出这个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