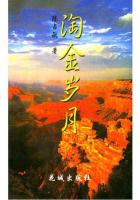从里斯本回来的李薇,还带回一个情报。
“这个情报,是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在里斯本的办事处无意之中透露出来的。”李薇对任可汇报:
“我去求援,直接找到了里斯本办事处的主任琼斯博士,他本人也是一位犹太人。我跟他说是你派我去的。一提起你,他便说,知道知道,我们知道任可博士帮助了很多的犹太人。他还善意地提醒,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同时,很多帮助犹太人的人也先后受到威胁与迫害,请你回去转告任博士,一定要注意,加以小心。”汇报至此,李薇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担心。
“我问他,是发现了什么迹象,有什么兆头吗?他回答,没有,目前还没有。不过,任可博士的这种善举,你们有的中国人也在“竞争”,据我们所知,日本人扶持的“满洲国”,也在通过他们驻柏林的“大使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不过,不是去上海,也不是去云南,而是去往“满洲国”,进入哈尔滨等地。据说那里早就有犹太人的社区,日本打算与“满洲国”联手,扩大或者新建安置犹太人的社区。”
“我们应该搞清他们的意图,调查与核实这一情报。”作为一国驻外领事馆,本身就有办理签证和调查搜集驻在国情报的职责,但是如何调查远在柏林的“满洲国驻德国柏林大使馆”对犹太人的动向,任可还是颇费踌躇。请民国驻德国大使馆调查吧,佟人川大使不像他的前任大使,对自己既熟悉又支持。
李薇看出了任可的为难,对他说道:“你不要着急,这件事你也不要直接出面了,有德日的支持,伪满洲国在德国和维也纳的特务活动也不少,你还是要小心,由我去想办法吧。”
几天以后,领馆新来了一个人,向任可报到。他摘下领带,从领带夹层里面取出一个小纸团,摊平了给任可看了一眼,是对他身份的介绍。然后直接了当地说道:“我叫奕非德,留学德国柏林,毕业之后就在那里工作。我是受“行政院六组”孔令侃的派遣,来到领馆加强对你的保护的。同时,我已经带来了伪满洲国为犹太人入境办理“签证”的情况的情报。”
任可看了那小纸条上的介绍与他的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孔祥熙、孔令侃那条线上的人。任可将那张小纸条点燃烧掉,听他详细地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39年初,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外交国务秘书威兹萨克召见了“满洲国驻德国公使馆”公使吕宜文,落座后,极为强势的里宾特洛甫劈头说道:“根据我国与日本国、日本国与贵国的关系,德日满成为“友邦国家”。但是,作为公使的您,也应该知道,我们德国,地处欧洲腹地,但人口多达七千万,生存空间和战略资源十分有限,不像你们“满洲国”,土地广袤而肥沃,相对来说具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且地广人稀。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你们也知晓,我们的元首和我们的政府已经决定,不能再让劣等的犹太“赘疣”吸附在雅利安人的躯体之上了,驱逐驱赶他们,是我们当前的“国策”。原本以为,英美法等大国会承接他们,但他们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接收,那就不如由你们来接收!”
一直期望强大的德国能够给予刚刚建立不久的“满洲国”以支持的吕宜文唯唯诺诺。
“我们也知道,在你们东北,早已形成了一个犹太人社区,你们具有接收和安置犹太人的经验。”国务秘书威兹萨克也说。
“我们既是“友邦”,必须互相扶持与帮助,特别是在一方遇到困难的时候。美国于1933年1月15日通告世界各国不承认“满洲国”。英国政府于1934年3月13日声称永不承认“满洲国”。我们的元首,曾经顶着中国的强烈抗议的巨大压力,宣布承认“满洲国”,才有你们的今天,可不要忘记咯……”里宾特洛甫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拖着长音说道。
“是是是,贵国对我国的支持我们会永志不忘。对于贵国向我国输送犹太人的计划,我本人不持异议。我当向我国总理立即禀报,并预作准备。”
“请你们立即妥为安排,为此事,我国已经特别设立了“犹太人出境办事处”。”
“照办!”
召见“商量”之后,吕宜文立即向张景惠作了汇报,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于是,吕宜文找来他的属下、书记官汪代尔,要求汪代尔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为离德的犹太人办理赴“满洲国”的入境签证。
最后,奕非德说道:
“据我们的调查,经这个汪代尔之手,已经办了不少的签证。看来这是伪满洲国与日本勾结的一个阴谋。上峰指示我加强对你的保护,同时想办法干掉或者至少吓阻这个汪代尔,使他不能毫无顾忌地实现他们的阴谋与计划。”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任可心想:要不是李薇在里斯本的美犹分配委员会偶然听到这一情况,要不是身在柏林的奕非德的初步了解,自己还不知道,岂但自己,国内外交部,也从未有人提起。
“事不宜迟,正好我要到柏林去述职,你们两个就跟我一起去柏林,好将此情况再搞清楚一些,然后向大使报告。”
任可一行三人风尘仆仆地赶到柏林。在去往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路上,任可表情严峻。
柏林,任可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在慕尼黑上学的时候,他来过,那时候的心境,混杂着崇敬与崇拜,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这座在欧洲和世界都很著名的大都市,它的历史、它的建筑以及包括了音乐、文学、哲学甚至体育在内的文化,都给了当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倾心于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莘莘学子,包括任可这样的优秀人才以深刻的印象。就是自己任职于德国之初,也曾经来过。那时任可专程往柏林去看望当时在任的程天放大使,程大使虽然是早已名满中国外交界的前辈,但任可与之相处和谐,受教不少。
但是,眼下的柏林,在任可的眼里,抛弃了儒雅、绅士的风度,显露出强悍与狰狞。满大街的花花绿绿的宣传标语口号,就像在这个有着不可胜数的古典的、艺术的建筑的城市脸上胡乱粘贴着的“疮疤”,而那些满大街你来我往、穿梭不息的雄纠纠气昂昂的人流,又像流动着的“赘疣”!他们高呼着“拥护元首”、“振兴德国”、“铲除犹太”、“消灭敌人”等等震耳欲聋的口号,身穿着黑色的、褐色的、灰色的、黄色的统一的服装,让人数不清这些个望而生畏的“组织”到底有多少种。他们有的举着枪,有的挥舞着棍棒,有的集会,有的游行示威,有的又发了疯的一般冲击这里冲击那里。呼啸而过的囚车的笛声与被打砸抢的人家发出的鬼哭狼嚎般的哀鸣,令这个城市在恐怖中战栗,又在战栗中陷入更深的恐怖之中,犹如人间地狱。
在经过火车站的时候,任可坐的车子被拦截了下来。原来,是进行交通管控,连步行的柏林人都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打开车窗的任可一行人,听见了被挡在路边的德国人的议论。任可一行人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幕:
正准备开行的一列火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专列”,将要被送上火车的人的最终目的地是中国东北的哈尔滨。这些人有两类。
火车站的月台上渐渐涌满了人。这些人全都肃穆、哀戚,但似乎都强忍着。他们的四周,布满了党卫军与盖世太保,那种德国盛产的狼狗也几乎无处不在。第一声火车汽笛拉响,准备上车和前来送行的人这才如梦初醒。开始,只可以听见相互告别的隐忍压抑着的声音和很小的啜泣之声,但这声音像是能够传染,接着便有人如丧考妣似地嚎啕大哭。火车月台上一时哭声一片。
“不许哭,快上车!”端着枪上着刺刀的党卫军和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只露出一个圆筒形状的盖世太保,命令他们,威胁他们,强行把相拥而泣的人分开,有的还用手推搡,用脚踹,用枪托打。催促上车的口哨声与狗吠响成一片。
“造孽啊造孽!”听到德国人在议论。
在火车月台上的这些人,一半是有着纯粹的犹太血统的犹太人,另一半大多是德国人。纳粹与盖世太保正在用他们奇怪的逻辑处置犹太人。他们的长官想出了这样一个折磨人的恶毒的法子:他们要坚决执行“德意志的意志”,就是上升为法律的“元首的意志”,他们要落实早已制定的这样的“法律”——德国人不允许和犹太人结婚,并且,已经结婚的也要离婚或者分开。他们现在,就正在执行这样的法律,将那些至今没有自行离婚和分开的家庭中的犹太人驱逐出去,应友好盟邦“满洲国”的盛情邀请,将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送往满洲国!
这样的送行与告别场面可想而知,任何记叙的文字都必然苍白,难述其万一。
待党卫军与盖世太保将这些被强行拆散的家庭中的犹太人赶上火车后,就紧闭上车门,而且,每节车厢之间原本能够连通的过道与小门也被关闭,不允通行。这时候,包括任可一行三人在内的被阻挡在车站边上的所有行人,又看见被押着走过来一群人,一群女人,一群年轻的犹太女人。
“啊,妓女,她们是妓女!”人群中有人惊讶。
“军妓、母狗!”有人不是同情,而是咒骂,“让这些肮脏的东西滚得远远的,不要再玷污雅利安的小伙子。”
这些女人不像平常的“性工作者”那样花枝招展,争奇斗艳,瘦、露、短、透的,却穿着清一色的类似于囚服一样的服装。
人群中发出了各种声音,有人不解,有人反对刚才那人的咒骂。
“你们是有所不知,这些女人,原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刚才那个出言咒骂的人,像是辩解又像是卖弄自己知道事情的原因,“你们听说过吗,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让我们那些优秀的小伙子,优秀的战士在攻打波兰时勇猛顽强,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并且不留什么遗憾,誓师之后,组织上统一安排他们“尝一尝女人的滋味”。最浪漫的,就是出发头一天,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女情人,甚至女志愿者,摇着小船,来到湖心,然后由他们自由鼓荡。”
“那和这些妓女有什么关系?”又有人对这位“卖弄学识”但却“顾左右而言他”的家伙颇有嗔辞。
“那么多的战士,有的还很年轻,难道都有女朋友和情人!不够了,就用这些妓女凑,这些妓女,就是发给那些出征的战士用的!用完了,留在我们这里是祸害,所以让她们滚蛋,走得远远的。”
任可想起了《羊脂球》,李薇想起了《金瓶梅》,一旁的德国人想起了什么,不知道,但是,好像人人脸上穆穆谔谔,只有那个家伙,还在喋喋不休……
任可一行三人来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见到大使佟人川,任可做了例行的“述职”,将领馆日常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汇报,然后,就向他报告了“伪满洲国”驻德“大使馆”的情况与他们的书记官汪代尔目前正在做的事。李薇又将从里斯本分委会听来的情况,奕非德也将他调查所掌握的德日满勾结的情况一一向佟人川细述一遍。最后,任可又将刚刚在火车站见到的凄惨的一幕作为补充与证明。
让任可还有李薇及奕非德三个人都没有料到的是,大使似乎对此事漫不经心,沉吟片刻,才说道:“对此事我们爱莫能助!”他望着他们吃惊的眼色,接着不紧不慢地说道,“现在,中德邦交处在十分微妙的时刻,搞不好就会触怒和触犯德国,我们最好不要插手。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复杂棘手的事情,目前我们先不要管。”
年轻的李薇与奕非德张张嘴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佟大使却挥挥手:“你们先忙你们的去吧,我和任可领事还有话说。”
奕非德一直在柏林工作,而且是行政院六组的,平日里与大使馆有往来,有朋友在大使馆办公室工作。“走,跟我去看朋友。”奕非德对李薇说。
“任博士,任总领,我曾经告诫过你,对犹太人要限制,勿过于热心帮助他们,你却好像没有听进去。我们本来是可以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看过去的事情,你却越弄越清,越弄越多,越搞越深,何时是了!”
“怎么,您站得高看得远,您得到了我国新的政策、外交部对待犹太人的新的训令或者是指示?”
“呃,这个嘛,这个倒没有,只是……”
“那么好啦,再没有得到新的指示之前,不是还要按照此前外交部的“训令”执行?您是外交界的前辈,我知道您一直是不遗余力地执行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我也是。”
“咳,你还太年轻,有些事体,从来就没有人说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哪!”
“您的要求,我回去会好好考虑一下,对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没有学会无动于衷,就是于心不忍。”任可看了一下佟人川脸上的表情,见他似乎陷入沉思,明白其实现在谁也没有说服得了谁,便以退为进:
“要不,等我回去后再向国内请示,看看有什么新的指示?”
但是,佟人川未置可否。
任可从佟人川的房间告辞出来,便来大使馆办公室与李薇和奕非德会齐。但是,正听到办公室主任穆启雄的一番话:“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知道任总领从维也纳来柏林了,就到大使馆来求告,说是请任总领帮助想办法,躲过这一阵风头后,就去维也纳总领馆办理签证,到上海的签证,然后再想办法与亲人在中国团聚。”
“怎么回事?”任可问。正说着的穆启雄扭身见任可进来了,便解释道:“现在还有几个人在大厅中等着呢。他们是留在柏林的被拆散的人,你见不见他们?”任可早就知道,穆启雄虽然是佟人川的左膀右臂之一,但是在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上,却不完全与冯大使一致,他在柏林对犹太人的遭遇见得更早更多,一直取同情态度。
“暂时不见为好,这种事情还是慎重起见。”任可没有办法对他和他们说清刚才佟人川的“意见”,再说,这里是由佟人川负责的德国大使馆,不是由自己负责的维也纳的总领事馆,哪能在这里见他们来办这样棘手的事情。而且,自己还要多了解一些情况。
“犹太人注重家庭,这我是知道的,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人,中国的家庭。但是,他们是德国人啊,就是他们想去,就是我们有办法让他们去,德国政府也不会允许他们离开呀。”
“他们说,这是纳粹与盖世太保在耍弄他们,折磨他们!”穆启雄又说,“纳粹对他们采用“双重标准”,相对于纯粹正统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仅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是非犹太人,需要集中力量集中重点打击犹太人的时候,将他们区别对待,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那些纯粹的犹太人;但是,相对于具有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德国人来说,在纳粹眼中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德国人,而是“犹太杂种”,适当时机也必须予以打击。他们告诉我们,纳粹拆散他们的家庭后,并不算完,他们已经听说纳粹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他们赶到波兰,所以他们急于想办法找中国使领馆,帮助他们去中国。”
离开大使馆,任可在回程的车上,对李薇和奕非德布置:“你们要秘密了解,作进一步详细的了解,这些人到底有多少真的愿意去中国,去上海,有谁能够到维也纳来而不是在柏林,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能帮的就一定要帮。如果我们不知道,就算了,也没办法。但我们不能眼看着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在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