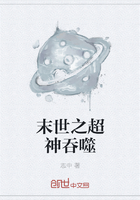看着他们四人那闷闷的样子,我难过极了。我知道此时四人所起的心思,因为我自己也不禁生出了那一种反思:加盟连锁似乎也不尽就有那么坏。至少,至少它真要比种地强比打工有希望。然而,——问题是,去哪呢?到哪里去呢?
我的眼泪突然止不住地奔涌而上,忙仰首闭目。黑暗中,我看不到天空。我似乎从始至终就不曾看到过北海的真正的天空。 我突然害怕极了。我发现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我们不过是狼狈地逃出北海逃出加盟连锁。一点也不潇洒。我们其实卑贱得可怜,我们甚至连自杀都谈不上。革命失败了,我们顶多不过是几个甚至都不能致牛德仁和潘昆于死地的的殉葬品。几具加盟连锁中沧海一粟般丑陋的死尸。这无疑将是场贻笑大方的“革命”。
3
弟弟的手机响了。是牛德仁打来的。他问接不接,几人先说不接后又让他接。有人找我,要我回个电话。是周兴明。
我打过去,他没接,一会他又打了过来。他问我发展好不好,让我多去串网抓紧写信打电话发电报。
我说:“也许是来得久了看到的尸骨多了,有时真的是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心惊肉跳,都不敢邀约不敢让朋友上来……”
周兴明说:“也许是你在家里呆的太久了,你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不把别人当作你的垫脚石,你就只有成为别人的垫脚石!”
我说:“别人家是新朋友到,我们家却只有老朋友走!而且,这个月……生活费……”
周兴明说:“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曾经所走过的!只要坚持,就必然会到达目的地!”
我问他说:“那你,你……你曾经,有没有,有没有和,和,和,——和上面的人冲突过?”
周兴明似乎考虑了一下才说:“你是不是对你上面的人有什么意见?”
“是的。上面的人,做得有些过份了!”
“你弟弟不就是你上面的吗?对他也有意见?”
“不是。是上面的……”
“你对他们有什么意见?”
我刚要开口,却见弟弟对我摇手示意,便忙改口说:“太多了。你有没有过这种事?”
周兴明显然又考虑了一下才说:“老同学,我只能对你说,你想得越多就会失去得越多。不要去问别人在做什么,在一楼的时候不要去想二楼的事,等你做上那个位置你就自然明白了!”
弟弟耳语要我问他多长时间上中级。他说十八个月。表弟说差不多。他告诉我说他父亲曾经来到过北海,要我相信做了对我只会有好处。
挂断电话,弟弟突然问我那天他说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我一时想不起他所说之事,表弟开口问,他就说出让我到周兴明下面去做的想法。不料表弟一听竟是立时拍手赞同,并当场表示他和表妹今后邀来的朋友也全带去加给我。施建平也满口同意,说只要把我一个人推上中级就行了。惟有施红军一言不发,一任额头那刀疤黯然无语。
三人一时就说得激情高涨,要我马上就再给周兴明打电话。
我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又回到了身负大家生死命运的那一个位置。我颤抖了。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还更高更重,自然也更加由不得我了。至少我必须得为上一次自导革命的失败有所表示有所付出。
弟弟拨通电话递给了我,那“嘟嘟”声立时就吓得我魂不付本。
周兴明问我有什么事,我半天放不出个屁来,忙抛蛇般将电话抛给了弟弟。
弟弟让周兴明过来吃烧烤。正说得激昂,不巧正好路过的藤川花子应召过来,他只好忙起身走开到一边去。
4
弟弟打完电话回来,张口就问藤川花子哪个会场发展最好,她一说“红房子”,几人就不禁相视会心而笑。
弟弟慷慨地给藤川花子要了一瓶啤酒非要她喝不可,又大声地喊上了一盘凉油粉、一盘炒海螺。
“我表弟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 藤川花子喝了一口酒,有些自言自语地说。“我第一个邀约的人是我表弟,最后邀约的一个人还是表弟!”言罢,只是喝酒。
弟弟问她说:“滕总一共邀过来几个人了?”
藤川花子喝了一口酒,神情木然地说:“前后一共二十八个!”
弟弟又问:“滕总来多长时间了?”
她闻言不禁呆视夜空,良久才说:“两年多了!”
施建平说:“滕总有几份单了?”
藤川花子毫无表情地说:“和胖总的差不多!”
几人不住追问,又说到都已面临死亡的家庭经济,直咒北海的天都是灰色的,说得原已消极不堪的藤川花子也不禁害怕似地起身先逃跑了。
表弟对着她离去的背影说:“她为加盟连锁付出的也够多了!为了新朋友去开房不说,还得为点生活费和牛德仁做爱。可要不是牛德仁,她早上中级了!”
弟弟骂道:“牛德仁这****的,平时骂这个流氓那个下贱,一副岳不群的样子,其实在背地里拿老子们的钱大吃大喝还搞女人!”
施建平忍不住说:“不是个个都说她家很有钱……”
弟弟笑说:“今天早上我老爸老妈还又当了一回优秀企业家呢!”
5
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几个只等我们起身好收摊关门睡觉的小工只不敢来当面驱逐。我们抿着早已冰冷的茶水,闷闷无语。我们懒得动。我们不敢动。我们怕进入下一个时空。最后的晚餐已经结束了,可是我们该去哪呢?我们能去哪呢?
“兄弟,借个火。”突然冒出个人来借火点烟,说。“好陌生啊,新来的?”
定眼一看,却是我刚到北海时来此吃烧烤要为我算命不成而替弟弟买了单的黄石的“公鸡”。只是他今晚又变成银都的“白鲨”了。而且,很显然,他今夜并非带着他的兄弟来消费,而是独自一人来消极了。
他本就是找着人来享受那份虚无的成就感以排挤无尽空虚及痛苦失落的,而弟弟他们马上又被他那副醉样滋长了免费晚餐的美妙念头,所以场面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当说到我们正因上面的人而准备打包走人时,他就再三追问我们是不是为上面的人做的,一时竟问得我们本已没有依托的心更加飘摇了。
弟弟他们又狡辩似地说不是自己不想做而是被上面的人搞得实在做不下去了。他就问我们中级是谁,我们是哪个会场的,当即便掏出手机来说他为我们给江锋打电话,可几人又不敢说了。
他就指责弟弟有没有好好带领我们学习业务知识打电话抓邀约,又断言说只有弟弟和表弟会走而施建平是绝不会走的。施建平就说正是他要带大家走的,因为他刚刚一次送走了十个兄弟般的朋友。他就追问施建平是不是为朋友做的,只说全中国十几亿人哪个不是潜在的邀约对象……
“兄弟,****的兄弟!有钱才是兄弟!”突然,不知从哪又冒出个人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我那个兄弟他竟然说他比我混得好……”
此人身后还有两人,都是喝得直流鼻涕了。场面一下子更热闹了,但叫人看着却再不知究竟是该哭还是该笑了。
不知为何,一人突然喊他为加盟连锁从家里调出了五万元钱,弟弟就喊自己调出了十万,白鲨只喊五十万,表弟大叫一百万……我终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一时只笑得眼泪“扑扑”作响。
我们的阴谋还未成形,他们的家人却寻来了。白鲨被人拉走,边走还边不住地回头让我们去找他,他帮我们去找江锋。
最后的晚餐终于结束了,没有人买单,得由自己付账。
弟弟骂声“失误”,只好伸手掏钱。一共六十七元五角,可弟弟却只掏出了六十元钱。我们一个个也都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那来收钱的女孩只好主动说算了。弟弟就趁机伸手在她屁股上捏了一把,说她将来一定能嫁个仅次于他的好老公。她一惊,扬手就要发火,但看了一眼我们的样子终只是骂出了“男人死光了”几个字来。
我们几人迈着醉步,摇摇晃晃,又喊又唱,疯疯癫癫地一路回到了楼下。
门早关了,弟弟和施建平伸脚就踢得山响。表弟忙阻住二人,打电话让藤川花子起床下来开门。
什么都睡了,世界好像已经死亡,只遗落下几个吃完了最后晚餐的人唱着摇摇摆摆的最后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