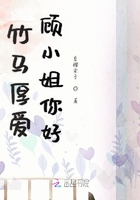眼光在他的眼、耳、鼻上逐渐攀爬而过,寻云坊中光影幽昧,幢幢在他面孔上交织流淌,每一个蜿蜒的弧度落在眼中,都即时在心里狠狠地砸出一圈明媚涟漪。话一出口,才发现声音原来已经是这样黯哑:“我不知道,”我埋了头,无数无处归去的血液一时在脸孔上充溢,透过皮层弥漫开大片稍带黯哑的粉红,指甲深深地扎进了手心,这一瞬间连这种疼痛也不真实起来,我茫然摇头,很是泄气:“我不知道,我是开玩笑的。”
他笑了起来,直立起身子,向我伸出一只手:“还不走?”
近在咫尺的面孔突然消失,越过他颀长的身形,我终于与一股细凉的清新空气相遇,逼仄感在广阔的天地中消失无形,但是那丝心灰意冷的感觉却挥之不去。
他静静站立在我面前,轻描淡写一句话便让我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可是他却见过这样多灵敏善巧长袖善舞的女孩子。我年轻的时候酷爱张爱玲,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范柳原的乐趣都是和白流苏作那种机智暧昧的游戏,应和着我此时的拙嘴笨舌,真是悲戚到山无棱天地合。活了23年,这是头一次让我意识到言情小说和韩剧在树立人积极向上信心方面的重要性,并为自己自幼缺乏这种正面教育而感到痛心疾首。
但是终究回不去了。我望着正在开车的苏乔,这座城市灯火并不辉煌,昏黄的路灯呼啸而过,苏大师眉眼俊秀,在这样的光影环绕中仿佛是一幅被刻意做旧的照片,而不是一个真实可触的人。我突然有点恍惚,他会不会有这样缅怀青春的时刻?如果有,那又该是如何值得缅怀的一场青春?
在这种时刻缅怀青春并助人为乐地帮助苏乔脑补青春显然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因为我很快发现事情开始往一个无法预知的方向发展:“苏大师,你往哪里开?你能找到路吗?”
他点点头:“当然能。”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死死地盯着他:“那你现在是送我回家吗?”
他开车之余侧过头微微笑着看我一眼:“我怎么知道你住哪里?”
我揉揉额角,实在不懂:“可你说你能找到路。”
他点点头:“是啊,我能找到去凌云山的路。”
这句话一分钟便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前面所有的感怀神伤,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苏大师,上山的路我找不到。”
他没有看我,唇边兀自绽出一点笑意:“有我在,不要怕。”
我撑着额头:“我的意思是我虽然是这里的人,但是我怕以我的能力,当导游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瞥我一眼:“我没有准备让你当导游。”
我哭丧着脸,终于不再进行委婉地表述:“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现在陪你上山吧?我没有准备啊,山上住宿很贵要钱,而且天气很冷,一定要穿厚衣服,现在我既没有带钱,也没有带衣服,还没有和家里说。”关键是,连心理准备也没有。
他车开得轻快,人看起来也是格外轻松愉悦:“那正好,我也没有准备,我们两个这是一场奇缘。”身子微微朝我这边侧了侧,笑意熏染中眉目尽舒:“很好,你终于不再拐弯抹角和我说话了。”
我直了直身子,严肃地说:“请注意行车安全。”苏大师一向是个富有执行力却缺乏基本沟通能力的人,如果我更豁达一点,我会承认他不和我沟通其实是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既然已经不声不响开到了这里,下车看来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想到这里,我打了个寒战,战战兢兢地按下妈妈的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显然颇为忐忑:“怎么样?今天没有出丑吧?”
母亲大人现在对我的要求如此低,这让我欣慰之余又有点心酸,一想起阆苑仙葩身上每个能让我奋起暴走的点或许在他们眼里都是正常的,这心酸不免又加重了几分:“没有出丑”,听着妈妈在电话那头略微松了口气,马上字斟句酌地加上一句:“但是可能也不怎么合适……”
接下来是如我所愿的暴动:“怎么又不合适了?”
我深吸一口气,对刚才不得以夸他的那句“英俊”进行精神上的鞭尸:“那个男生,相貌,不合适。”
这个理由显然让妈妈觉得很无语:“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虽然在苏大师面前我的智商情商和反应都要打上一个折扣,但应对这种话却是意料之中的游刃有余:“但是长得不好看可能会让人吃不下饭,吃不下饭可能会饿死,所以和这样的人相处,也是一种高危行为。”
趁着母亲大人正在惆怅,我颤抖着说出正题:“妈妈,我有个朋友来了,我现在要陪他去凌云山……”
电话那头妈妈打了个哈欠,似乎听见了一个笑话:“半夜三更去凌云山?”
我低声说:“是的,我现在要陪人去凌云山,没有时间回来拿衣服,事先也没有来得及和你们商量,我实在很异想天开。”我瞟了一眼身旁若无其事作出一派云淡风轻状的苏大师,咬咬牙说:“但是,这个朋友,他不止是我的朋友,更是白老师的朋友。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出什么事。但是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们可以去找白老师,让他负责。”
电话那头妈妈沉默了一下,似乎终于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良久,急促地问:“什么?你白老师哪个朋友?”
我望了苏乔一眼,正准备说出他老人家的大名,在这关键时刻手机中那丝轻飘飘的电流声突然中断,喂了几声都被那头的寂然吞没,我沮丧地放下电话,一看果然是不出意料地没电了。
苏乔微微抬了抬下巴:“没电了?我的手机在那里,你可以继续打。”
我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不用打了。”侧头迅速看了他一眼,说:“我相信你会对白老师负责的。”
他点点头:“这么说起来我确实是该对他负责。呆会儿我就打电话给他,叫他以后不要跟人说认识我。”
这一瞬间我很是泄气。想当年刚入学时,我凭借本科四年在中文系历练出的铁齿铜牙在众多同门之中所向披靡,一举荣获白门弟子中年度最佳毒舌奖。岂知到了苏大师面前,总是连连败退,溃不成军。这种挫败感简直叫人怀疑人生。
见我良久无语,倒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微勾了唇角,眼光在我身上浅浅一扫:“筠君,你究竟在怕什么?”
他一提醒,我顿时陷入思考,我究竟在怕什么?这一刻我却很明白,我紧张而慌乱,这种感觉远远大于单纯找不到路给我带来的恐慌。
他却不容我继续思考,直截了当地宣布答案:“你是在怕我。这么晚了还上山,你并不怕,你怕的是和我一起。”
我脸上烧得厉害,所幸的是有浓郁的夜色作掩饰,红得并不明显。长久以来一直躲避的问题被他轻易看出,还不留情地作了击破,虽然并不想承认,但是这一刻,我真的无话可说。只听见他的声音沉慢下来:“虽然我很久也想不明白,你究竟怕我什么。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那样伶牙俐齿,当时问我是请林志玲吃饭还是买充气娃娃回家,问得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感觉脸上越来越烫,似乎四肢百骸的血液都一时蜂拥入脑,忙不迭打断他的话:“苏老师,那个时候我口无遮拦,实在很没有礼貌。你千万不要见怪。”
车身微微一震,竟在路边停了下来,他转头看我,眼光之中尽是无奈:“看吧,又是这样的话。筠君,”他的眸色越来越浓,虽然黑不见底,但中间又有一抹闪耀的亮光,使得这样的黑却不同于夜色的寂沉,反而像沉浸了夜色的寒星,“你为什么要和我拉开距离?”
他的手扶在我的肩膀上,嘴角仍然噙了那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这样看我,我心里像是十月纷繁中的钱塘潮,心脏跳得仿佛要立即夺眶而出:“苏大师,你是成名大家,我只是一个学生,我们之间的距离,貌似不用拉开就相隔天涯了。”
他收回手,那丝笑意却越来越盛,低低说了句:“好吧。”踩下油门,车继续向前行。我心里怦然作响,十分狂暴,转眼望向窗外。
我似乎又出现了幻觉,刚才他虽然笑得开怀,可转眼的一瞬间,怎么好像有丝转瞬即逝的感伤淹没在这样明朗的笑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