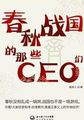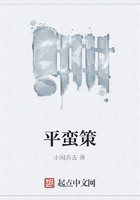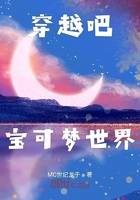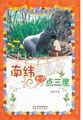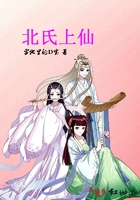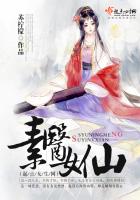会飞的桥,当地俗称藤篾桥。藤篾桥要用三条藤竹索横跨江面,牢牢地系在两岸的大树桩上,藤竹是独龙江地区的蔓生植物,最长的可达100多米,十分坚韧,经久耐用。两条在上方平行作为扶手,底下用一条,用竹篾将两三根大龙竹并排捆在一起用于脚踏,按江面的宽度把竹排连接起来。扶手索与下面脚踏的竹排之间再结上密密麻麻的细野藤条,或者竹篾条作为保护网,即成藤篾桥。独龙江对自己的子女很慷慨,两岸的森林里长着取之不尽的藤竹、野藤。藤篾桥修起来很方便,哪儿坏了修哪儿,经得住风吹雨打,万斤重压压不垮,被独龙族人亲切地称为“不断的桥”。
过藤篾桥,不仅要胆大,而且要会走。过桥时脚步要轻而快,不能与桥晃动的频率一致,否则藤篾桥会上上下下震荡不止;眼睛要直视前方,不能向下看,不能左顾右盼,否则,眼前是100多米摇摇晃晃的桥,脚下是汹涌奔腾的急流,您会觉得桥“飞”了起来,两岸连绵的山峦也跟着“飞”了起来,头晕目眩,非叫您趴下不可。因此藤篾桥又被称做“会飞的桥”。然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独龙族人背负百十斤重的行李过桥,却谈笑风生,如履平地。
溜索和藤篾桥,是独龙族人在这片山河艰苦创业的一个历史缩影。斗转星移,溜索已经不再是篾索,而是铁索了,安全系数大大提高;溜梆许多还是木头做的,有的人则用铁滑轮取代了木制溜梆。藤篾桥也不再是藤竹做成的,而是铁索的铁篾桥和钢索吊桥了,独龙江两岸江面、河流上已经架起了几十座铁索吊桥,但在一些高山河谷的偏僻地方,溜索和藤篾桥还在起着辅助的作用。
3.竹木筏和猪槽船
竹木筏,独龙语叫“嗖”,清末夏瑚在《怒俅边隘详情》里叙述:“……(曲人)不知为船以渡,只用篾索三根,平系两峰,虽以木槽溜梆,衔索系腰,仍需手挽足登,方能徐渡。”其实,独龙族是会用木筏或猪槽船的,在木静氏族的迁徙传说中就提到,他们祖先原来居住在独龙江上游的马必力河谷,后由于鬼怪的骚扰才乘木筏顺流南漂,分散到各地。
木筏是用龙竹或木头捆扎而成的,猪槽船则是把巨木挖凿成猪槽状,故称猪槽船,但独龙江落差大,水流湍急,旋涡险滩多,很多地段都不能摆渡。过去,只有在独龙江下游,在冬季水位下降,水位稳定的时候人们才用木筏或猪槽船摆渡,有几处固定的渡口叫“嗖砀”,后由于溜索、藤篾桥的普及,用得越来越少了。
(二)礼仪和禁忌
独龙族人在路上相遇,都要相互问候,问对方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去。遇见年长者,年轻的要给长者让路。长途旅行途中野炊,男子砍柴、女子生火做饭,临行时一定要留下一些干柴火,以便于其他人迅速燃火,节省时间赶路。
几个人同行,过桥要按顺序一个一个过,老年人和年幼者先过,不允许小孩子在桥上玩耍、逗留;走路也是一个跟着一个,不能随意超越别人,如果有人脚疼或生病落后,要有人陪同照顾,慢慢跟在后面,其他人先行,到宿营地安排露宿的准备工作。过去独龙族地区都是羊肠小道,独龙族人养成了走路一个跟着一个的习惯,即便是今天,一些山村的老百姓到县城逛街,在宽广的大街或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独龙族人一个跟着一个,饶有趣味。
独龙族人出远门,比如到行程十几天、荒无人烟的山里狩猎或采药,途中会把携带不便的粮食、衣物等物品悬挂在宿营地的树上,别人路过是不能随意取用或偷盗的,否则会受到山神的惩罚。这是独龙族人的信仰,也是每个人自觉遵守的道德。
独龙族人到高山上,忌讳大声喧哗、唱歌和笑闹,否则会引来暴风雪。翻越雪山垭口时,要从山下带一些石块、拄杖、钱币等,插放在以往过垭口的人堆砌的石堆上,这是祭献给山神的,以求平安,以往别人放置的东西不能翻动或拾捡。家中有人去世,一个月之内一般不翻越雪山,否则登山会感觉十分劳累,脚上仿佛绑着大石块,独龙族称这种现象为“阿莫尔”。
(三)对外交通和现代交通
独龙族地区过去的对外交通十分困难和凶险,随处是激流和绝壁,独龙族就靠原始的溜索、藤桥、天梯等与外界交往。
过去,独龙族到缅北寻亲访友或交易物品,从独龙江北部出发要翻越担当力卡山脉,道路十分艰险,这些路上尽是悬崖峭壁,要常常攀缘天梯,行程四五天才到缅北托洛江流域的独龙族村寨。从独龙江中下游到缅北去就顺江流而下了,但一路上也有数不清的激流绝壁,要过很多独木桥、藤桥和溜索。到缅北的坎底(今葡萄县城)要顺江走十多天到缅北龙蒙(乡),绕过担当力卡山脉,转向西再走六七天才到坎底。独龙江的居民很少到坎底去,多数最远也就到下江的几个独龙族寨子,春夏季节一般不去缅北的,缅北天气酷热、潮湿,迄今多瘴气(疟疾病)。
北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境内,要沿着独龙江上游的马必力河,翻越高黎贡山两座雪山后先到怒江边的札恩,再溯怒江而上,需要5天时间。过去察瓦龙土司到独龙江征收赋税、放债交易,独龙族人到察瓦龙谋生,都是往返于这条山路。往东到怒江沿岸都要翻越高黎贡山,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有古道通达,行程需要三至七天不等,都很艰险难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1964年政府组织当地人民先修通了县城丹当到独龙江巴坡(原乡政府所在地)的人马驿道,行程时间从原来的七天缩短为三天,大大拉近了独龙江和内地的距离。1999年7月1日,县城到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孔当的“独龙江公路”竣工通车。今天的独龙江,虽然每年还有半年左右的大雪封山,但交通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独龙江村村通了公路,每条河流上都架起了汽车也能奔驰的钢索吊桥了。
二、通信方式
独龙族历史上没有本民族文字,语言的使用又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就广泛采用刻木和结绳来记事和传递信息。
(一)刻木和结绳
刻木和结绳是中国远古的记事和传递信息的手段,在中国古代史书上就有上古伏羲、神农时代“刻木、结绳”的传说。
独龙族的刻木,过去主要是用于传递土司的命令和本民族之间交往的记事,也用来作为借债、赔偿和结婚彩礼的凭证。刻木的长度约2尺,宽2~3寸,木片的两边斜平,便于刀刻。木刻的一端呈箭头状即头部,另一端齐头为尾部。木刻的上部刻官方的情况,下部刻民方情况。例如,木刻的左边上部刻一大口,表示要来一位官员,下面刻有几个小口表示官员要带来几个随从;木刻上部的另一边刻几个较小的口子,则表示官员要带着几个背夫。木刻中间如果刻有横线,则表示要修好路,准备好住宿和饮食。如果刻有一个两条线交叉的图形,则表示要在某天来到并一定要在那个村住宿。木刻下部还经常拴有各种不同的物件表示不同的意思:若拴有箭头,表示要像箭一样很快抵达;若拴有辣椒,则表示事情如果不办妥,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若拴有鸡毛、火炭,则表示事情很紧急,要迅速把消息传达到各村各寨。木刻要由各村寨传送,送木刻的人,送到便解释,人们见到木刻便立即明白传来的信息。木刻送到哪个村,哪村就立即派人传送至另一个村,中间不能停留,直到送达各村为止。
亲戚朋友之间借用东西,如粮种、锅、锄头、砍刀等,也常常用木刻来计数。不同的物品刻以不同形状的缺口,在两边刻相同数字的缺口,再将所刻木刻分为两半,分别各存一半,等借用的东西还清时再将木刻销毁。
木刻也可用来计时。如两个朋友相约几天后在某个地点相会,就在木刻的两边刻上相同数目的缺口,一个缺口表示一天,双方各持一半,隔一天削去一个缺口,木刻削完的那天就是两个人同时在相约地点碰头的那天。
结绳用于日程的安排方面。例如,如果出门的时间很久,如上山狩猎、挖草药等。为了能够准确地记录出门在外的时间,独龙族常带一根绳打结,每过一天打一个结,回到家时再数结,便知道了此次出门的天数。结绳也可用于日期的约定方面,这和木刻计时相似,约定日期的天数是多少,就结几个结,每过一天或每走一天就解开一个结,等所有的结解完时,便是约定聚会的日期。
今天,刻木和结绳在独龙族的生活中很少见了,许多年轻的一代已不知刻木和结绳为何物,他们用纸和笔记录事务,用钟表和日历安排日程。刻木和结绳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漠,成为书本上的历史。
(二)现代通信手段
1954年,贡山县建立了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邮电局,开始开展邮政电讯及报刊发行工作。邮电部门在短期内架设了长途电话线,改变了以往贡山跟内地联系全靠函件的状况。1957年,独龙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邮电所,但山路依然艰险,通信靠的是信函和口信。1964年独龙江人马驿道修通后,1966年初,云南省邮电局拨款4万元,开始架设独龙江电话线路,到年底架通了县城到独龙江乡的线路。至此,贡山实现了各区(乡)通电话。到1969年,独龙江各区除最北的迪政当村以外,每个行政村都通了手摇电话。
高黎贡山的大雪,一直是独龙江对外通信的障碍,每年封山期间,电话光缆和线路几乎都会被雪崩冲毁。遇上紧急事件,独龙江的人们只能靠电台与内地联系,独龙江宛如与世隔绝。独龙江的人们无奈地戏称《人民日报》为“人民年报”,《半月谈》杂志为“半年谈”。2004年10月,中国移动独龙江基站建成开通,现在每个行政村都通了手机,很多独龙族干部群众都用上了手机,美丽的独龙江跨入了数字通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