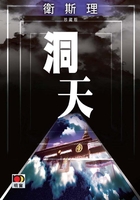布达拉宫广场上,列着一个个女兵方队,在这些女兵当中,有刚入伍不久的,有即将要当母亲的,有已经当了母亲但远离自己子女的,还有当了母亲却失去儿子或者失去女儿的……她们静静地列队准备接受藏族群众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检阅。
一位将军,一位被兵们亲切称作“老嘎”的嘎玛泽登将军,他昂首挺胸呼喊“长期建设西藏”,女兵方队整齐回应“坚决保卫祖国边疆”。这个声音伴着数只腾空而起的鸽子传播开去,使遥距万里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高原女兵的飒爽英气。
在藏族群众的欢呼声中,女兵们开始迈着坚定的步伐行进。太阳动容地停住脚步,把它的金发绾成数捆油菜花递给女兵们,就有一支我从没听过的《女兵之歌》在方队里唱响,每一个手抱油菜花的女兵都涨落着金黄的潮汐,整座高原便沸腾起火山喷发般的血液,朝我沉默已久的脉管不断注入……
当然,这个诗一般的阅兵场景在现实中不曾有过,今后也不大可能有,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仅仅属于我个人的梦幻现实中。
即便无情岁月悠然而过许久了,我依然还能听到那些女兵的歌声在世界屋脊回荡。而她们的脚步,她们的精神,还有她们被强烈紫外线灼红的脸膛,她们抱住油菜花的那一双双生着冻疮的手……无不体现出中华女性的一种独特的献身精神。
每当回味由我创作的那个阅兵场景,都有一种极美的感动,犹如神灵为我新塑了一个可以超越任何现实的魂灵。在这个回味过程中,我所经历的那种心灵升华的美妙境界真是难以描述。也正是在这个回味过程中,我写下了中篇小说《兵子弟·子弟兵》。可惜由于我的艺术生涯的不成熟,最终没能在这部作品中完整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使我留下太多的遗憾。但幸运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毕竟重温了一遍我童年生活中的一些精彩片断,这是上界的神明也不可能帮我做到的。
我还得感谢一位叫马萧萧的军旅诗人,他为《兵子弟·子弟兵》写来一篇读后感《童年的酿造与酿造的童年》——
金黄是一种宝贵的颜色。我以为,它与黄金二字的区别,仅是排列顺序的不同而已。
在那片金黄的油菜地旁,在那片金黄的憧梦里,一群十岁上下的“兵子弟”,身披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阳光,从作家薛晓康笔下向我们跑来了——
钟高原一把沙土扬起,飞往黄马肚下的黑色肉棍;张小飞把钟高原的“总司令”给炸了,可钟高原谎称他爸爸是总司令,张小飞只好说那就算你赢了吧;王莎莉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正与外国人打仗,杨小刚的钢笔不能用,并要检查那钢笔里是否有放情报的机关……
杨小刚呢?杨小刚当了小组长,分苹果时他只能把最小的留给自己,可要让出小组长这个位置,他还真舍不得;他把鲜花握成冲锋枪,欢送曾经恐吓过他的速成班高个子同学;他“啪”的一声将寝室的大玻璃打碎,举着受伤的右手,像举着一朵鲜花,并在缝了三针之后把小酒窝笑成大酒窝;你们就不敢用手打玻璃吧;他想看男金鱼与女金鱼的那地方有什么不同,并最终以王莎莉看过他雀雀为名,名正言顺地巡视了她的那地方……
独特的生活经历给了作家以独特的观点视角。三十多岁的军旅作家薛晓康,竟把一群三十年前的儿童的言行与心理,描绘得如此锥心刺骨,不能不让人叹服。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一脉童年留下的珍贵矿藏,那是童心酿造的琼浆!这位沧桑者的深刻才能在孩子般的天真单纯中得以艺术地表现出来,作品才具有了真正的审美意义和引人共鸣的感染力。
这种“沧桑”与“天真”的反差,增添了作家薛晓康的主体魅力和创造表现力。
如果你误以为作家在此苦心经营的是一篇“儿童文学”,那就大错特错了。
随着故事的步步深入,作家极不情愿地在孩子们天真的笑语里,活泼的举止中,披露一幕幕他试图极力隐藏,但却怎么也隐藏不住的感人故事。那位喜欢亲杨小刚小雀雀,让他做了最初一半金黄色梦的小阿姨死了,死在海椒地里,一丝不挂。杨小刚妹妹得了肺炎,病死了;公路上挑土的人倒下去,饿死了;连那位听说他们的名字叫“高原”,便怒火顿熄的李大叔也倒在猪圈里死了,死在杨小刚还弄不清为何物的“自然灾害”里了。在“自然灾害”的日子里,杨小刚发明的“舔蜜解馋”,则让一群马蜂把王军那年幼、勇猛的生命和永远的梦想给活活夺走了。
真切的感受在作家的手中并不是平铺直叙,也不是信马由缰地倾泻感情,而是极为精细、机智地描绘那一段生活经历(历史)给予他的境界。他营造氛围,推敲语言、揣摸童心、回望生活、体验过去,看得出,这是薛晓康倾注了心血与激情的累心之作。
奇怪的是,这一切在作家笔下都发生得那么轻巧,那么自然。而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飘满了带雨的阴云。每一次死亡的发生,似乎都是一撮绝妙的养料,小树般欣欣向荣的孩子们,因了它而拔节、绽叶,直至田老师从他们瞳孔中变成那一片永远的金黄,他们不由得开花结果,一下子长大了十岁、二十岁……
现在明白了,作家薛晓康表面上写的是一群孩子,一所部队子弟学校师生的经历。事实上,他是通过孩子们的见闻、思想,来展示那特定历史条件,我们军人及其子弟的欢乐与痛苦、友谊与冲突、振奋与迷惘——不用说,那是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牺牲与奉献。他是在天真中表现沉重,在笑声里展示隐痛。这种表现与展示,难道不比直接倾诉更见小说家的功力吗?
这是作家薛晓康的独特之处。
巧妙的构思,绝好的伏笔,就不必再提了,而精神的语言却让我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咯咯咯地扭着腰肢走了——多么轻松而又形象。
要叫马大叔叫李大叔——对童心的体悟在语言上的流露。
黄医生伏在桌子上,呜呜地——简洁而又生动。
“就可以”和“就不可以”惊动了整个宿舍楼——绝妙的语言概括力。
哭声召唤生长记忆的雪。雪花惶惶飘来——含情的叙事与形象生动的表达融为一体。
王莎莉“哇”的一声,立即勾引出集体的“哇”——两个“哇”竟然哇出了情和景。
……
作家薛晓康应该是一位诗人,他对语言的把握,是如此的熟练、别致。他的小说语言,在轻快中饱含沉重,既简练又不失内蕴,虽飘逸但不游离。他是在通过对语言自身功能的不断完善,多侧面地制造情绪、强化氛围,最终达到表现主体的目的。使人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在许多类似的作品中,我很少能见到这样对小说语言如此精心的作品,我看重这篇作品的另一个原因便是作家薛晓康对语言的刻苦与用功。
以上只是我信手拈来的几段文字,并仅仅披露了我对作家薛晓康这篇杰作的一点儿激动(也可以说是我写这篇读后感的理由吧)而已。而对作品的全面把握,还得靠读者您自己。
相信小说《兵子弟,子弟兵》能对广大业余作者在军旅文学式微的今日突破重围、走出困境,会有些有益的启发。
这样说来,这部小说,不仅在我们记忆里铺展了一片永远的金黄,更在我们笔触里浇铸了一片永远的金黄。
我曾经给我姑妈讲过一些我的作品里的内容,我以为总会有点儿什么可以感染她,并为我而感到骄傲。可是,姑妈听了以后并不激动,只是笑着说,如果你真的这么喜爱写作,那你应该多去晒晒太阳。
晒太阳?
对,晒太阳,要多晒。凡是被太阳晒过的东西,都会有它自己的故事,你只要能把它好好写出来,别人就能感受到阳光。当然啦,你自己得首先感受到阳光。瞧见了吗,扎西和达珍捡回来的这只小流浪狗,还有这些个破烂儿,你知道它们都有什么故事吗?不知道吧。嘿嘿,我也不知道,扎西和达珍可能更不知道。但肯定有,肯定有哇。被太阳晒过的东西,不管是人也好,是动物也好,是一块小石子儿也好,那都是有故事的。
我愣愣地看着没有多少文化的姑妈,觉着这番话不像是从她嘴里讲出来的。我有些振奋,问,姑妈,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
姑妈说,你记得不?德清次珍,就是那个成天笑哈哈的巫师,记起来了吧?她早告诉过我,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我们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待你哪天写不出故事了,就去太阳地里待上一会儿,说不定就会想出别人愿意听的故事。不信你试试看,试试就知道了。太阳好哇。唉,太阳……太阳真好哇……
姑妈的声音使我觉着她很像是个祈福者。她埋了头,扶了扶她的黑色墨镜,不紧不慢地继续收拾摆放在她两腿间的那些破烂儿。突然间,她的银色头发在阳光下喃喃有声,仿佛在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整座高原肃然起敬,并向我姑妈报以惊异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