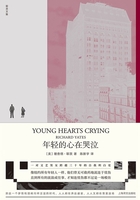既然姑妈喜欢,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把来之前用牛皮信封装好的两千块钱拿出来,要扎西收下。我告诉他,明天我就要回内地了,还不知道这次要去多长时间,我姑妈就拜托给他和达珍了。
扎西不屑地推开我的手,说,你别以为我除了这些破烂就一无所有了。
我刚才努力压下的火又蹿上来了,朝他嚷道,那你应该去办一个捡破烂儿俱乐部,让姑妈和达珍也成为你的会员,说不定我也会加入。我还可以把军区文工团的创作员请来,给你的俱乐部谱首歌,“拉萨城的垃圾明又亮,沿河路的破烂甜如蜜”,这样你扎西就真的是西藏名人了。
那好呀。赶紧去请呀。你以为我怕军区文工团的人?在我扎西的眼里,那些人跟你也差不多,不过是穿着军装的一帮小孩儿,有啥了不起?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想抓住扎西的衣襟,好好教训他一顿,但他的力气太大,猛地挣脱身,夺门而去。
姑妈把我叫住,让我坐到她身边,有些感伤地说,你咋能这么对待扎西,好像他是反革命分子似的。唉,你们过去是那么好的兄弟,我看着你们就跟亲的一样,萨萨就把他当自己的亲哥。怎么,你现在是军官了,就不认他这个兄弟了?再说,他捡破烂儿也没碍着你什么。你要觉得丢脸,那也是丢我的脸,我认这孩子是我的儿子呀。他是我的好儿子……如果没有他……
我解释说,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怕这些破烂儿太脏,容易传染上病。
你说啥?传染上病?
姑妈嘿嘿地挥了几下手。她那并不清脆的笑声却让我体会到了某种东西——跟病恹恹的老年人讲卫生常识是完全白费口舌的。
姑妈一遍遍抚摩小灰,很快从小灰柔软的身上就抚摩出了她那样笑的理由。她说,其实你比扎西捡破烂儿的时间还要早,要早好些年呢。你现在不也是健健康康的,没得啥传染病嘛。你可能早忘了,那一年你好像才念到三四年级,我和你妈去“藏八”看你,是个星期天吧,传达室的吴大爷领着我们到处找你,总算在澡堂后面找到了你,看你正拿着一根木棍跟几个同学在垃圾堆上玩儿,我们上前一瞧,你们在玩儿啥?捡破烂儿嘛。你那双小手脏得,指甲盖都是黑的。唉,那是我觉得你最乖的时候,真的乖,太乖了,乖得不得了,连吴大爷都夸你是乖孩子。
哦,我记起来了。那时候,学校号召我们多做好人好事,每个班教室的墙上都挂着一本“好人好事登记簿”,凡是帮同学辅导作业,帮炊事班洗菜,帮生活老师打扫寝室卫生,捡废品交给学校等等,都是“好人好事登记簿”的登记内容。
一到星期天,广播里便反复播放与军队有关的一些歌曲,比如《长征组歌》《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之类。印象较深的是马玉涛唱的“总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咱们村。每逢我遇见了高兴的事儿,就想起当年的八路军……”因为这歌声一般就是我们集体出动去捡废品的序曲了。废纸、碎玻璃、生了锈的铁钉、牙膏皮,甚至橘子皮(老师说是卖给中药店)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使我们逐渐变成“好人”的珍贵道具。谁捡的最多,谁就最像“好人”。这项活动决不会使我们腻烦,它给所有“藏八”学生带来的欢乐和自豪感当然是扎西无法体会的,其意义远不是我姑妈所说的“乖孩子”那么简单。
辞别了姑妈,我在青年路的路口处看见了扎西。原来他并没有跑远,他想干什么?还想跟我较劲?
我停住脚步,跟他对视。他凝神的眸子里已经没有了儿时的那种清亮,但他却在努力用儿时的那种憨笑来招呼我。
金珠玛米,嘿嘿……
你没事在这儿傻笑什么?
不知道,可能是佛祖让我这么笑的吧。
扯淡。我没心情跟你玩儿什么幽默。你要有话就赶紧说,我可没时间陪你傻笑。你瞧,都有人在看我们了,以为你是精神病呢。
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这没办法,如果佛祖要让我们得精神病,我不得也不行。好了,你不愿意听,我也就不多说了,我只想告诉你,你最好能早点儿回拉萨来。
为啥?
不为啥。因为……我……我会想你的。
想我?
嗯。
通过捡破烂儿的方式来想我?
你……你还想我怎么样?非要我磕头给你赔罪?
磕头?免了吧,我怕你把我的头晃晕。我告诉你,在我没有回来之前,我姑妈哪儿也不能去,等她的眼睛完全好了以后也不能离开拉萨,到时候我会找民政局想办法把你们安排好的,不行的话我还可以去找热地书记帮忙。
你谁也别找。千万别找。不然……不然我可保不住秀秀姑妈又会躲到哪儿去。到时候她要回那曲,那我和达珍也只能听她的。
那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今后别再去沿河路边捡破烂儿了,你没闻到那床破棉絮有多大的味道?那样容易得病,姑妈的身体那么虚弱,还经得起再病一场?
好吧。我听你的,今后不捡破烂儿了。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捡过破烂儿的,姑妈都看见过,但我那并不是真的喜欢破烂儿,而是喜欢做好人好事。
噢,照你这么一说,我捡破烂儿是喜欢做坏人坏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管你是什么意思,反正你也知道了,我本来就是个坏人,不,是个罪人。拿你们这些文人作家的话说,是个掉进罪恶深渊不能自拔的人。不过我想跟你坦白说,我还真的不想拔出来了。罪人就罪人吧。唉,这是命,命中注定……
你别这样好不好?谁也没说你是罪人。就冲你对我姑妈的这种感情,你也是个好人。就算不是大大的好人,起码不是大大的罪人吧?哦,达珍呢?
她活着。活得还可以。
什么话。她在哪儿?
这跟你没关系。你别去打扰她。
你以为我想去打扰她?我是想去谢谢她,就跟她说几句话。我好像还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呢。
她不想跟你说话。照顾你姑妈是她应该做的。你不懂。
扎西边说边一阵风似地跑开了。那阵有弹性的风,在路面上书写了一行表示怨恨的字迹。我认识。因为我始终认为,真正应该有怨恨的是我,而不是扎西。是扎西带走了我的表妹萨萨,是扎西连萨萨被埋葬的具体地点都不肯告诉任何人。
如今,我姑妈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扎西了,就因为这个现实,我从内心想跟扎西重归于好,但这实在难以做到。一想到萨萨,我对扎西的怨恨便会从裂开的胸膛迸出。不过眼下我还得忍一忍。万一有机会让扎西讲真话呢?
是从哪座寺庙里传来的低沉的法号声在提示我——在某个夜莺啼啭的夜晚,扎西可能会“良心发现”地指给我一座褐色的坟穴,里面可能会有一具风干的面具。但是,当我俯下身,看到的却不是我想看到的那双眼睛。我想看到的,是我表妹萨萨的眼睛,或者,是我亲妹妹小萨的眼睛。都不是。那么,是扎西在对我撒谎,对我姑妈撒谎,对我们全家人撒谎。
我越来越坚信我的判断,我的表妹萨萨并没有死,她肯定没有离开西藏。我对我的预感一直都很有信心。
当然,我的亲妹妹小萨是真的死了。比我晚来人世的小萨已经在黄土下面睡了好些年了。
那时候我的父母还在拉萨。是在1961年3月30日这天,我那时任军区保卫部部长的父亲得到一个情报,美军的一架飞机在昌都贡觉地区空降了益西旺加等八名藏籍美军特工,各种枪二十一支,电台两部及其他特工器材一批。该伙特工企图与宁静地区的叛匪首领扎巴喇嘛等人联系,策动指挥新一轮的武装叛乱行动。军区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和搜捕,于5月18日围歼了宁静地区的叛匪首领扎巴喇嘛和麦巴本等,以及他们指挥的武装叛乱分子,并全歼了益西旺加等八名藏籍美军特工(毙七、俘一)。为此,军区召开了庆功会,相当热闹,晚上还举行了小型舞会。
可是,我的父亲老薛一天无话,只推说他要加班,没有陪我母亲去俱乐部跳舞。我母亲很喜欢跳舞,随老薛去北京开会时,还跟陈毅跳过,从那以后她对跳舞更是兴致盎然。当军区举办的舞会散场后,沾一脸喜气的母亲踩着舞步闪进房间,看老薛还呆坐在那儿,紧皱眉头一个劲儿地抽烟。母亲急忙上前,夺下老薛夹在手指头上的烟头,向老薛展示她当天得到的一枚奖章(她临时抽调去负责看管部分叛匪俘虏)。
你抽这么多烟干什么?本来身体就不好,还想把我的身体也搞垮?我母亲说着就把老薛的烟盒和打火机给没收了。
老薛像是什么也没看见,却没头没脑地问,你说说,要是咱们的孩子死了一个咋办?
我母亲的脸色骤变,你尽胡说些什么?不要你抽烟是对你好,还发脾气,往孩子身上扯,什么死了一个两个的。
老薛惨淡一笑,好好,我是胡说,快睡吧。
但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老薛仍然那么问,我母亲就觉得那不像是胡说了。老薛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呢?
老薛问,你把我的烟藏哪儿去了?
我母亲把脖子一扭,说,我倒要看看,你不抽烟还能不能活。哦,对了,我要听听,你不抽烟还会编出啥恶毒的话来。你老实说,咱们的孩子咋回事儿?
我说,你先把烟拿出来好不好?你们山西人咋这么赖?
我们山西人赖?我看你们河南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先说咱孩子的事。不说实话是不是?我这个山西人倒可以跟你说实话,你的那些烟我统统扔到井里去了。我还跟管理科的人打了招呼,以后谁也不许给你供烟。
那我的烟盒和打火机呢?
也扔进井里去了。
什么?
是我用石头砸烂以后才扔的。知道吗,砸烂了,砸得稀巴烂,捡起来也是废铁几块了。
哎呀,你,你这个人呐。那烟盒和打火机都是银质的,是我去印度执行任务时买的纪念品,花了四十多块大洋呢。你这个山西人就不心疼?
不心疼。金子做的我也不心疼。这样,你要说了咱孩子的事,只要说的好,说的是实话,我去八廓街的尼泊尔商店给你买个新的。别说四十块大洋,就是八十块大洋我也给你买。这行了吧?赶紧说吧,咋回事儿?
你在审问俘虏呀?不想跟你说。
老薛头也不回地甩门走了。我母亲没有去追,她知道到了晚饭时间一切都会好的。
咦,这是什么?
写字台上摆着一张照片。我母亲拿起来一看,是女儿小萨出生不久的照片。她端详一阵,嗯,女儿真像一朵好看的花。戴的帽子上有她亲手用毛线织的几朵牡丹花,怪好看。她记起了在军区总医院生女儿的所有细节,这使她很开心。但她的心不知怎么突然悬了起来——这朵花似乎有了凋谢的迹象,要不老薛为啥要背着她看这张照片?她越想越不对劲,急忙跑去找老薛。
找到了。老薛正领着警卫员和保卫部的几个干事在办公楼前栽树。
当着众人的面,我母亲不大好提自己孩子的事,便问,怎么想起来在这儿栽树?
没有人回答,一个个都停了手,站在那儿看着老薛。
老薛走到一边,把手插在衣兜里,好像是想掏烟,却什么也没掏出来。他抬头看了看天,说,咱在这儿栽几棵树,纪念一下咱的女儿小萨。
你说什么?你……
老薛终于从怀里掏出一份揣得发热的电报,我母亲接过来一看,当即晕倒在地,老薛赶紧叫车把她送往军区总医院。
等我母亲苏醒过来后,她哭喊着女儿的名字,差点儿要疯了。对她来说,这时候什么奖章,什么先进,什么舞会,什么丈夫一概不存在了。她背着老薛到军区后勤部搭了辆便车,不顾一切地从川藏公路往成都赶。
那的确是一次令人心碎的旅程,2416公里的路程,我母亲的心里一直托着装满伤心的行囊。她恳求两个驾驶员轮换着开车,昼夜兼程,几天几夜都没有休息。她不能休息,不敢休息。我的那个在拂晓时分生于拉萨,取名叫小萨的妹妹剥夺了她休息的权利。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等我母亲赶到“藏八”,只见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坟包,时至今日一提起,我母亲仍是泪湿满襟。
如果不是见到我母亲如此伤感,我很早就会把埋藏多年的那桩心事讲出来——
一天,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我看见一个小女生,她站在一棵树下,背靠着一片荫凉。我很喜欢她,喜欢她比我还多一个小酒窝的圆脸蛋。当然,我更喜欢她手里的那个大大的黄果果。在我的印象中,我好像从没吃过也从没见过那样大的黄果果。于是向她走过去。
小妹妹,叫什么名字?
小萨。拉萨的萨。
噢,挺好听的名字。刚入学的吧?
嗯。
把你的广柑给哥哥看看,行吗?
我的甜美的童声传到她脸上,她脸上的酒窝立刻变浅了,说,不能给你看。
我说哥哥又不要你的,只是看看。
她把紧握的一只小拳头伸过来,说,可以给你看这个。
我说哥哥不看这个。
她把小拳头亮开,说,这是饿(二)分钱。
我告诉她,捡的钱要交,不然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她犹豫片刻,说,那……交给你吧。
我说要交给老师才对,哥哥只看你的广柑。
她把广柑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跑,跑了几步又站住,看我捡不捡,结果我捡了,她便哭着走开了。
天地良心,我追上去是想把广柑还给她的,不料这一追却把她吓得“哇哇”大哭着跑了,还跌了一跤。一个生活老师正好路过,她大呼小叫地跑过来,对我说,连你自己的亲妹妹都要欺负呀?简直……
我很吃惊,我哪儿来的什么亲妹妹,从来没人跟我讲过呀?
生活老师告诉我,是我母亲托人从拉萨送到学校来的,刚入学才两天。尽管我相信生活老师的话,但我并没有对我妹妹产生什么感情,反而使我决定留下这个大广柑。哥哥吃妹妹的一个广柑应该不算罪恶。
广柑很甜。我知道。但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是个怎样的夜晚。那应该是个哭泣的小萨的夜晚。可能是吧。
几天以后,生活老师来告诉我,我的妹妹小萨因患急性肺炎死在成都军区总医院了。我一听就傻了,一句话也没说,大概脸上也没有悲伤的表情,生活老师后面说的什么话我也没听清。在此之前我只见过一个被车碾死的死人,对死的概念还比较含糊,但我知道小萨也不能回学校来了。我猜想,小萨死的那一刻,医生护士会不会让她抱一个洋娃娃之类的玩具。如果当时我在场就好了,只有我知道小萨想要什么,我会向生活老师要一个大大的黄果果给她。在后来的一个梦里,我看见小萨怀抱黄果果,她笑着,抚摩着,竟把黄果果抚摩成了栩栩如生的洋娃娃。
对于小萨的死,应该说我是有间接责任的。但那时我对此很麻木,直到我母亲领我去给小萨上坟时我也没流一滴泪。
记得上坟的那天细雨蒙蒙,我母亲说她就要回拉萨了,想带我去给小萨上坟。鲍校长一个劲儿地跟我母亲说对不起,守门的吴大爷和几个老师也上前来说对不起,一个个红着眼要跟我们一起去,但都被我母亲给拒绝了。
我和母亲坐着一辆吉普车来到成都北郊的凤凰山。雨水湿透了黄土,天上地上黄成一片。几只乌鸦“啊啊”地叫来阵阵寒气,我不禁有些发抖。母亲把她的军帽扣在我头上,太大,还有股什么难闻的味儿,我不要。母亲又拿出一张大手帕,在四个角上打了结扣在我头上,把我弄得像个小妖怪。
小萨的坟包很小,连块木牌子也没有,将来还会有人认识这座坟吗?
我母亲问驾驶员要了一根手枪通条,我站在一边看她在小萨的坟前一点儿一点儿地挖土……
不是挖,是撬,是掏,是戳,好半天才戳出十几个很小的坑,然后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包水果糖,剥了纸,一个坑里埋一个,还要我跟她学。我不学。剥纸干什么?种在土里弄脏了谁还吃?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