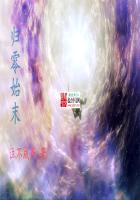我父亲要求我,今后凡是我写的东西,不管是诗还是小说,都要交给他亲自过目之后才能发出去,以免在政治方面出一些不该出的问题。他说,这是对年轻人真正的爱护。现在虽然粉碎了“四人帮”,文学创作的环境比过去宽松了,一批外国文学作品也“解冻”了,但你们太年轻,只顾着乱兴奋。你知道吗,忽略了政治的兴奋所表现出的是什么?是张狂,是忘乎所以的张狂,那是要犯大错误的。既然你跟龚巧明、周力和徐慧他们是好朋友,那你就应该赶紧提醒他们,再这么写下去是很危险的,说不定上面有人会对他们采取措施的。那样的话,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可真是太可惜了。
父亲瞥了我一眼,然后又埋头继续翻看那份大《内参》。我能感觉到,他给我的那一瞥是意味深长的,那是当年“地下工作者”时常使用的一种卓越技巧——不露声色的暗示。
他在暗示什么?
夜色中,我骑上自行车往周力家去。一路上我都在想,天这么晚了,周力睡了没有?也许他正在编辑或是校对下一期《锦江》的稿子,我该怎样以“政治”的道理来劝阻他?还有你,我已经管你叫巧明姐的这个人,你正处于危险境地却可能毫不知情,我有责任保护你,我来啦……我越骑越快,周围的一切都看不清了,终于在一个拐角处被另一骑车人撞翻倒地,我顾不上听他向“解放军叔叔”的道歉,忍了肘部的痛,赶紧跳上自行车飞奔而去。
周力还没有睡,他在这个玫瑰落红的夜晚,静静地读着《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和《红楼梦》被他称作“床头书”(经常要看的书),他说他这辈子至少要有计划地看五遍。
我把《锦江》的“工本费”拿给周力,他不要,说是没有这个必要了,今后也没人再收“工本费”,因为《锦江》已经停刊了。
看来,我父亲的那些话还真有点儿“言之有理”。借着台灯的灯光,我不由吃了一惊——周力的眼眶像是突然间陷了下去,脸上深深刻着情绪失落的痕迹——也许是我自己的情绪失落,因为在此之前,我对《锦江》很快要发表我的“处女作”还满怀信心。《锦江》的停刊,对我的这种信心,或者说是我的虚荣心,简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所谓“文坛新星”的升起之日会遥遥无期。
为什么非要停刊呢?编辑在选编稿的时候,稍微作点儿“政治”的删改不就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吗?
记得几天前周力还兴致勃勃地跟我讲,《锦江》第四期的封面设计如何如何大胆新颖,将会给读者带来如何如何的振奋心情……然而此时此刻,他似乎正以疲倦的神情向我郑重宣称,从此决不再写任何文学作品了。他告诉我,省委宣传部的某位领导找他谈了话,如果《锦江》再不停刊,组织上将考虑他的党籍问题。
这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老革命”的后代,他的骨子里从来都是想为我们党歌功颂德的。再说,他在野战部队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吃了很多苦去“挣”表现才入的党,怎么可以轻易就把党籍给丢了呢?
我想到了龚巧明,她不是党员,但她是不是想争取入党我不清楚,于是问周力,那……龚巧明会不会也跟你一样,从此不再写任何文学作品了?
不会的。巧明是个天使般地精灵,她总会为她的理想找出一万个理由而欣喜若狂,她肯定会在文学道路上一直折腾下去的。
三年后,龚巧明果然还在折腾——去《西藏文学》杂志社当了一名编辑。她是喜好在遍布荆棘的崎岖路上折腾的那种人。拓荒者披荆斩棘般的折腾过程,会使生命的步履愈显活泼而富有激情。
我是怀着敬重之情去跟她见面的。在她那间窄小杂乱的宿舍里,她激动地尖叫,呀——你也来西藏工作啦,早该来啦早该来啦……
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她连连问道,你那篇小说稿带来没有?带来没有?有其他稿子也行……《战友》这个标题太平淡,不过问题不大,平淡就平淡吧,但要平淡得有点儿味道,当然,关键还是故事要生动……
她建议我再好好读一读苏联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好好读一读军旅作家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她认为,《西线轶事》是我国新时期军事文学的里程碑。
由于她太忙,或者说太喜好折腾——要组稿、编辑,还要去偏远农牧区和边防部队体验生活,甚至有谁未婚先孕需要堕胎的这类事情她也要去操心,因此,她没时间跟我细论《战友》的修改意见。
后来,我把这篇小说改为《二十号病房》,她替我转给了《西藏文学》的副主编秦文玉。
我试图通过一个普通病房的窗口来凭吊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并且重新认识和理解他们的价值。不论这篇“处女作”成功与否,我都将它视为我写给战友的一段鲜红的誓言和一副心诵的挽联。
我一直希望读到龚巧明的新作,可是不知为什么,自从她到西藏工作以后,几乎再无作品问世。我很想弄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又怕伤了她的自尊心。一日,我终于忍不住,怯怯地问她,听说你很久不发表作品是因为“才尽”了?
听说?听谁说?
我笑。反正有人这样说。
其实,这话是听跟我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朋友洪历伟说的。洪历伟跟龚巧明很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弟媳徐慧是龚巧明的川大同学,更主要的是龚巧明曾经有一段在洪历伟所在部队体验生活的经历。
那个部队是有着“天下第一团”美称的汽车团。龚巧明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去那里体验生活的女性,来到以各项工作都要力争第一而令人刮目相看的九连。当时的连长刘恒和指导员洪历伟正年轻,朝气蓬勃得犹如站在太阳的边缘,嘴里随时畅诵滚烫的青春语言。他俩的父母都是当年背着背包,靠两条腿步行进藏的“老西藏”。大概就出于这个缘故,他俩有一整套自以为从父辈那里承接下来的带兵方法,手下一百来个大吃“苦头”的兵却很服。
一次,九连在全团内务卫生评比中得了个第二,挂了很久的流动红旗就这么“流”到别的连队去了。九连的兵们便都不敢拿正眼去看一看连长和指导员的脸色。心肠很软的龚巧明当然看不过去,当然要为兵们鸣不平。她以亲近孩子的爱来润泽兵们犯愁的脸,说,不就是一面小小的内务卫生流动红旗吗?有啥了不得,改天我给你们做一面房子那么大的流动红旗,绝对“流”不走。
岂料一个心眼护着连长和指导员的兵们并不买她的账,只狡黠地对她笑笑:你不懂。
对于龚巧明的成名之作《思念你,桦林》《长长国境线》,兵们并不特别欣赏。尽管龚巧明的文笔很漂亮,故事也编得很不错,但那些故事离兵们太远。兵们有自己的故事,有许许多多“高万丈公路”的故事——
那次,全连出车去边防执行运输任务,一个由拉萨来的长途电话通知连里,张老兵的妻子携女儿来队了。连里特批张老兵速返营房与妻子女儿团聚。临行时,张老兵记起妻子来信说过,女儿梦见爸爸给她买了一件红裙子。他就真的去镇上买了件大红色的小裙子。不料在返回途中遇到雪崩,张老兵被连人带车掩埋在雪堆里。人们将雪挖开时,只见他蜷缩着僵硬的身躯,十根手指死死攥住冰冻成壳的红裙子。
红裙子早已被十指洞穿,已经不可能取下来了。如果要取,就只能用火烤了以后再用剪子一刀一刀地剪下来……张老兵女儿的“裙子梦”遗落在“高万丈公路”上,永远寻找不见了……
哇——龚巧明猛地把脸埋在膝盖里:别讲了,你们干吗要这么平静地把这样的故事讲给我听,别讲了……
龚巧明在屋外堆了个雪人,以寄托对“红裙子故事”的哀思。洪历伟一脚把雪人踹了。龚巧明气坏了,说,你这家伙,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洪历伟没生气,说,“天下第一团”的人都不需要眼泪。
似乎就在那一瞬之间,龚巧明说她更理解了兵们,停下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扑在了兵们身上。她办起了文化补习班,有谁出车没上课,她等到深夜也要单独为他补上。她父亲来信提醒她:你的眼睛不好,千万要仔细保护。
可她仍然戴着八百度的近视眼镜给兵们批改作业。谁要是写了一首哪怕很蹩脚的打油诗,她也要一边叫着“惨不忍睹”,一边逐字逐句地帮着修改。连队参加团里的篮球比赛,她自我举贤当了“拉拉队长”,你就看球场上自始至终呈现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九连的兵甭管谁上场,都有股“一拼到底,打死拉倒”的劲头,甚至“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的感人场面也时有出现。一时间九连横扫篮球场,所向无敌。连长和指导员的脸上幸福出龚巧明很喜爱的那种颜色,龚巧明就很高兴地背着手风琴,和兵们一起去参加团里的歌咏比赛。随着一曲雄壮激昂的“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龚巧明和兵们全都融进了“高万丈公路”。全团官兵情不自禁地合着节拍击掌高歌,把一个个讲也讲不完的“高万丈公路”的故事唱成一首首动人心弦的赞美诗。
龚巧明要离开九连了,兵们用包饺子的方式来送她。饺子包好了,煮在高压锅里了,可是没人去揭锅。因为揭了锅,就要吃饺子,吃了饺子,她就要走了。一大锅饺子成了“面片汤”,饺子没吃成,可她还是走了。
兵们列队欢送她,行军礼向她致意。平时口才很好的她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良久,她终于颤抖出一声,“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深深鞠了个躬,蒙住脸转身跑了。她不愿意兵们看见她的泪。然而,不相信眼泪的兵们却流下了泪——男子汉的泪。
1985年9月的一天,龚巧明搭一辆军车去边防采访,从林芝给洪历伟来信说,如果这次不翻进尼洋河,回去我们还包饺子,该死的饺子……
没两天,噩耗传来,她真的翻进了尼洋河,永远属于了尼洋河。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西藏文学》的副主编秦文玉告诉我的,我又转告给洪历伟。我记得那个阴沉的傍晚,秦文玉泪眼汪汪地说,龚巧明刚才回拉萨来了,今后,她哪儿也不用去了,她哪儿也不能去了,就只能活在我们这些朋友的心中了,永远……
秦文玉的眼睛模糊了整座拉萨城,而街头悬挂的五色经幡则在晚风中拼命飘摇,并发出似乎与往日完全不同的阵阵喧响,向我传递着周围大小山岭送来的悲痛悼词。
洪历伟开着车拉上我,疯了似地赶到自治区医院。龚巧明的遗体已经入棺了,洪历伟央求医院的一位老职工打开棺盖让他见一见。直到我抬着棺盖的手臂实在支持不住了,他才站起来。他轻叹一声,巧明的妆是谁给化的,化得还可以。
我俩走出太平间,洪历伟环顾四周,像是自言自语地问,他们单位怎么不派个人来守守灵?巧明生前的那些朋友呢?
我说,也许好多人还不知道,或者那些人心里太难过,不愿看到巧明就这么睡着的样子。
确实难过——第二天,洪历伟和我去了马原的家,马原和他的妻子小冯紧闭家门,难过得躲在屋里哭,谁也不想见。过了好一阵,马原和小冯红肿着眼睛打开门。一见我们,马原刚一张口想说什么,却两手捂住眼睛呜咽起来。
那时候的马原已经在全国的小说界小有名气了,被有的评论家“结论”成“一个玩弄叙述圈套的老手,一个小说中偏执的方法论者”。在我的印象中,这个身材魁梧的东北汉子从来没有难过的表情出现。正如他的代表作《西海的无帆船》里的一句话——“记住,不要向别人诉苦,包括不要向别人展示你腹部的伤疤”。我曾把这句话抄在我的读书卡片上。印象最深的,是在西藏作协经常举办的笔会上,马原每次都会从一个旧军用挎包里掏出他刚写的小说,笑眯眯地重复他过去对别人说过的话,“这篇保证比我以前写的哪篇都好”。
现在,这个因自己“善于玩叙述圈套”而时常兴高采烈的人却埋着头,身体软绵绵地倚在他的家门,不断朝我和洪历伟摇头摆手。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别提啦,别提啦……”
“龚巧明”这三个字悲伤着马原善良的神经——只要一提,他就会拼命……挠他的背部和腰部——后来才知道,马原有皮肤神经过敏症,无论在何时何地,一激动,必会皮肤瘙痒难耐。
那么,不提啦。我和洪历伟转身走了,把一片被泪水灼痛的沉默留在马原的小屋门前。
墓地上空,响起洪历伟悲痛的声音:我们永远感谢那些有理想、有良知、有才华和理解我们的知识分子。
洪历伟朝龚巧明的坟茔抛撒着细土,抛撒着热泪。“天下第一团”三营九连的兵们全都看见了他满脸满脖子的泪。
龚巧明那可爱的小女儿妮子避开人群,蹲在陵园外面的小溪旁采摘野花。兵们说,小妮子是对的。我们今天的努力就是把艰苦的生活留给自己,把美丽的鲜花献给他们。
那夜,洪历伟难过得彻夜不眠,写下了《怀念巧明》的文章,后来发表在《西藏文学》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变成铅字的东西,这是他的第一篇,同时也是最后一篇。再写什么也表达不出他和兵们对龚巧明的怀念之情。
我很理解洪历伟的这种心情,但我不大理解他的一个举动(并且他嘴里往往会冒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语)——将龚巧明过去写给他的几十封信全部炬之火炉。
由于我跟洪历伟本人以及我们父母之间的特殊友情,洪历伟给我看过那些信,每封信都附有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在我的印象中,龚巧明生前几乎从不发表诗,但她其实是一个很能以诗抒发情感的才女。
我为那些被烧成灰的诗大感惋惜。那可以算是龚巧明遗作的重要部分吧,诗行里充满了她内心的欢愉和憧憬,以及焦虑和痛苦——而所有这些,她却只悄悄对一个跟她私人生活毫不相干的人倾诉,这极可能是她想把“孤独”化为“圣乐”的无奈之举。我以为,那些诗大概是她在当时饮润歌喉以竭力释放情感的唯一方式,也是她渴望追求完美的最后绝唱。
在龚巧明的葬礼上,秦文玉代表《西藏文学》编辑部念了一篇悼文,然后将它放在墓前烧掉了。我看见那片片黑色纸灰在墓地上空蜿蜒飞行,然后一缕缕地变形消失——分明一个不肯离去的灵魂在为自己吟唱无声的挽歌,就见碧蓝的天空呈现一派肃然的颂祷景象——从远方迤逦而来的那几只苍鹰,那几只上天派来迎接亡灵的体态矫健的苍鹰,用它们舒展的宽大羽翼细致梳理炫目的阳光,一遍又一遍,梳理着,竟然梳理出声……仍在梳理着,那声音,似乎是亡灵的切切呼叫,将我们的哀痛紧紧揪住。
这个景象会不会也感染了洪历伟,由此促使他烧掉了龚巧明写给他的那几十首诗?
也许,那些燃烧起来的诗的点点热量,可以给龚巧明冰冷的灵魂平添些许温暖。
龚巧明就这么匆匆地走了——听说她在尼洋河里挣扎着想靠岸,并且有个跟她一起掉进河里的记者曾抓住了她的衣服,可惜没能抓住她的身体。其实她平时是个游泳好手,但过于冰冷刺骨的河水还是无情地拽住了她——她来不及收拾她那间杂乱不堪的小小宿舍,她换下来的内衣和袜子之类还没有洗,连被子也没有叠,桌上散放的稿纸和笔记本甚至蒙着灰尘——秦文玉和我坐在那里目睹这一切,是不是需要帮她打扫一下?我有些不解,难道才女们的生活习惯就应当是如此的不整洁?秦文玉解释说,忙,她太忙,其实她是一个很讲究的女人,差不多每次从内地回来都要带几套时髦的服装,很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