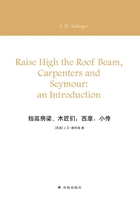我不是找理由,我不必找理由。我饮下色泽阴暗瓶颈曲长的烈酒,吸下了状如珍珠粉的毒,注射灼烧煮沸后的针药,我和每个房间、每层舱内的人没有区别。
在中央厅的舞池里,乐声中扭动的赤裸身体,假若穿上衣服,其实跟过去时代的迪斯科舞厅里看到的男女没太大区别——腿向外分开摆动,臀部与上身往回往前运动,手挥在空中。只是脱去衣服后,原先的象征动作成为功能动作而已。
那个一直坐在外舱灯光下看书、戴眼镜的褐色皮肤南亚女子,这时走到我身边,她取掉了眼镜,随着音乐节奏起舞,一副金坠子的项链垂在乳沟间,很亮,很吸引目光。她在各种肤色的人堆里,动作自然、专横而柔美。由于一丝不挂,更像头雌兽。她从舞台这头舞到舞台那头,又狂舞回来。终于,仰倒在洁白的地毯上,她的仰卧的舞姿显出技艺更加不凡。她的长相平平,但我看不到这一点,因为她动作出众,长相便被掩盖了,只有粉红的乳房和漆黑的阴毛在那儿飞舞。看着她,我的心猛然跳起来。
如果她是花穗子,那又怎么样?我被自己突如其来的这个问题怔住了。我跑到酒柜前,为自己倒了一杯冰水。花穗子一根
一根拨六弦琴,微微低垂的脸,眼睛里一尘不染。那词,我当然还记得,不会忘,就像从那个时代里过来的人都会唱一样: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停留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
“我要开个晚会,请所有认识的人来,包括三亲六戚、朋友仇人一个不少。”她扔下琴说,“我将开的这个晚会,让想象实践,随性情行动。然后在酒和食物里放一种毒药,狂欢而暴死。”肉体交错、尸体遍地的幻景,使她激动不已。是不是她同时展现给我两个极端?一边是纯情,忧郁,但对未来充满梦想;另一边是淫乱,残酷,对未来绝望,只求生命赶快结束。
也许,我是在那一刻才真正被花穗子勾去了魂。我寻遍世界,我也碰不到第二个人会像你。我对她这么说。那天,我们在床上长久跪拜,不向天王老子,不向土地菩萨,也不向上帝,只向我们自己的心,说,我们从此就是姐妹,跟亲生的一样,比亲生的还亲。可是她,现在的布拉格女王,不仅想不起,也根本不会来参加这样的晚会,他们是精神生活高雅的东方贵族。
“下一个!”又跳起舞蹈来的南亚女子叫道。舞者越来越美,场面越来越壮观。在梅毒接近消失,疱疹尚未流行的六十年代;在疱疹接近消失,艾滋病尚未流行的八十年代初;在艾滋病接近消失,爱包拉刚开始在纽约出现尚不为人知的此时,在爱神和病毒互斗的喘息期,幸运的人类总是在幸运地尽情享受。
船头独静,我朝那儿去。风横在皮肤上,雨则斜着。我举起玻璃杯子。灯光在黑暗中描出一个赤裸的女人,熟透的女人快乐的身段。光中雨丝牵在杯里,滴答滴答。我仰起脸,张开嘴唇任雨水飘进。
高举的杯子被一只坚硬的手接了过去,这个男人站在我背后,倾斜杯子朝我身上倒。
我闭上眼睛,带股凉气艳红的酒,仔仔细细往我嘴唇、耳朵、脖颈、乳头、腰、肚脐,一点一点流。那手陌生,但带着火焰,从我头发、后颈、背、臀部、腿,一点点滑落,在一片黑色丛林和深渊区,水和手会合。杯子砰然落在甲板上,随后是我往后仰压倒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