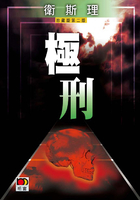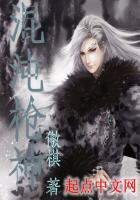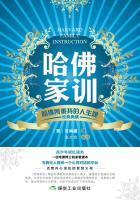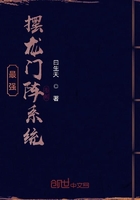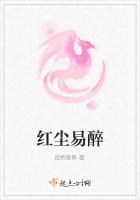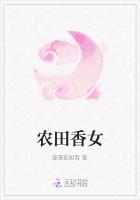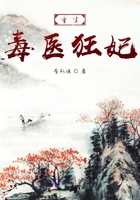位于佩特林山之南的思乡旅馆,叫人想起马思聪的名曲,把那支曲子留在脑子里,故土便挥之不去,种种忘却的记忆也就像霉点一样冒了出来。有广场那么大的草地,七八个英国人穿着白衣裤,悠闲地交谈,不当一回事地挥动板球,视线懒散。枫树、梧桐等大片树林在风中轻唱,远远的城市如一个漫步的诗人,头上戴着好多尖顶的冠冕。
我将垂下的草秆帘子卷起来。我喜欢这旅馆,一是我夜里睡得不错,很久未有这么好的睡眠;二是它的房间不像外表装饰得那么华丽,圆形拱门,宫殿壁画的顶,维纳斯、纳西瑟斯的雕像耸立在喷泉中心,齐整的草坪,郁金香、玫瑰怒放在规矩的方块里,阳光使每一种色彩都夸张十倍地逼现在眼前。
整个房间墙全白,有手工漆的木桌、木床,嵌进墙里的壁橱,有淡淡的新生树叶的嫩绿,或染有几抹最宁静的幽蓝。靠门口,有个穿鞋的木墩,上面深深的鞋印,完全可以肯定是从上世纪遗留下来的。
房间里还立着个大海盗箱,屋梁墙柱是奥地利式,黑木暴露着。床上的全套用品为白底碎紫花,纯棉布,触及皮肤,就像跟一个可心的人缠绕一般。
这个国家最优秀的音乐家斯美塔那在流亡的途中,如果能够或允许返回这儿,哪怕看一眼,最终的结果可能就不是发疯死在精神病医院了。流亡的路漫长,使人心生出这样那样的厚茧,才能忘掉家乡,一个够不着回不了的家乡。虽然在这个时代,家乡不过几个小时的距离,飞越它,就如同飞越整个世纪那么艰难。
这么平静的心情,既不沉浸回忆,又不奢望未来,令我产生出换件惬意的衣服的欲求。我赤脚走在地板上,拿了靛青色齐脚踝长丝裙。不错,镜子衬出一个不年轻的女人,脸仍瘦削,眼睛和头发一样漆黑,未涂口红的嘴唇,唇线自然地弯曲,我在上面点了点儿紫红。镜子里的女人变成我不认识的了,冷漠,冷漠到我的心头紧紧一缩。绸裙前后两道斜纹,像专制的符号,贴着手臂、腿的部分又一丝不露,设计这时装的人向妖魔请教过。
仿佛这番收拾是为了等门铃响。我笑自己,走到门边。
一位高个、栗色头发长及后腰的姑娘,站在直走廊。她不太安静地移动着脚,转身,我没见过这个看来像捷克人的姑娘。我从门孔里观察她约摸一分钟后,打开了门。
姑娘说她叫娜塔丽。她一开口说话,那股挂在脸上的严肃劲儿全消失了。她表情开朗,喜欢笑,额头极高,有点斯拉夫与日耳曼的混血,很吸引人。
我自己坐了下来。她坐定后,用一口地道的BBC英语问我,是否知道阿历克斯的伤势?
我不是未听明白,而是不想回答,所以我支吾两声。
“你那天在贵妃醉餐馆。”她提醒我。
可能是她样子友好,不像警察那么一副挖出你心肝的无情冷酷样,我脑子在一阵夹着烟雾的碎玻璃块里搜索一遍。说如果未记错的话,阿历克斯最多伤了点皮。但他逃不出振荡器的波网。
娜塔丽告辞前,建议我到“真正的布拉格”走走,不必老呆在“殖民者”的圈子里。
她说得有道理,我大胆地问她有无时间,没想到她竟然很高兴做我的向导。
当我们一起上了有轨电车后,娜塔丽已经和我熟如朋友,从内而外透出的自然和放松,让我不能把对异族人的疑心警戒拿来对付她了。电车越走越慢,行人和汽车在轨道上横穿。七十年代醉酒开车,八十年代超速开车,九十年代初发脾气开车,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胡乱开车。喇叭、铃声一路齐奏,让人又想起涣散而无奈的六十年代。
“我们下车,走路也比坐车快。”娜塔丽说。
走在街上,心情宽敞些了。街头立着一个雕塑:翻倒的坦克。一九六八年,有个学生自焚,抗击苏军坦克入侵,压制布拉格之春运动。娜塔丽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我的脸那么痛,仿佛自焚之火还熊熊燃烧,火焰炙烤着我。而坦克被乱涂乱画,根本见不着原先的油漆,炮塔上有条黑字的标语:溜滑板不是罪。我对娜塔丽说:“全世界都一样。”
娜塔丽点点头。
“你瞎点头。”我有点火了,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指的什么。”
“我当然知道。”她重复了一句,“全世界都一样。”
拐入小巷,差不多每个小广场都有两个裸露的天使雕像守着。天使断臂、少翅膀,灰尘、鸟屎披满全身。窗框油漆掉尽,有的锈迹斑斑。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一说话,又进入老题目。我说:“自由决不会有罪。但写这条标语的人忘了,自由总和罪相连,否则就不叫自由。否则这么美丽的一个城市就不会变得这么不伦不类。自由也不会套上电子振荡器。”
“我带你去斯米乔夫地区,或许你会喜欢。”娜塔丽收敛笑容,说,“如果法庭要你作证,你能不能以刚才的观点加以引证来讲话?”
我听得很专心。
“比如,左翼社会党并未枪毙人,但政府将以此定罪,说现场中弹死去的几个人皆为左翼社会党劫持者击毙的。”她看着我,稍停了停,“我们知道你会同情左翼社会党从事的事业,恳望你能合作。”
这才是娜塔丽来找我的真正目的,并非为了了解阿历克斯受伤的情况。阿历克斯的伤势,她当然知道,就像她知道怎么找到我。我不置可否地笑笑。
娜塔丽说:“你总不可能不与正义站在一边吧?”
我说:“我站在我自己的一边。”
争执持续一路。我和娜塔丽越争执就越像一类人,因此气氛并未冷淡下去。而脚下生风似的快,没过多久,已进入斯米乔夫地区。
六十年代盖的俄式住宅区,当时为社会主义的骄傲。房子早已破败,杂草丛生,树叶肥大茂盛。地铁广场正在举行狂欢,戴着假面具的人们载歌载舞。街上游荡的人无拘无束,闲散自在。这不是我已见过的那个漂亮优雅的城市,而是另一个布拉格,这里的天也蓝得特别,那些废弃的建筑、颓塌的道路、油漆剥落的房子好像也是一种有意的陪衬,精心的安排。环绕广场的楼房窗外随风飘扬的挂晒之物,如懒散而满不在乎的旗帜和宣言,来吧,和我们一齐舞蹈!单簧管,还有六孔竖笛回旋在广场四周,像处于幸福之中的祈求:要尽情享受生活!
慢慢地走着,我们过了桥,站到斯洛凡斯岛上,我的眼睛才不由自主地转到周围的风光上。眼前的一幕令我惊讶万分:岛上热闹异常,全是人,从老到幼全都一丝不挂。刚开始长出点点青春毛的男女少年混在一块玩牌,每件器官新鲜得晶莹,阳光沐浴在他们身上,一轮轮闪着纯洁的辉光。欧洲各国人都有,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围坐在桌子四周。浑身都是毛的俄罗斯人,像庞然大物。苗条的法国女人,乳房高耸,屁股如花瓶那么曲线圆润。一群德国老太太皱纹折叠,一伸一缩,韵律十足地在网两边打板球。裁判戴着眼镜,年龄几乎可做我的外婆,光着身子坐在网前高凳上,干瘪的乳房紧贴胸膛,差不多晃不动了,却一样怡然自得,高声地喊着:“二比十五!”
河滩上的吼叫引起我的注意,泥、沙、汗水弄得身体白白黑黑的,除了几件器官,几乎分不清男女,但个个肌肉都发达,像希腊的雕像。悬挂在钢架上的沙袋被击得连钢架都晃动。摔跤的人紧紧抱住,一个肉体缠住另一个,彼此勒得骨骼嘣嘣地响。一个个儿不大的女人用一个漂亮的大背袋动作把男人猛摔倒在沙地上。然后,全身压了上去,手臂和腿狠命钳住男人身体。男人的双腿无奈地踢蹬着。耍弄棍棒的人,头系红带,离沙滩稍远,比起摔跤的人,身体要干净得多,有进有退。击木剑的人,头盔下长发飞舞。
直到娜塔丽拍了我一掌,我才回过神,掉转身去。她已脱掉衣服,身体匀称、结实,乳房不大,却含满了汁液般地鼓胀着。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我想我的脸一定红了。
“叫了你两声也不应。”娜塔丽说,“把衣服脱掉。你已快成注视中心了。”
“注视中心就注视中心。”我仍不动手。
“怎么,不愿或是不敢?”
我摇摇头,虽然自己从未见过这阵势。欧洲的天体营只是听说过,在东方却是不可能的事:“在东方,裸体就是性,性就是房间里的事。因而在这个号称全球文化一体的时代,我这个算得上见多识广的女人还未进过天体营。”我对娜塔丽说,“女人还有个样子。男人却没有一个像男人,怎么都蔫着,赌气似的。”
“哦,不满意?”娜塔丽听我这么说,大笑了起来,“这就是我们每年一次的‘布拉格之夏狂欢节’。”或许我比她想象的东方女人表现得好一些,没惊吓,也没大叫大嚷。“来看男人是要失望的。”她说。
“这儿缺乏一样狂欢必不可少的东西:性。”我失望地撕开拉链,裙子顺着手臂和腿滑落在地,露出未穿内衣裤的身体,好像我早就知道会到这地方来似的。这下轮到我对吃惊的她大笑了。
娜塔丽打量我。我的幸运数字“1”,幸运花朵康乃馨,在我股沟上沿,紧贴着最敏感的部位,色泽比往日更加鲜艳,更加夸张。
娜塔丽上上下下看着我的手臂和屁股上的文身,目光久久地盯在上面,神态由惊奇渐渐转为惊恐,半晌,她问:“这是胎记?”她从数字和花朵的图案上念出声来:“二○一一。”
“不是胎记。”我说,“这是中国刺花高手弘法大师所作。”
她似懂非懂地闭了一下眼睛,脸上泛起大片的红晕,一直延伸到脖子上,朝她赤裸的乳房蔓延开去。她干吗如此紧张?似乎透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