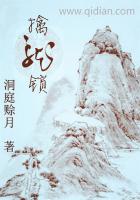一直到母亲再婚,挨打少了,他也从母亲视线里逐渐退了出来。母亲不再关注他,她眼里只有那些同母异父的弟妹。他在母亲的家里像个多余的人。在他十六岁那年,父亲突然记起了他,要求他回老家上学工作,父亲对母亲说,他姓齐,该让他回家。于是四伯从母亲北京的家回到湖南,高中毕业后上了一所职业中专学校,每个月他能从父亲那收到二十元生活费,他不去拿,警卫员也会把钱送到学校。他是没家的孩子。在父亲这边,齐其的奶奶对他很客气,可是他心里没有温暖。他看着齐其的爸爸他的六弟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尽管骂声一片,可是那份关爱在骂声中流淌。那个时候六弟只有十岁,一个人包揽了父母全部的爱。这一切,不是因为他在兄弟中如何聪明如何可爱,而是他生得逢时。在父母年纪稍大了,懂得爱子的时候,在父母由恨而爱的阶段,来到他们中间,自然而然,他们便会爱这个孩子。
四伯像个孤儿,独自一人在外闯荡,在他参加工作后,父亲便中断了那二十元生活费。而他是更少地回家。父亲偶尔会想到他,坐在院子的台阶上,抽着大中华,嘴里骂着,娘希匹,这些儿子都白养了,没一个来看老子,那个老四看我像看仇人样。于是齐其的奶奶便给四伯打电话,说,抽空来看看你父亲。电话那头一般是沉默的。开始四伯也还听话,能在第二天回到家,见到父亲,四伯看不到父亲对儿子的思念,他的神情依然是漠然的。他只是抬起眼睛,懒懒地问,工作怎样?你没在外边说是我的儿子吧?父亲从来都要求儿子们不要打他的牌子。四伯是有些个性的,他说,哪敢呀,我连在个人工作履历表的父亲这一栏上,也没敢把你老人家的名字填上去。爷爷一听,噔地从躺椅上坐起来,虎视眈眈地盯着四伯,接着便骂,你这个狼崽子,那你写了谁的名字,你那个北京的爹?四伯说,我谁都没写,我空着。爷爷气得用拐杖顿着地,说,那你哪来的。四伯理直气壮,说,我跟别人说,我是孤儿,我本来就是孤儿,你们谁真心关心过我?爷爷这辈子都是要别人摸他顺毛的人,四伯的顶撞,让他大怒。他说,你是孤儿,那你滚,我没你这个儿子。四伯抬起脚便走。留下站在那动怒的爷爷,与一屋子不敢出声的人,奶奶、爸爸、警卫员与炊事员。
四伯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在那找了位姑娘结婚,安安静静地过起了小日子。他结婚生子,北京母亲那边他也不报告,父亲这边他更是不提,因为他根本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