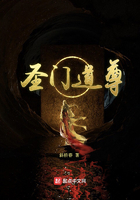最近因为布店的倒闭,我才带着同情的心理走了进去。一进去,像爱丽思掉进了仙人洞里的糖果乡了。满眼是五颜六色的扣子,挂着的,摆着的,还有一个柜子里一只只小抽屉里躺着的,种类是不可思议地繁多。原来像集邮一样,收集扣子如今不但是一种国际性的嗜好,而且也自成一门学问。
小店老板从意大利移民美国,五十年前在纽约给一家犹太人开的扣子厂当推销员,所以家中扣子的样品极多。后来,有一位收集扣子的老太太去世,遗留给他更多的扣子,使他忽然明白:扣子虽小,在爱它的人眼中,何尝不是宝贝?因此,一退休他就开了这家“集扣店”,他说:“以扣会友,乐趣远超过扣子本身的价值呢。”
跟他闲话,真的“胜读十年书”。他的扣子就像他的儿女似的,他可以告诉你哪种扣子是哪一年出品的、哪种是古董、哪种是艺术品……
金扣银扣象牙扣、皮扣包扣化学扣,由史前时代用石头磨成的只做装饰还不会用来扣衣服的小石扣,到十八世纪欧洲巴洛可时代扣子的黄金岁月,扣子的学问可真不小。虽然拉链发明之后,扣子的实用性打了点折扣,可是它的装饰性却提高不少。
想想扣子这小不点儿,可以使一片平面的布变成立体的,使披挂变成穿上,默默走了这么长远的路,好不谦虚可爱。拿破仑的军服上,要是没有那一长排亮晶晶的金扣子,他神气得起来吗?
去年有一种“扣套”非常流行,任何平凡的扣子只要套上各式各样的“扣套”,整件衣服立即改观。我有个朋友还拿它做成耳环胸针,非常别致。
小小的扣子,芝麻似的,但积少成多,像我们的知识。芝麻开门,阿里巴巴的山洞一开,说不定我们会发现他的百宝箱中,原来堆满了扣子。真的,扣子的学问,它带给我的惊讶并不亚于珠宝。
麦田群瓜
美国加州的气候,一年四季分得很不明显,尤其在旧金山,夏天跟冬天的气温好像只在一件毛衣的分别而已。有些喜欢春有春花、冬有冬雪的朋友,就不免要抱怨:好无聊哇!
我却很喜欢这种无聊。因为在无聊中,做出些不无聊的事来,正是考验我们智能的最好方法。譬如,这里的秋天没有什么满山似火的红叶可看,但是到乡下的农场里去,却可以看到满地的南瓜——成熟时,金黄带红,像金子铺的地毯,比起枫树林的美,一点儿也不逊色。
美国人在十月底,有个南瓜节——又叫“万圣节”或“鬼节”,原来是为了驱逐死神的意思。到了这一天,家家点个南瓜灯、吃南瓜饼,小孩子还可以穿奇装异服戴面具,沿门去要糖。各种好玩的比赛也因此纷纷出笼,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全国南瓜比赛——哪个地方的最大?有的真是巨大得像一头象,得奖的农夫,总是会在电视上把脸笑得比南瓜还圆。还有,小学生的画南瓜脸比赛也极有趣。圆脸、瘦脸、笑脸、哭脸、美的、丑的、可怕的……南瓜都一个个变成活过来的人似的。
我喜欢南瓜,喜欢那快乐温暖的颜色。但是,它也使我想到画家梵高。梵高的许多名画,都是以这南瓜色为主调。譬如《向日葵》、《麦田》、《麦田群鸦》……尤其《麦田群鸦》是他自杀前最后的一张画,他画得好不凄惨。一样的田,有人种麦子,有人种南瓜,一样的金黄色,也可以画喜气的南瓜满地的瓜田,也可以画悲伤的秋收后的麦田。我总是想到:要是梵高住在加州,说不定他的疯病都会治好。因为这里的秋天,田地里长满了健康的南瓜。
我敢跟你打赌,世界上再没有比不健康——身体的或心理的——更无聊的事了,天气算什么呢!
钞票上的艺术
在一本讲古往今来钱币演变的书上,读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通货膨胀得不得了,有位伪钞制作者在他印出来的假钞背面居然附加一行小字——我的钱不比你的坏(M y m oney is no w orse than yours)。
实在佩服这位“艺高胆大”的“坏人”。当然了,在俄国他理当被枪毙的,但在钞票史上,他却是绝无仅有的一位“艺术家”。想象他写下这行小注时的得意与愤慨吧——其实他是在抗议沙皇的卢布太不值钱。
美国情报局的墙上,倒是真的收藏了一位画家所画的“艺术”“伪钞”。这位艺术家只想证明,不一定要用多么精细复杂的机器才能印出假钞来,他用普通的水彩、针笔、墨汁这样简单的材料,就绘出了足以乱真的二十元和五十元钞票。
两样假的东西——俄国人想要鱼目混珠,美国人想的只是好玩。一方面明显看出国家穷富对艺术家的影响,一方面我也想到艺术家对钱的态度上明显的差异。
俄国人是拿艺术来为钱服务,他的艺术品结果只值他想要的价值。美国人把钞票当艺术上的道具来使用,结果非但将钞票变成了艺术品,并且使它超过了票面的价值。命运时常跟人开着玩笑,这不过是其中之一。
要测验一个人是否真爱艺术,我想只要问他:
“失火的时候,你先抢救你家的黄金呢还是你墙上的名画?”
一般人很难想到:黄金的价格有一定的标准,艺术品有的却是无价的。正如同拿到一张空头支票,很少有人会觉得它是一张伪钞,然而,据说将来最能防止假钞制作的就是个人支票了。因为它看起来不那么像钱,只是象征。
究竟,钱的价值在哪儿?古代的钱,依所用的金属材料定价值,金比银贵重,银比铜贵重,一眼就能分别。第一个有艺术味的钱“块”,是罗马的青铜块,长方形,有的铜块足有五磅重,铜块上还印了一只牛(当时买卖都是以牛只计算),一磅重的青铜就值一磅重的价格。如今的“铜”钱,用的是合金,金属的价格与钱本身的价值早已不合,金币与掺铜的假金币,有时要专家才分得清。我刚到美国时,时常弄错美国的一角钱和五分钱,因为五分反而比一角(十分)大得多。
中国古钱,有的中空,有人说是“天圆地方”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乱唬老外的——其实是很聪明的发明,一来节省金属材料,二来便于当中穿根绳子好携带。
说实话,钱在手上,来来去去的,有谁真的留心细查过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几回从银行拿到崭新的钞票,我还怕是假的呢。现代电脑技术愈来愈高妙,钞票要防假也愈来愈难,但是,真正的艺术家依然是那种有勇气在假钞上加一行小字的人吧。
数字游戏
数字,看起来不是个有趣的东西,因为它的诞生就是为了实用,不是为了想象或娱乐。但是,等数字发展成“数学”,那学问可就大了,因为数字跟哲学结合,变成了一切科学的源头。
一般人会以为只有文学需要想象力,其实不然,所有重要的科学原理都是先由想象推演出来的。不过,他们不用文字来“说”,而用数字来“说”,像牛顿的地心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鲍兹曼的“紊乱也可以度量”的“乱”说……
现在是个科学时代,数学不好是很吃亏的。其实,如果不是心存偏见的话,数字跟文字其实一样好玩。比如,有个古老的阿拉伯故事说:
一位数学家和朋友在街上看到三个兄弟吵架,问他们为什么吵。大哥说:“父亲留给我们三十五头骆驼,说二分之一是我的,三分之一是老二的,九分之一给老三。我们怎么算都不对,因为三十五的一半是十七多一点点,我要是只拿十七头骆驼就吃亏了,但又没办法把骆驼切开来分,所以才吵起来的。”
数学家说:“不要紧,我朋友的这只骆驼先送给你们,再分就容易了。”他的朋友气得脸色发青,数学家说:“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于是,他牵了朋友的骆驼交给老大,说:“现在有三十六只骆驼了,你再算算看。”
老大说:“三十六的一半是十八,我可以得十八头骆驼。”他欢天喜地牵了十八头骆驼就走了。
老二说:“三十六的三分之一是十二。”于是也好高兴地牵着他应得的骆驼走了。
老三说:“三十六的九分之一是四。”很得意也满意地走了。
你猜怎么样?这聪明的数学家结果不但没有赔掉他朋友的骆驼,反而白赚了一头。
现在,你还怕数学吗?
美国狗
下班时,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正训练着一只黑狗,因为路有点堵塞,车行缓慢,刚好可以看得清楚:那狗真乖,跟着那人,忽走忽坐忽站,都中规中矩、抬头挺胸,显然已颇有教养。
这人在马路边上表演做什么呢?不由得让我好奇起来。仔细一瞧,原来这附近开了一家“宠物店”。
“真聪明!”我心中暗自叹服。现代广告,真是无奇不有:天上,可以有喷气机去写字;还有人写情话或求婚语,昭告世人。地下招牌林立,如果都市是个丛林,我想半数以上的人靠吃广告为生。行走在无数的广告牌下,人们狩猎着新奇的主意,原始人饲养动物为了活命,现代人饲养动物只为了好玩,在活命与娱乐的中间地带,最是生意人的天堂。
这社会怎能不向“经济挂帅”的方向走?当活命已不成问题,“娱乐自己”却不容易学会。生意人,广告经,不纷纷出笼才怪。
美国人爱养小狗小猫,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延伸,其实是为了排闷解除孤寂——这是个人主义的代价。
有位哲学家说:“如何打发休闲时间,是测验智能最好的方法。”人牵着狗走,或是狗牵着人走,变成了智能的考验?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代,知识在前进,智能却在倒退。
在美国,狗好像是小孩子的活玩具、大人们的伴侣、老人的“晚来子”。
狗是个长不大的小孩,不过,小孩子越大越自作主张,狗却越老越乖。所以,养只狗几乎变成美国老人流行的嗜好,见了面谈起狗来,亲热如亲子。
在美国的中国人,渐渐也有了这种算坏不坏、算好不好的“瘾”。养狗是有瘾的,狗命比人命短很多,养过狗的,常常是前狗才死,后狗又来,很少有人为一只狗悼念一辈子的。可是,狗却有“义犬”,忠心耿耿,也难怪会叫人爱。
说到“义犬”,我虽不养狗,倒拥有一只。
我有个好友,养只阿拉斯加那种会拉雪橇的中形狗,取名“钢笔”(美国一个电视卡通影集里的橡皮人之名)。她每次跟我们聊天,三句不离“钢笔”,我们都笑话“钢笔”是她儿子;她也很得意,自称“家有犬子”。这还不打紧,因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结果“钢笔”被七嘴八舌说成了我的“义犬子”——白话一点说,就是干儿子啦!
此“义犬”非彼“义犬”,但在美国,人狗打成一片,可见一斑。
在旧金山渔人码头还看过两只卖艺的狗。两狗正衣冠戴墨镜,天天在街头替主人赚钱,像上班似的,非常有趣。我想,天天都有那么多拿着热狗或香喷喷食物的观光客从它们面前来来去去,它们始终不动心地守住那个装钱的小箱子,算得上是真正的“义犬”了。
裸体画
“裸体画,不过是让男人想起他是个男人。”
约翰·伯格的《看的方法》书中,有这么一句,引起我的深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上,多数的裸体女人,似乎都是情妇的角色,不是画家的情妇,就是出钱请画家的富人的情妇。富人的情妇,通常在画上总是一副很纯洁的样子,完全不具挑逗性。因为富人找画家来画的目的,多半是要向人炫耀的意思——仅止于炫耀而已,并不想引发别人的占有欲。这就是裸体和色情之间的区别。
美感不具占有性,那就是雅的,否则便俗。但是,好的画家,应有移俗化雅的本事,我想画家面对充满诱惑的肉体时,如没有崇高的艺术精神作为后盾的话,也很难不把他的私欲流露到笔下。裸体画的雅与俗,因此有了高下。裸体本身无罪,画的人和看的人,他们本身的艺术精神确是有高下的。
为什么在民间艺术品上,却很少看到裸体画,也没什么雅俗之争呢?色情,在民间也许平凡得跟生活里的任何细节一样,不足为奇?多子多孙,难道不是一种美满的性生活的暗示?要不然,我想到:就是——民间艺术,起源于宗教情怀和梦想,都与信仰有关。圣奥古斯丁说:“我相信,以便了解。”信仰是不需要知识做基础的。如果民间认为艺术只是一种“无名且公有”的东西,那么,不可以公有的东西,怎能拿出来画呢?
人欲是本能,节制是修养,人无论如何知识化,他的义务始终是做人。这就是民间的信仰——一种人性再生为淳朴的奇迹。裸体画,要让人想起他是人——不是男人或女人,才算是艺术吧?需要净化的,是灵魂而不是肉体,在这方面,民间艺术反而教导有方了。
鱼玩具
史学家说,中国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内地无数的小农村,每一个小农村是个打不破、摔不碎的团体。小团体其实是个大部落,改变慢,但认同感极强。似乎不需要把思想整理个次序出来,就有了自己的风格。民间艺术,因此自成某种“模式”——可以作为典范看待。
小时候有一种玩具车,做成鱼的形态。我特别喜欢的不是鱼,是鱼身装上轮子成为玩具的创意。有一种古典的游戏活在里面。因为轮子,鱼变成动态,游回童年以及更为久远的年代。
人跟鱼的“血统关系”开始甚早,鱼纹在半坡、仰韶彩陶上就出现了。科学不能向后看,科学没有越古董越值钱这回事。但是,艺术却不一样。鱼在商代陶盆里定的格,跟鱼在穷乡僻壤的婚宴上用木头刻来作为象征“有余”的情意,或者如鱼做成了带轮子的玩具,可以一脉相承又各自独立变成“原型”——一种考古上使时间静止的精神世界,一种传统的古典的象征。
“上帝不会扣除你生命中钓鱼的日子。”在这个不电动不算玩具的时代,鱼和玩具的脱节,其实也象征着生活与生命的脱节。生活和生命,何为鱼、何为水,就不必太计较了,反正钓鱼的日子扣不扣除,现代人也不在乎。
玩具,据说跟孩子成长时探索与模仿成人世界的生活有关。鱼和钓鱼,被电动玩具的弹珠跟积分取代,正好反映了成人世界物质泛滥与生活俗化的倾向。
鱼玩具,像我们的童年,在时间的轮转中消失了……它还会不会回来呢?
卑化的凤凰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读到:
“云南永宁纳西族,人死火葬后,杀鸡,一面杀,一面诵咒曰:这只鸡是你的伙伴,现在打发给你了。希望你俩一路同行,早去寻找你们的先人,他们在等待着你们。”
我本来对鸡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生肖属鸡,又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只因为看了那本书,书上追溯着那奇怪的云南风俗,我一路追随,发现原来“鸡”是他们的“导魂鸟”——凤凰的卑化就是鸡,他们说。
于是,开始搜集鸡的艺术品:鸡画、鸡瓶、鸡石、鸡盘……每集得一鸡,就想到某一颗灵魂和某种卑微的愿望——期盼升天,等待重生。人与鸡,结伴去寻找灵魂与凤凰。死亡原本是黑色的,现在变得鸡血般红艳……巫师于是对悲伤的群众说:
“让我打发这只卑化的凤凰,给你们带路吧……”
绣鞋
水晶形容《金瓶梅》里的潘金莲:“绣花鞋子泥里踏”,真是再贴切不过。越精美的绣鞋,越让人疼惜;踏在越污浊的泥里,越叫人疼惜。我们的爱及于人呢?及于鞋?还是及于人鞋共毁的悲剧?
旧小说里,三寸金莲时常是肇祸之源,情欲可以从这里开始,也真是压抑得过分。
不过,就是天足,着了绣花鞋子,无论如何是要比穿上皮鞋女气得多。金莲三寸,无比的罪过,是东方之耻。然而,鞋跟垫高三寸的西方人,也不是很文明。如今,女强人虽然绝不会让人联想到绣花鞋,但穿高跟鞋的女强人却依然“正规”。可见“从下往上”挑逗之心还是有的,只是情由欲生还是欲由情生,始终拿不准罢了。
十三的女儿学绣,除绒绣、线绣、金银绣,还有广绣、苏绣、乱针绣。据说从前也有绣花师傅叫绣花状元,是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