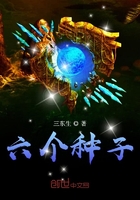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所谓“最高统帅的命令”,以至于后来把他的命令神化到了类似于皇帝的圣旨,部下接到他的手谕竞要象“接旨”一般的虔诚和恭敬。因为保住他和他的集团的命,就意味着要其他军阀的命,完全听“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意味反抗地方军阀的命令。服从命令不是为了别的,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战场上的指挥通畅,而是为了“尊君”。为了方便起见,我还是让蒋介石自己来结束他的命令论吧:“管子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又说:‘明君察于治民之体,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王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这就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命令,我们要奠国家于磐石之安,要服从领袖;但是服从领袖,就是要服从领袖的命令”。
蒋介石的法纪论,即使从外表上看,也不过是封建的纪纲,野蛮的军纪和临时性的命令的混合体,其精神实质则是不要法律和蔑视法律,他所提到的法,仅仅是刑法,是多少代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的治民之法,真正的法律精神,在他的论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赤裸裸皇权意志的外溢——人民基本法律权利的践踏和统治者的随心所欲,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军阀就意味着无法无天,军阀统治就意味着草菅人命,巧取豪夺。
4、自由论
自由是最令蒋介石不舒服的字眼之一。对西于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人权等的口号,蒋介石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全面文化输入为特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恶感,责怪这场运动招来的欧风美雨“毒害”了一般青年,腐蚀了社会风气,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性自由这种东西,它已经使许许多多愚鲁可爱的青年变得不安分起来,在他看来,“青年的个性应当是良知,不能发展其兽性”,因此,“五四运动的目标是完全的失误,它抛弃了中国固有道德,反而引进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然而,蒋介石毕竟顶着三民主义的招牌,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许,而孙中山先生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有目共睹尽人皆知,有关民主、 自由、平等,孙先生诸多论述,言之凿凿,所以蒋介石尽管有一肚皮不愿意,也不好公开骂娘。无奈之际,只好绞尽脑汁在概念上打主意,用看上去好象十分正当的所谓团体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来取代和否认真正的“自由”。
蒋介石认为:“在政治哲学上有‘小我’与‘大我’之称,小我指个人,大我指由数万万或数千万小我合成的国家,而国家又是一切团体的统一的组织。”既然个人是国家的组合分子,“那自然只有国家的自由,而没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国家的生命,而没有个人的生命。”所以“有些人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他们看见了卢梭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张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中国国家还没有自由,还没有平等,所以所有中国人首先要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而国家的自由和平等又全系于国民党,所以归根结蒂要争团体(国民党)的自由。在团体之内,个人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团体,“只有团体的自由,不能再有个人的自由”。
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一个国家对外还没有争得平等自由,它的国民就活该当王朝的奴隶,带着镣铐生活,天经地义衣分五色人分九等,一些人生来当老爷,一些人注定当奴隶,事实上,任何社会群体,小至家庭火到国家,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离开了个体的自由,也就无所谓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相反,什么叫做国家的自由?一个国家,只要还存在着奴役被奴役,束缚被束缚,那么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说是自由的,这个国家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以国家和团体的自由,来取代个人自由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假借群体名义施行个人独裁和暴政的借口。这一点,蒋介石自己的话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作为国家和团体的一员,个人除了服从性之外不应有其他的表现性,“有服从性的人,才能够做真正的党员!不能有这个服从性的人,就是党的败类”。服从谁呢?答案是明确的:“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总百言之,只能有治人者的自由,而没有治于人者的自由,只能有蒋某人的自、由(生杀予夺),而没有其他成员的自由,结果谁的自由也不存在,只有一个专制的“帝王”高高在上。在蒋家天下,不但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国民党党员动辄获罪、毫无人身保障和行动自由,就是其他军阀集团的高级成员也逃不脱被监视的命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民惟需奴性。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同时代的许多传统主义者甚至某些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对西方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解往往走人了同一种东方文化的误区。就拿自由为例,首先,蒋介石对自由作了无政府主义的解释,认为“现在一般人所谓的自由,其意义就是‘随便’,不但言论随便行动‘随便’,生动‘随便’,甚至逾越范围,随便侵犯他人。”其次,他认为自由就是自私自利,发展私欲,发展人的动物性、兽性。其三,他认为自由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以为一旦强调了由自,人们就会无法无天,放纵恣肆,“强凌弱,众暴寡”。
为什么蒋介石以及一代中国人会走入这种荒唐的文化误区?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由于蒋介石独裁统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他有意无意地无视自由的真正含义,随意曲解,属于某种出于情感因素而导致的认知失误。另一种解释可以归之为文化因素。 自由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泊来品,中国人听说自由自严复始,他在翻译《自由论》时,于累累汉字之中竟找不出一个与Liberty相对应的词,几道老先生踌躇再三,只好杜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自繇”应付了事。从严几道到蒋介石,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而文化背景巨大差异所造成的隔膜与陌生感却并不那么容易消除,群性文化积淀所造就的文化定式,使人们容易以东方的观照来审视西方的事物,所以说,对自由的曲解,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复古的传统主义者来说,也是自然的。蒋介石曾非常真诚地说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讨论民主政治最透彻、最精辟的一部书,比卢梭的《民约论》的价值要高得多。而我们知道,如果说《明夷待访录》有些什么“民主”思想的话,那仅仅是些与孟子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民主思想在黄宗羲那里虽说阐发得相当激进,但其精神却是连皇帝(除了朱元璋)也能接受的陈年老酿。
5、领袖论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所有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造就一群循规蹈矩,盲目服从的臣民和一个威灵赫赫耸入云端的领袖。
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帮闲们,为使王权宝座下的垫脚石稳些再稳些,煞费苦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理论,活生生把一个个肉头肉脑的皇帝打扮成了半人半神怪。有的说帝王受命于天,有的说皇帝是真龙天子,到了董仲舒手里,干脆造出一套“天人相通”的鬼话,以人事比附于天,好让老百姓相信,他们生来就活该有个皇帝骑在他们的脖子上。
蒋介石对自己的统帅地位也有类似的说明。首先,在他看来,他的“领袖”地位也是受命于“天”的,不过他的这个天不是指老天爷,因为那样除了穷乡僻壤的愚乡人谁也唬不住。蒋介石借以吓人的“天”是孙中山所倡、在民众中颇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尽管蒋介石早就把三民主义变成了四维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物,然而三民主义的字样却成了他才下口头又上笔端的一缕情思,时时处处不忘以三民主义的大旗包裹自己,刻意突出他所谓“总理忠实信徒”和三民主义传人的身份。他还此地无银似地解释说:“我决不是为我私人,或希望大家来拥护我个人,而是希望大家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共同一致的跟着我统帅,为国家为民族来努力奋斗。’他有意给别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之所以成为领袖,就是因为他是主义的传人和化身的结果,用他心腹大将陈诚的话来说就是:领袖(指蒋介石,笔者注)代表了整个三民主义,文化、思想与信仰,只有领袖才能解释三民主义,“如果反对领袖,无异反对主义,即是革命的罪人”。
其次,他也是“天之骄子”。蒋介石与他的“文胆”及帮闲们特意渲染的中心题目之一,就是把蒋介石说成是孙中山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据说在1928年7月他与冯、阎、李等人同往西山碧云寺谒孙中山灵,老先生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别人似乎觉得他真象个嫡子了才算罢休。对早年随孙中山蒙难永丰舰的一段经历,一有机会,他就会搬出来炫耀一番,以显示他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甚至到了让人感到肉麻的地步:“当时我就是认定,如果总理不幸死了,而没有我蒋介石一个人和他同死,那么我们中华革命党员,革命军人,和整个中华民族,从此以后,便没有人格!”非但如此,他还时常对部下讲孙中山如何看重他,如何培养他,教导他,暗示他早就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当年董仲舒把君君臣臣的关系比附为天象,而蒋介石则把所谓领袖与部下的关系比喻成人的各种器官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各级官长是各该所部的首脑,各个官兵就是所属上官的耳目手足。耳目手足要由首脑来自由指挥。”又说,“总之,上官和统帅就是我们的头,如果不信仰上官,尤其对统帅有一点不信仰,就等于自己砍自己的头!不要自己的头!”自然,人没有头是不行的,而蒋介石就相当于每个人的头,要想保住你的头,就得以“服从领袖为天职”。可惜的是部下们始终不象他那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害得“蒋统帅”总是怨气十足:“现在我们的军队,对于主义和统帅,尤其是对于信仰统帅一点,可以说完全没有注意到,甚至绝对不提起,以致一般官兵的精神没有共同的寄托处所,因此军队就好象是一盘散沙。”
对于王权的内涵,传统理论规定的是“君师合一”,落实到施政方针上就是政教合一,统治与教化并行,对于所谓“领袖”的内涵,蒋介石接过传统理论而又有所添加,即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五尊天地君亲师,他老先生占了三位。作之君即为人主宰,作之师是为予人教诲,建立师生这种半封建的关系(蒋有当军校校长的瘾)。可是凭什么做人家父母呢?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无论父母怎样打骂,却没有子女从父母身边逃跑的,所以为要在集团中培养出家庭气氛和家族情感,就非得设法作之亲不可,君亲师三合一,部下的精神就全都寄托在他——领袖身上了。
蒋介石的领袖论,不过是新时代的君王论。
6、军队论
自人类出现职业军人起,军队就成了专门从事战争这种特殊职业的一种社会群体。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军队自然是政治的工具。在封建时代,军队是封建主私人利益的执行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军队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卫士,而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他们手中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一切,既是财产、资本,也是工具和寄托,甚至等于他们的宗族和所有社会关系。这一点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完全在自己的军队里面,不注意自己的军队,就是不要自己的生命。”即使对蒋介石这样的全国统治者来说,军队也是他集团的主要成份,也是他维系的主要对象,他的所有维系理论,无论是伦理观、社会观还是教育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军队所发,相形之下,他关于军队自身属性的理论,就显得有些干瘪和枯燥。下面,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成军队的性质,功能和目的三大方面来谈。
第一,关于军队的性质,蒋介石从来都堂而皇之地认为军队应该是党(国民党)的军队、主义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因为党、主义甚至国家的化身都是他蒋介石,所以军队就是他私人的军队,而且全国的军队都应该党化、主义化,最终变成他蒋记的私人化。各个地方军阀的军队在“中国国民党及其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出来之后,”就应该乖乖地统一到他的名下,“若想拿个人的势力来做自己不可告人的勾当,那就是完全的梦想。”“现在国家的军队,都是在一个主义下的军队,一个主义下的军队,大家精神应当团结,意志应当统一,国家才有强盛的希望”。说得更露骨一点:“国家的军队,如果有了派别,内部即不统一,无论表面上如何粉饰,终不能做对外的大事”。大道理堂堂皇皇,为主义为国家,但无非是让其他的军阀把军队统统交出来,统一在一个抽象的大帽子之下,实际上都化为蒋某人的囊中物。党化、主义化、国家化,无非是吞并人家的借口,事实上,就是在他下野之际,他的嫡系军队也是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的。抗战胜利后,诸中间党派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费尽了口舌,耗光了心血,始终没得到一个要领。军阀的军队,的的确确是大观园中贾宝玉项下的通灵宝玉。
第二,关于军队的功能,蒋介石直言不讳:“军队就是维持秩序,振作纲纪的最有效的工具。”也就是说,军队的功能就在于镇压人民各种形式的不满和反抗,震慑和平衡各种势力,维持蒋介石个人独裁、专制、军事化的统治秩序,以振作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上下有序的封建纲纪。虽然蒋介石有时也把他的军队萎缩了的对外功能提上几句,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只能化为乌有。事实上,对每个军阀而言,相互间的内战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就是他们军队最实际的功能,以至当这种军队一旦用于抵御外侮时,竟显得那样的虚弱和力不从心。
第三,关于军队的目的。蒋介石认为军队的目的在于“行仁”,在于实现三民主义,“仁”的含义,依蒋氏的说法,即包含“三民主义中心要点”的一种统摄所有的儒家德目的德性。所实现的三民主义,也并非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而是在全国推行蒋记三民主义的信仰。所以在蒋介石的思想里,军队的目的和它的功能紧密相连,后者维持秩序,前者推行教化,两者加起来就巩固了蒋天下。有的时候,蒋介石觉得军队不应该有什么目的可言,只管按着领袖的命令去执行便是,因为“我们有了最高尚、伟大、完善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今后的责任就是照着来实行,用不着再有一点怀疑,再来多研究什么理论!”只管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麻木到了跟手中的枪一般,无知无识无情感意志,领袖指哪打哪,这才是蒋介石理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