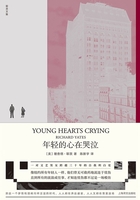张兆坤心中疑惑,不敢张口问娘,只是不住地连连点头。正在这时,有人在外面拍打院门,常氏丢下张兆坤,恋恋不舍地走出屋子。张兆坤等了半晌,不见娘回到屋里来。他跳下破炕,赶到屋外寻找,却被站在屋门前的张长善拉住了。
见张兆坤魂不守舍的样子,张长善手指他的鼻子尖,声色俱厉地嚎叫道:“不许出去找你娘,否则老子打死你!”
张兆坤吓坏了,浑身直打哆嗦,再也不敢挪动脚步。张长善把儿子拉到屋里,随手闩上屋门,怒气冲冲地说:“你个饿死鬼,滚到炕上去,别再惹老子生气。”张长善气呼呼地坐在炕边,嘴里不停地大骂张兆坤。他实在骂累了,倒头便睡。张兆坤乖乖地爬上炕,龟缩在墙角里,“哇哇”大哭不止。他哭了半天,见张长善不答理自己,只好停下来。他悄悄地打开房门,磨磨蹭蹭地出了屋,摄手摄脚地跑到院子里,却发现亲娘踪迹皆无。
常氏离家半个多月后,张兆坤从旁人嘴里得知,爹把娘卖给奉天营口厅(今辽宁营口)来的一个金矿矿主,再也回不来了。张兆坤少了母亲管教,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变得出奇的顽皮,喜欢胡乱打闹,弄得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大鼻涕经常流过嘴角,也不知擦一擦,傻里傻气,活像个傻子。街上的孩子们见状,都管他叫“傻子”,其中程洪兴的孙子程善策叫得最欢。张兆坤也不含糊,当即拳脚相加,孩子们都被他打过,程善策挨的打最多,登门找张长善告状的人,络绎不绝。
这一日,张兆坤端着破碗,提着打狗棍,独自一人沿街乞讨。他转悠一整天,也没有要到一口吃的,掌灯时分,来到“仙人居酒家”门前。他发现陈掌柜身穿石青绸缎大褂,正站在酒家门口招呼客人。
张兆坤灵机一动,伸出一只脏手,拦住陈掌柜,可怜兮兮地说:“老爷,俺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您赏点吃的吧陈掌柜唯恐影响酒家生意,给了张兆坤半张白面大饼,打发他赶快离开。张兆坤肚子早就饿了,接过大饼,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个干干净净。他又跑到路旁水坑边,用手捧起坑水,“咕咚、咕咚”灌进肚里,方才抹抹嘴巴,细细回味大饼滋味。
张兆坤见陈掌柜只顾迎来送往,腰带上系着鼓囊囊的钱袋,在自己眼前晃动。他一时陡起歹意,顾不上再管其他,悄悄凑到陈掌柜身后。他小心翼翼地解下钱袋,揣到破祆襟里。见陈掌柜没有发觉,张兆坤撒开脚丫子,扭头朝家里跑去。
张兆坤回到家里,发现张长善站在面前,不免有些心慌意乱。张长善察觉张兆坤行为有些怪异,少不得厉声质问他。张兆坤挪到张长善面前,把钱袋子放到爹手上,吞吞吐吐地招认了偷窃行为。
张长善越听越气,羞得满脸通红。他未等儿子说完,一把拉过他,抡起巴掌,劈头盖脸地打去,厉声骂道:“奶奶的,让你偷东西,俺砍掉你的爪子。”
张长善说罢,转身去灶台拿菜刀。张兆坤见状,乘机跑出家门,在外面躲藏了六七天。待到张长善消气,张兆坤方才回到家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从此,张兆坤又添上小偷小摸的毛病,越发不可救药,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小无赖。张长善见状,心灰意懒,只好求助神明。他来到城北定海门外东海神庙前,找到算卦先生傅铁嘴,请他给张兆坤相相面,看如何才能让孩子走正道。
傅铁嘴接过张长善递来的卦资,仔细打量张兆坤一番。见他长得傻里傻气,乱蓬蓬小辫拖在脑后,身材长大,长满黑毛。傅铁嘴看罢,便一口咬定说:“这孩子浑身长满黑毛,是男人中的青龙。不长毛的女人是白虎,青龙只有配白虎,事业才能发达。”
傅铁嘴拍拍张兆坤脑袋,神情庄重地问道:“公子,你长大想干啥?”
张兆坤怔住了,张口结舌,过了半晌,方才小声嘀咕道:“奶奶的,他们都叫俺‘大傻’,长大干点儿啥呀……”
傅铁嘴听罢,摇头晃脑,故作神秘地说:“了不得,了不得,公子年少志大,他要做领兵打仗的大帅。”
张长善听傅铁嘴胡诌,似懂非懂,疑疑惑惑地说道:“先生,不对吧,孩子说‘大傻’,怎么是大帅呢?”
傅铁嘴撇着嘴,随口辩白道:“错不了,就是大帅,张大帅。”
张兆坤觉得有趣,心中暗笑,牢牢记下这个话头。他撅着小辫,大声对张长善叫嚷道:“爹,俺就要当大帅,每天都吃白面大饼。”
傅铁嘴又问过张兆坤生辰八字,掐指细算,咋咋呼呼地喊道:“这孩子八字好,主官运亨通,财路兴旺。三十岁后必走宏运,可当大帅,领兵百万,坐镇一方。可惜他杀气太重,五十岁后须急流勇退,否则必有杀身之祸。”
张长善听罢,大喜过望,兴高采烈地说:“借先生吉言,盼着他将来能升官发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张兆坤已经十一岁。正是三九时节,冬夜天气特别阴冷,刺骨寒风横扫莱州府城,漫天大雪从天而降,一阵儿紧似一阵儿,天地间变成冰清玉洁的世界,人们都躲在家里猫冬。张长善围着家中仅有的一条破被,蜷缩在炕上,酣然人梦。
张兆坤衣不蔽体、破烂不堪,冻得瑟瑟发抖。他从炕上爬起来,在屋里又蹦又跳,跺脚取暖。天交三更,张兆坤冻了半夜,饥肠辘辘,实在忍不住了。他拿起仅有的半个窝头,又捡了一条麻绳,悄悄地溜出家门。
张兆坤顶着风雪来到西大街上,左顾右盼,见人迹皆无,便来到路边一堵低矮的院墙下。院墙里有一条狗,听到动静,“汪,汪”狂吠几声。狗主人程洪兴见天寒地冻,懒得从炕上起身,呵斥狗几声,让它别再狂吠。
张兆坤等了半晌,见程洪兴没有动静,不由得心中暗喜,贼胆子大了许多。他把辫子盘在头上,不慌不忙地掏出麻绳,在绳端打了一个活套儿。他隔着低矮的院墙,将绳套儿悄悄抛到院里。紧接着,他又拿出半个窝头,轻轻丢到绳套儿里。
从院子角落里,跑出一条大黑狗,见到雪地上半个窝头,扑上前低头就咬。张兆坤手疾眼快,猛然间拉紧绳套儿,把大黑狗头活活套在绳套儿里。大黑狗再也叫不出声,不一会儿,便张大嘴巴,被活活勒死。张兆坤忍不住暗自窃笑,嘴巴都合不拢,迅速地把大黑狗拖出矮墙。
张兆坤腋下挟着死狗,回到东倒西歪的家,阴冷刺骨的风雪跟着他,席卷进屋里。他把大黑狗抛在地上,用刀扎进狗脖子里,用力向下剖割,一直划到狗肚子上。狗肚子被撕开,鲜血立即喷涌出来,溉了张兆坤一身。张兆坤顾不上狗血,从狗肚子里掏出内脏,扔到一旁。他从狗头开始,慢慢地往下剥狗皮,唯恐将狗皮弄破。直到把整张狗皮剥下,方才松口气。
张长善睡得正香,被张兆坤惊醒,从炕上爬起来。他见到大黑狗,吓了一跳,脱口问道:“奶奶的,你从哪儿弄来一条狗?”
张兆坤一边用水冲洗狗皮,一边回头对张长善说:“甭问啦,从程洪兴家偷的。”
张长善十分气恼,向张兆坤嗔怪道:“不长出息的东西,你咋总偷鸡摸狗。”张兆坤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撇着嘴答道:“瞧你,大惊小怪的,不就是一条狗吗!赶明儿俺当了大帅,赔他一万条狗。”
张长善听罢,张口结舌,把后半句话咽到肚子里。
张兆坤把狗身放进破锅里,又倒进半锅水,最后点燃灶火。他用筷子不断地在锅里搅拌着,待到狗肉煮熟,他从锅里捞出来,用鼻子嗔嗅香气,甩开腮帮子,大吃大嚼一番。
张长善见状,忍不住吧嗒着嘴,往下咽唾沫。他从炕上跳下来,扑到破锅前,也学着儿子狼吞虎咽。待到填饱肚子,他止不住直打饱嗝,倒在炕上又酣然人睡。
过了几天,风停雪住,张长善来到海边盐碱地里,扫了一大堆碱面,用破褂子兜回家。他将碱面倒在破锅里,又倒进半锅水,点火烧开。碱面在热水中溶化,随着水慢慢熬干,锅底析出白花花的芒硝。
张兆坤将黑狗皮绷在墙上,从锅里抓起一把芒硝,用尽吃奶的力气,往狗皮上揉搓。他把黑狗皮揉搓了一遍,芒硝刺鼻的酸味,呛得他不停地咳嗽,眼泪、鼻涕止不住地往外流。
张兆坤屏住呼吸,气恼地摘下黑狗皮,随手扔进水缸里。黑狗皮被浸泡一整天,芒硝溶在缸水里,像尿碱一样骚气。张兆坤捞出黑狗皮,小心翼翼地挂在院墙上。待到黑狗皮晾干,再也没有芒硝骚味。张兆坤忙将黑狗皮披在身上,借以抵挡寒冷。在黑狗皮包裹中,他的身子渐渐暖和起来,感到温暖如春。他不由得大喜过望,得意扬扬。
张长善见儿子整日偷鸡摸狗,胡作非为,无法管束。他只好领着张兆坤,找到在“戏凤鸡舍”斗鸡的陈掌柜。他厚着脸皮,求陈掌柜收留张兆坤,在“仙人居酒家”当跑堂。陈掌柜见张兆坤年纪虽小,傻里傻气,个头儿却挺高,口齿还算伶俐,便收留了他。张长善见状,跪倒叩头,千恩万谢。
张兆坤在酒家当跑堂,晚上住在灶间草垛上。他每天都要早早起来,烧好洗脸水,端到内宅上房和姨太太房里。他放下洗脸水,就拿走床头脚踏板上的便壶倒掉。等陈掌柜大老婆和姨太太洗罢脸,他再将洗脸水倒掉。
张兆坤忙完内宅的事情,要赶到前面店堂去,帮师兄们卸掉门板,迎接客人。他整天手脚不闲,楼上、灶间乱窜,伺候着喝酒的大爷。每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客人们大都酩酊大醉,醉眼蒙昽中,看见张兆坤在眼前晃荡,少不得要拿他开几句玩笑,有的酒鬼甚至要揍他几下。张兆坤受着窝囊气,反要赔着笑脸,不时地插科打诨,逗客人们开心。到了晚上结算时,如果酒家生意红火,陈掌柜还给张兆坤一个好脸。假如没有赚到钱,陈掌柜就拿他当出气筒,怨他整日胡侃,把客人气跑了。
张兆坤累了一天,尽管精疲力竭,还要烧好洗脚水,端到内宅上房和姨太太房里。紧接着,他要拿来便壶,放到大老婆和姨太太的床头脚踏板上。每天深更半夜,他才能回到灶间草垛上躺倒。
陈掌柜年过半百,仍是春心未老,结发大老婆与他年龄相当,又是良家妇女,床笫间自然拘谨,讨不到陈掌柜欢心。陈掌柜寂寞难耐,便娶了一房姨太太。姨太太郑氏年仅二八,窑姐儿出身,生性放浪淫荡,床上功夫非同一般,最得陈掌柜宠爱。姨太太郑氏往东走,陈掌柜不敢往西去;姨太太郑氏要星星,陈掌柜不敢摘月亮。姨太太郑氏本来瞧不上陈掌柜,嫌他是个棺材瓤子,只因她独守空房,见不到其他男人,只好应付陈掌柜,权且拿他顶缸。
张兆坤知道姨太太郑氏的分量,不时用甜言蜜语哄她开心,拼命讨好。姨太太郑氏喜欢张兆坤“傻”实在,没少在陈掌柜面前夸他。
一天晚上,张兆坤按照老规矩,端着洗脚水,来到姨太太郑氏屋门外。听得屋里陈掌柜和姨太太郑氏正在窃窃私语,他没敢造次,轻轻放下洗脚水,蹑手摄脚地来到窗户下,用舌头舔破窗纸,眯缝起眼向里偷窥。他不看则已,看罢登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一幅西洋景展现在眼前。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