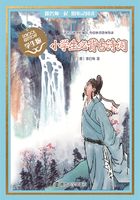弗兰克做了些记录。那颗失踪的子弹可能是另一种口径或型号,这或许可以说明至少有两名袭击者。弗兰克的想象力再强,也无法想象一个人两手各持一把枪向那个女人开火的情形。因此,现在可能有两个嫌疑犯。这个结论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不同的入口和出口,以及脑内伤的不同类型。那颗翻飞着射入的达姆弹的入口要比另一颗子弹的入口大些,所以第二颗子弹不可能是颗空心弹或柔头弹。这颗子弹击穿了她的头颅,留下了半个小手指宽的弹道痕迹。射弹的缺陷虽然可能是最小的,但他找不到那颗该死的子弹,所以这还是毫无意义。
他看了一遍自己的原始现场记录。他正处于收集资料的阶段,但愿自己不会永远被困在这里。至少他还不必担心这个案子的有效时限法令会过期。他又看了一遍验尸报告,不禁又皱起了眉头。他拿起电话拨打。十分钟后,他和验尸官面对面坐在验尸官的办公室里。
那个大个子正在用一把旧的解剖刀刮着手指上的老茧皮。终于,他抬头看了一眼弗兰克。
"勒死的痕迹,或者至少是企图勒死的痕迹。明白吗?尽管软组织有些肿胀和出血现象,但气管没被压碎,而且我还发现舌骨有轻微的骨折痕迹。眼睑的结膜内也有淤斑的痕迹。不是绳子勒的,验尸报告上都写了。"弗兰克把那些话思量了一遍。结膜或黏膜内的淤斑或轻微出血现象都可能是勒杀和大脑内部压力增加的结果。
弗兰克在椅子上倾过身子,看着墙上那一排学位证书。这些东西证明,他对面这个人是个长期献身于法医病理学的好学生。
"是男的还是女的干的?"
验尸官耸了耸肩。
"很难说。人类的肌肤不像星球的表面那样容易留下印迹,这你是知道的。事实上,除了几个不相关联的地方之外,几乎不可能留下什么痕迹,即便有些什么,大约半天以后也不存在了。一个女人试图徒手勒死另一个女人,这虽然很难想象,但确实发生过。压碎人的气管并不需要太大的压力,但徒手勒死人通常是男人的做法。在一百桩勒死人的案例中,我还从未见到过有一桩是女人干的。这也是从前面的案例得出的结论。"他又补充说,"如果是肉搏,你得他妈的对自己的力量优势颇有信心才行。如果根据我所受的教育来猜测,是个男的,如果说猜测有时也有用的话。""验尸报告上还写着,她下巴左边有挫伤和青肿,牙齿松动,嘴里面也有伤口。""像是有人猛揍了她一顿。有颗臼齿差点刺穿面颊。"弗兰克瞥了一眼自己的卷宗。"那第二颗子弹呢?""第二颗子弹造成的损伤使我相信,它也是颗大口径子弹,和第一颗一样。"
"你对第一颗子弹怎么看?"
"都在这里了,可能是0.357口径或0.41口径,也可能是9毫米的。上帝呀,你看到那颗子弹了。那该死的玩意儿平得像块薄煎饼,有一半穿透了她的大脑组织和脑液。没有着陆点、弹道痕和变化曲线。即使你找到一种可能的枪,你也无法得到吻合的结果。""如果我们能找到另一颗子弹,可能就有事儿干了。""或许不能。无论是谁把它从那面墙上挖出来的,都可能把那些痕迹搞乱了。弹道学家不会开心的。""是啊,可弹头上或许沾有死者的一些头发、血液和皮肤。我倒是乐意去研究一下那些线索。"验尸官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那倒是,但你得先找到它才行。""可能我们找不到了。"弗兰克笑笑。
"天晓得。"
两人彼此对看了一下,都很清楚无论如何是没法找到另一颗子弹了。即使能找到,他们也无法把它与谋杀现场联系起来,除非那颗子弹上面有死者的痕迹证据,或者他们能找到那支发射这颗子弹的枪,并把它与谋杀现场联系起来。这两种可能都不太现实。
"找到空弹壳没有?"弗兰克摇摇头。
"那你也没找到任何针孔啊,塞思。"验尸官是指枪的撞针在弹壳上留下的那种特殊痕迹。
"我从未说过事情会顺利。顺便问句,在这桩案子上,州里那帮人没有把你逼得太紧吧?"验尸官笑了。"相当沉默。如果遭重创的是沃尔特·沙利文,谁知道会怎样呢?说不定我的报告已经交到里奇蒙(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译者注)了。"然后,弗兰克提出了他来这里真正想问的问题。"为什么会开两枪?"验尸官不再刮老茧皮了。他放下手中的解剖刀,看着弗兰克。"为什么不呢?"他眯起眼睛。在这个平静的小县里,他处于一个不被人嫉妒的位置上,而且完全有能力抓住那些送上门的机遇。作为弗吉尼亚州大约五百名副验尸官之一,他进行过广泛的刑侦实习,但他个人对刑事调查和法医病理学都很着迷。在搬到弗吉尼亚州来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之前,他曾在洛杉矶县当了大约二十年的副验尸官。如果说到杀人案,那里的情况比洛杉矶市好不了多少。但这桩案子他得费些心思。
弗兰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说道:"显然,这两枪中的任何一枪都会致命,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为什么还要开第二枪呢?有很多原因让你不去那样做。首先是会有枪声。第二呢,如果你想他妈的尽快离开那里,你干吗还要浪费时间去补她一枪呢?最关键的是,为什么要留下另一颗将来或许会暴露你身份的子弹呢?难道是沙利文惊扰了他们?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子弹是从门口射向屋内的,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射击线是下行的?她是跪着的吗?很可能,要不然就是那个枪手超乎寻常地高大。如果她是双膝跪地,为什么?想学执行枪决的样子?但又没有近距离开枪的痕迹。还有,你也看到她脖子上的那些勒痕了。为什么先想勒死她,然后又停下来,拿起枪,把她的脑袋打开花呢?而且接着又开一枪,还拿走了一颗子弹。为什么?有第二支枪?干吗要把它藏起来?那有什么意义吗?"弗兰克站起来,两手深深插在裤子口袋里,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这是他专心思考问题时的一种习惯。"而且犯罪现场是他妈的那么干净,我真不敢相信。什么也没留下。我是说任何痕迹都没有。我都奇怪他们为什么没给她动手术,把那颗子弹也取出来。
"得啦,我的意思是,这家伙是个盗窃犯,或者是他想让我们这么认为。可密室的确被洗劫一空,大约有价值四百五十万美元的东西被盗。那会儿沙利文夫人在干什么?她本该在加勒比海边享受日光浴的。她认识那家伙吗?难道她在背着丈夫与别人胡搞?如果是的话,那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你为什么会先大模大样地走进大门,然后弄坏保安系统,最后却用根绳子从窗口爬出去?每次我自问一个问题,就会有另一个问题冒出来。"弗兰克又坐了下来,看上去对自己的一连串疑问有些困惑。
验尸官往后仰靠在椅子上,把那份卷宗拿过去,翻阅了一会儿。然后,他摘下眼镜,在袖子上擦擦,用拇指和食指牵拉着嘴角。
弗兰克看着验尸官,他的鼻翼扇动着。"什么?""你说犯罪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你说得对,现场太干净了。"验尸官慢悠悠地点起一支珀尔摩尔烟。弗兰克注意到,是那种不带过滤嘴的烟。他共过事的所有病理学家都抽烟。验尸官向上吐着烟圈儿,显然是陷入了沉思。
"她的指甲也太干净了。"弗兰克一脸的困惑。
验尸官继续说,"我是说,没有一点尘土,没有一点指甲油---虽然她是涂指甲油的,就是那种鲜红的东西---没有一点你期待的能找到的任何普通残留物。什么都没有。现场像是被全面清理过,你懂我意思吗?"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我还发现了一种药水极微小的痕迹。"他又停了一下,"像是一种清洁液。""那天早晨她曾去过一家高级美容院,修理了指甲,还有其他全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