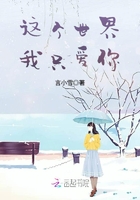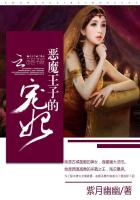张小别坐在教室里的靠近窗户的座位上,教室的讲台上老师用力地在黑板上划出各种曲线,但张小别的眼睛却盯着窗户上明亮的玻璃发呆。整扇窗户有两块玻璃组成,每一块都被擦拭得一尘不染,明净得倒影出他的清晰的脸孔,也倒影出他的困惑:到底是怎样一双芊芊细手才能把这两面玻璃擦拭得如此清透,竟不会留下一隙灰尘,哪怕飘落一丝蛛网在它的表面,也会毕露无遗。他转过头环视四周,努力在整个班级中寻找那一双芊芊细手。他知道,擦拭这扇窗的那双手,一定就坐在在这件教室的某一个角落。
但最终证明这样的寻找徒劳无功,没有人会在擦拭完玻璃后,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游离之中,他下意识地把目光定格在前桌女生的身上,她的手指白嫩纤细,宛如这面玻璃一样晶莹剔透。
一定只有这样洁白的双手,才能擦拭出如此洁净的玻璃,张小别想。
虽然开学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透过窗户,外面的校园甬路上依然有新生拉着行李箱来报道的身影。这是一所让人趋之若鹜的高中,是只有有才或是有财的同学方能进入的“大学摇篮”。这样讲它,大抵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不爱才的学校,也没有不爱财的校长。
张小别本不该进入这所高中学习,在连玩带耍了整个初中时代之后,他本应进入他家那边的一所重点高中就读。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张牧之坚持要把自己送到一百公里以外的这所学校上学,毕竟在这个时代里,考大学如同古代进京赶考一样,考上了就好,没人在乎你是坐着轿子去,走路去,还是骑着驴去,分数说明一切就是中国教育的“唯结果论”的最好证明。
同他一起转入市一中的,还有邻居兼死党巫桂理和李三宝,他们因为入学分数不足而额外缴纳了一笔不菲的择校费。
开学那天的早晨天色阴霾,三个母亲喋喋不休地争吵着要送儿子们入学,张牧之一声令下替三个家庭做了主:“从读高中开始,他们就是成年人了,家长们谁都不许送。”
三个母亲叽叽喳喳地说:“高中生就是成年人?”
“才不吃奶几年?”
“他们还小呢。”
张牧之义正言辞地说:“早该是成年人了,他们的父亲的爷爷有哪个不是十四五岁结婚的?要是不结婚,哪来的他们的父亲的父亲,到最后哪来的他们?”张牧之表象气势汹汹,实则理亏,因为直接跳过了他自己那一代人。
三位母亲继续叽叽喳喳地商讨一番,却最终没有违抗张牧之的决定,早点让他们学会独立也好。最后只是卑微地恳求,用宝马车送他们去学校,讨一个“一马当先”的彩头。
张牧之欣然应允,派了自己的司机把三人打包好的行李装车,无奈宝马车太小,装了行李就装不下人,最后只好全部卸掉,改用破旧却宽敞的货车送行,惹得几位母亲抱怨连连。
这辆载着三位学子的货车缓缓地停在这座高中的门口—某某市第一中学,当三个人费力地从车里搬下各自的行李箱以及各自的身体之后,立即被它的雄伟壮丽的校门震撼得激动不已。
校门口两侧是正四方形的大理石结构,仿照烽火台的构造耸立云间,连接两侧的横梁上,用烫金的隶书体写着市一中的全名。横梁下面是乌黑的铁板门,关起门来,校内校外是两个毫不相连的世界。每座“烽火台”的顶端能站立四五人,倘若每一个人搭弓射箭的话,绝无人能从这座大门活生生地逃脱。
此刻,忙于入学的高一新生们,正络绎不绝地从“烽火台”之间川流走动。
拉着行李,跨过市一中的大门,巫桂理发出感慨:“穿过这道门,我们就失去自由了。”
平时素爱建筑书籍的李三宝说:“你有所不知,校门建成看守所大门的样子是现代高中校园的潮流,如同中世纪时期欧洲的教堂流行哥特式建筑一样,所有的建筑风格总是同来同走。”
张小别摇摇头,说:“高中哪里比得过看守所,监狱里的犯人以出去为荣,高中生以出去为耻。如果监狱长告诉一个犯人,你回家吧,犯人高兴得很。如果校长告诉你,你回家吧,多半是被开除了。”
跨过校门的里面是横七竖八的被人高高举起的白色指示牌,用醒目的红色字体写着:高一·一班,高一·二班,高一·三班…。三人各自掏出录取通知书,分散去找寻自己的班级。
张小别的通知书里写着高一·六班,于是他努力在人群中四处寻找写着“高一·六班”的牌子。但是,推搡着在人群里走了一圈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到“高一·十班”的地盘,却依旧没有找到六班的影子。
继续找了很久之后,他终于在人群的最偏僻的角落找到了正被斜挂到树枝上的“高一·六班”的牌子。那指示牌原本洁白无瑕,大概举牌的人嫌它太重,索性将它放到地上,被先前来报到的同学踢得一条条的脚印。后来某位高个子的人担心新人找不到地方,索性高高地挂到树上,恰好被返回的张小别发现。
张小别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扫刚才的倦容,激发出新生报到时应有的激动,在攀谈正酣的人群中挤出一条缝隙,高喊:“请让一让,我是高一6的,前来报到!”
一个穿着绿色连衣裙,身体瘦小,乌黑齐耳短发的女生坐在里面,侧着脸示意他靠到她的附近,“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小别。”他镇定下来,逐渐平息了口鼻里的喘息,同时也开始注意这位未来的同班同学。
这位女生皮肤白皙,牙齿洁白而整齐,一双眸子不算很大却算是异常精致。从年龄上判断,她应该不是老师,同自己一样,是六班的新生。既然是同学,又是异性,说不定两人以后会培养出浪漫的爱情,因此,第一印象更加不能毛躁。张小别深呼吸几口气,把刚才激发出的激动暗暗地压了回去。
“噢,报到单上写上你得名字,然后跟着他们几个人去班里报道。”那位女生微笑着,转过身帮张小别指引其他几个人的前行方向。
张小别本想问她的芳名,要一下联系方式,方便以后联络,又觉得太过唐突,毕竟以后都是同班同学,不急于一时。
市一中的校园很大,是这座城市里占地面积最大的高中。走出新生接待处,是一条笔直宽敞的马路,两边种着两排茂密的垂柳和梧桐树。再往左边是一片广场,隔着广场是两栋整齐的教学楼;马路的右边隔着粗壮的梧桐,是一排二层的校办公室,这里是市一中最老旧的建筑,低矮的砖混结构透露出这座校园悠久的历史,校长室、主任室、教导处、教务处、后勤处这些校务部门都设在此处。
张小别沿着马路继续往里走,马路的尽头是操场。高三的学长们早已经开学了,此时有两个高三的班级在上体育课。远远望去,只有十几个男生在操场里踢球,和几个女生在场外加油鼓劲,另外的几十个人躲僻静清凉的角落里看书。
笔直的马路到操场后戛然而止,往左转是一条甬路。走过一段距离后,甬路的一旁是塑胶篮球场,另一旁是教学一楼——也是高一新生的教学楼。
张小别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注意到篮球场的后面,有一片面积很大的花园。在花园里有几栏开满鲜花的苗圃,苗圃边上有很多长椅,遮盖在茂盛的垂柳树中。
“真是个夜间约会的好地方。”他默默地说。
就在张小别想象着约会的美好场景之时,走在他身旁的胖子提醒该上楼了。小别“噢”了一声,跟随他们上楼。
这座教学楼总共四层,六班的教室在三楼边上,最靠近篮球场的位置。走进教室后门,班里早已站满了人,其中好多人都拿着行李箱,他们与张小别一样,是以后要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学生。教室里还没有摆放课桌,同学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相互自我介绍。
张小别将行李箱放在教室后面的靠窗的空地,纵身一跃,坐到窗户的窗台上,脚蹬着行李箱的侧边,斜着身子看窗外的高年级男生打篮球。
旁边的有几个男生开始对他指指点点,其中一个男生说:“那个一身白色运动服、带着白色帽子的那个男生,我看到他从‘宝马牌货车’车里走出来。啧啧,‘宝马牌货车’,你们肯定都没见过,老得要报废的那种!”
众人跟着起哄道:“啧啧,长见识了。现在的人真是看不懂,没钱就不要装大款。”
小别听到他们的议论是在说自己,没有过于在意,甚至没有扭过头去看他们。他和巫桂理、李三宝来的时候,乘坐的是最普通的拉货的汽车,巫桂理他妈迷信,不知从哪里捡来一个宝马车的车标,临时插到那辆车的车头上,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笑料。张小别此刻深受其苦。
议论过后,那几个人笑嘻嘻地走了过来,为首的那个人冲着张小别喊:“嗨,乘坐‘宝马牌货车’的哥们,我们认识一下,我叫王龙飞,别人都叫我王秃子,你怎么称呼?”
张小别转过头来,打量了他一番,眼睛细长,脸短而胖,皮肤黝黑,带一副粗边黑框眼镜,口鼻之间留有一撮浓密的苏联红军式的胡子,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天生稀疏的发型,头顶和前额处的头发早已干枯,只有四周勉强长出些杂乱的头发。这个发型相对于十六七岁的年龄而言,的确显得有些着急了,不愧于“秃子”的称号。
小别认真地伸出手,客气地打招呼说:“你好,我叫张小别,以后请多多关照!”
王秃子率众来的目的是他,见他答话,便嘲笑道:“你们家的座驾真的是高,我们几个人都大开眼界。”说罢,其他几人跟着大笑起来。
小别伸出一根手指在嘴边,说:“嘘,不要声张。那是家父在中东富豪手中买回来的古董,世界上都难得一见那种。”
王秃子不信。
小别掏出电话,在手机的图片册里找出几幅张牧之与身着阿拉伯长袍的中东人的握手合影,展示给他们看。
王秃子看了几眼,对着旁边的几个人说:“看来是真的,我们几个人的确开了眼界。”其余几人不再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