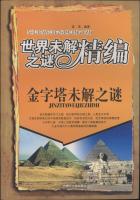罗森早晨八点钟离家的时候有三个地方可去,这也是一天里他要做的事情:再到孚白广场去询问证人,去拜访白冰太太,区警察分局已经把这件事通知她了;最后就是再和宇文娜谈谈。
他起床的时候就跟局里打了电话,要他们准备那幢大房子里房客的名单,还有和这场悲剧多少有点儿关系的人也要列在上面;因此,当他来到办公室时,有关的详细资料也许已经在等着他了。
玄武门大街上行人很多。天气很冷,探长翻起他大衣的天鹅绒领子。孚白广场离得不远,不过得步行着去。
这时候,有一辆驶向朝日广场的有轨电车经过,这就使罗森打定了主意,他先去看宇文娜。
不言而喻,她还没有起身。在旅馆的接待室里,有人认出了他,感到有些担心。
“她不会被牵连到什么麻烦事吧?这个姑娘平时够安静的。”
“来看她的人多吗?”
“只有她一个朋友。”
“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
“她只有一个朋友。既不年老也不年轻……”
旅馆设备很好,有电梯,房间里都有电话。罗森乘到四楼,敲了敲27号房间的门,听到有人在床上翻身,随后有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说:“什么事?”
“请开门,尼娜!”
大概有一只手伸出了被子,碰到了门闩。罗森走进一个昏暗和潮乎乎的房间,看到那个少妇的睡眼惺松的脸;他走过去把窗帘拉开。
“几点了?”
“还不到九点……您别起来……”
由于光线太强,她半睁着眼睛。她看上去并不漂亮,她更象一个农村姑娘,而不象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有两三次她摸了摸自己的脸,后来把枕头做了一个靠背,坐在床上,然后拿起电话。
“请把早餐拿来!”随后对罗森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您不怪我昨天晚上向您借钱吧?……唉……我一定得去把我的首饰卖掉……”
“您首饰多吗?”
她指了指梳妆台,台上有一只廉价烟灰缸,里面放有几只戒指,一只手镯,一只手表,总共约值五千人民币。
有人在敲隔壁房间的门,宇文娜侧耳细听,听到又一次固执的敲门声时脸上漾出了微笑。
“是谁?”罗森伺道。
“我的邻居吗?我不知道,可是谁能在现在这个时候叫醒他们呢……”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即使他们起床,也从来不会在下午四点以前。”
“他们吸毒吗?”
她的眉毛一拧,表示肯定,可是她连忙又加了一句:“您总不会利用我刚才讲的话吧,是吗?”
隔壁的房门终于开了,宇文娜的房门也开了,一个侍女拿来了放在盘里的牛奶咖啡和羊角面包。
“对不起,我吃早饭了。”
她的眼睛上有黑圈,从她睡衣的隙缝可以看到她瘦削的肩膀和发育不良的乳房。她把羊角面包一块块掰下浸在牛奶咖啡里,一面还在倾听着,仿佛对隔壁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
“我是不是会被牵连到这件事里面去?”她说,‘这太倒霉了,如果报纸上谈起我!尤其对白冰太太来说……”
这时候响起了轻轻的、可是很急促的敲门声。
她叫道:“请进!”
进来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皮大衣,光着脚,看到罗森魁梧的后背,她差一点要退出门去,随后她大着胆子咕哝着说:“我不知道您这儿有客人!”
探长听到这个粘乎乎的几乎象是被挤出来的声音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他看着她推上了房门,这个女人脸色惨白,眼皮浮肿。宇文娜丢过来的一个眼色证实了他的想法。她肯定是用壁房间里的吸毒者。
“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有人来看白冰……所以……我就自己……”她坐在床边,神色淡漠,象宇文娜那样叹气说。
“几点钟了?”
“九点钟!”罗森说,“看来您好象不喜欢可卡因,您!”
“不是可卡因……是乙醚……白冰说这要更好些……”她感到冷,站起来靠到暖气上去,并瞧瞧窗外说,“又要下雨了……”
一切都显得没精打采,梳妆台上的梳子上全是断下的头发。地上拖着宇文娜的袜子。
“我打扰您了,是吗?……可是,这件事好象很重要……白冰的父亲死了……”
罗森看看宇文娜,他注意到她突然皱了皱眉头,好似她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这时候,刚才讲话的女人一手托着下巴在沉思,并咕噜着:“嗯!嗯!”
探长立即问道:“您认识白冰的父亲吗?”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可是……等等!……喂,宇文娜,您那位朋友没有遇到什么事吗?”
宇文娜和探长交换了一个目光。
“为什么这样问?”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不太清楚……我突然想到,有一天白冰对我讲过,他父亲经常到这个旅馆里来……他觉得很有趣……可是他不想遇到他……有一次有一个人正在上楼,他飞快地退进了自己的房间……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好象是走进这个房间里来的……””
宇文娜不再吃东西了,搁在她膝盖上的盘子使她难以活动,脸上显露出担忧的神色。
“他的儿子……”她慢吞吞地说,眼睛盯在青绿色的窗框上。
“那么……”那个少妇大声说,“那么、是您的朋友死了……好象是一件胸杀案……”
“白冰,是啊!”
他们三人都感到有点儿意外,不说话……房间里寂静无声,只微微听到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讲话,足足过了一分钟,探长才接着说:“他是干什么的?”
“什么?”
“他从事什么职业?”
那个少妇突然说道:“您是警察局的,是吗?”她很激动,也许要责怪宇文娜使她中了圈套。
“探长是个好心肠!”宇文娜从床上跨下一条腿,俯过身子去搂她的胳膊。
“我本来早该想到了!……那么……在我进来之前,您已经知道了?”
“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白冰!”罗森说,“现在,您得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在一起才不过三个星期。”
“在这之前呢?”
“他跟一个大个子的红头发女人,她自称是修指甲的……”
“他工作吗?”
这句话使她显得非常馗尬。
“我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不做工作……他有财产吗?他生活很富裕吗?……”
“不!我们几乎总是吃六人民币一份的客饭……”
“他经常谈起他父亲吗?”
“他只谈起过一次,就是我刚才跟您说过的那件事。”
“现在在他房里的是怎么样一个人,您对我说说好吗?您过去遇到过那个人吗?”
“没有遇到过!那个男人……我怎么说呢?在我来到这里时,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执达员,我原来是这么想的,因为罗热欠别人的钱……”
“他穿得好吗?”
“等等……我看到一顶团帽子,一件灰黄色的大衣,手套……”
在这两个房间之间有一扇门,现在这扇门被帘子遮着,也许门已经被堵死了。罗森本来可以把耳朵贴在门上,就可以听到隔壁房间里的谈话,可是面对两个女人,罗森不愿这样做。
宇文娜穿起衣服,将就着用湿手巾擦了擦脸。
她很神径质,动作突兀,感觉得到接二连三发生的事超过了她忍受的能力,她感到难以应付,也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准备认命了。
另外那个女人比较平静。也因为她还在乙醚的作用之下,也许她对这类事情比宇文娜有更多的经验。
‘您叫什么名字?”
“王小娜。”
“什么职业?”
“上门服务的理发师。”
“在警察局风化科登记过吗?”
她摇了摇头,也没有生气。隔壁房间里传来的轻微的讲话声始终未停。
宇文娜已经穿上了一件连衣裙。她向房间四周望望,突然呜咽着说:“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真是一件怪事,”王小娜不慌不忙地说,“如果真是一件凶杀案,那是够麻烦的。”
“昨天晚上八点钟,您在哪儿?”
她想了想说:“等等……八点钟……噢!我在‘唐山’……”
“白冰陪着您吗?”
“没有……总不能一天到晚呆在一起……我是在半夜里,在喷泉街的香烟店里找到他的……”
“他跟您讲过是从哪儿来的吗?”
“我什么也没有问他……”
罗森从窗口看到外面的玄武门广场,广场中心的小公园,夜总会的广告。突然,他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
“你们两个等着我!”
他走出去了,敲了敲隔壁的房口,接看马上转动门柄走了进去。
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坐在房间中央唯一的一把扶手椅里,尽管窗子开着,屋子里还是充满着一股令人作呕的乙醚的气味。另外一个人踱步,一面做着手势。他是罗森头天晚上在孚白广场那个院子里遇到过两次的马冰先生。
“啊,您的手套找到了吗?”
罗森看着这位登记局公务员的两只手,他一下子面如死灰,以致探长有一会儿以为他快晕过去了。他的嘴唇在发抖,想讲又讲不出来。
“……我……我……”
年轻人还没有刮过胡子,他的脸色象纸一样白,眼圈通红,嘴唇柔软,这一切都说明他意志薄弱。他正用漱口杯在大口大口地喝水。
“请别这么激动,马冰先生!我没有想到在这儿会遇上您,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您的办公室里早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面前的那个人。这个不幸的人显得那么慌乱,他真很难不怜悯他。
从皮鞋到用赛璐珞架子支着的顶带,马冰先生十足是一个漫画上的公务员的典型,一个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公务员,小胡子亮亮的,衣服上一尘不沾,如果不戴手套出门,他一定会感到羞耻。
眼下,他真是不知道该把他的手怎么办,他的眼光在杂乱无章的房间里到处乱转,仿佛想在哪儿找到什么灵感。
“您能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吗,马冰先生?您认识白冰有多久了?”
他的表情不是害怕,而是惊愕。
“我吗?”
“是的,您!”
“那……从……从我结婚以后嘛!”他讲话时的表情似乎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
“我不懂?”
“罗热是我……是我妻子的儿子……”
“和白冰生的?”
“是啊……既然……”他恢复了自信,“我妻子是库歇的前妻……她生了一个儿子,白冰……她离婚以后,我娶了她……”
这句话产生了狂风扫乌云的效果。孚白广场上那座房子起了变化。事件的性质改变了。有些情况清楚了些,另一些情况却变得更加模糊,更加使人担忧了。
因此罗森不敢贸然讲下去了。他需要在脑子里理出个头绪来。他看看面前两个人,越来越不安了。
头天晚上,女门房曾经在院子里瞧着所有的窗子问过他。
“您是不是以为是这座房子里的人干的?”
而她的眼光最后盯在拱门上。她希望谋杀犯是从那扇门进来的,希望是一个外来人。
现在看来不是外来人!这件悲剧就发生在这幢房子里面!罗森讲不出理由,可是他可以肯定。
什么悲剧?他还一无所知!
他仅仅感到有一些看不见的线在伸展着,这些线把一些距离很远的点连接起来了,从孚白广场到玄武门大街的那座旅馆,从马冰的套间到王维大夫的血清公司的办公室,从尼娜的房间到那一对沉醉于乙醚的男女的卧室。
最使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象掉在迷宫里般的马冰先生的丧魂落魄的模样。他的眼神在寻找什么固定的注视点,但总是找不到。
“我是来通知白冰……”他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
罗森平静地盯着他看,简直可以说他在等侍他的对话者惊慌失态。
“我妻子对我说,最好是由我们……”
“我懂!”
“白冰是非常……”
“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罗森接着话头说下去,“他是很神经质的!”
年轻人正在喝他的第三杯水,恶狠狠地向他盯了一眼,他大概有二十五岁了,可是脸色憔悴,眼皮上已经有了皱纹。不过看上去他还比较漂亮,那种可以吸引某些女人的漂亮。他的皮肤无光,只是在他懒洋洋的神色中,尚未染上那种浪漫主义的怨天忧人的姿态。
“请告诉我,白冰,您经常看到您父亲吗?”
“有时候见到!”
“在哪儿?”这时候。罗森神色严峻地盯着他。
“在他的办公室……或者在饭店里……”
“您最后一次是在哪里看到他的?”
“我记不清了,已经有几个星期了……”
“而您向他要钱了吗?”
“每次都一样!”
“总之,您是靠他生活的喽?”
“他相当有钱,因此……”
“等等!昨天晚上八点钟左右您在哪里?”
他毫不犹像地回答:“在俱乐部!”他脸上带有一种讥讽的徽笑,意思是说:难道您以为我不知道您的意图吗?
“您在俱乐部里干什么?”
“我在等我的父亲!”
“那么说,您需要钱啦!而您知道他要到俱乐部去……”
“他每天晚上几乎都在那儿,和他的情妇在一起。而且,昨天下午我还听他在打电话时说过……因为隔壁房间里讲话这儿都能听见。”
“看到您父亲没有来,您没有想到去孚白广场他的办公室里去找他吗?”
“没有!”
壁炉架上有很多女人照片,中间有一张是罗热的,罗森拿起来放进了口袋,一面咕哝着说:“您允许吗?”
“如果您要就给您!”
“您不以为……”马冰先生说。
“我什么都不以为。这使我想起了要向您提几个问题。您家里和白冰的关系怎么样?”
“他不常来。”
“在他来的时候呢?”
“他只呆几分钟……”
“他母亲知道他所过的这种生活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别装蒜了,马冰先生!您妻子知不知道他儿子生活在沧州,什么工作也不干?”
这位公务员瞧着地面,显得很越尬:“我经常劝他要工作!”他叹着气说。
这时候,年轻人不耐烦地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说:“您看到吗,我一直穿着睡衣……”
“您愿不愿意告诉我,昨天晚上在俱乐部里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熟人?”
“我看见过宇文娜。”
“您跟她交谈过吗?”
“对不起,我从来不和她讲话!”
“她坐在哪个位置上?”
“酒柜右边第二张桌子。”
“您的手套是在哪儿找到的,马冰先生?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昨天晚上您曾在垃圾桶旁边、院子里找过手套……”
马冰先生勉强地笑了笑说:“手套在家里……您倒是想想看,我戴了一只手套出门,自己却没有觉察……”
“您昨晚离开孚日广场后,又到哪儿去了?”
“我在散步……沿着堤岸……我那时头很痛……”
“您经常散步吗,在傍晚,没有您妻子陪着?”
“有时候是这样!”
他一定感到很痛苦。他那双戴着手套的手始终不知做些什么好。
“现在,您去您的办公室吗?”
“不去!我已经打电话去请过假了,我不能让我的妻子处在……”
“那么,到您妻子那儿去吧……”
罗森仍旧留着。马冰先生告辞了,他尽量做得得体一些。
“再见,白冰……”他咽下一口唾液说,“我……我相信,你最好去看看你母亲……”
可是白冰只是耸了耸肩膀,不耐烦地瞧瞧罗森。可以听到楼梯上马冰先生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了。
年轻人一句话也不说。他的手机械地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瓶乙醚,把它放到更远些的地方去。
“您没有什么要声明的吗?”探长慢吞吞地问道。
“没有!”
“因为,如果您有什么话要说,以后说不如现在说……”
“我以后也不会有什么话对您说的……不,我有一句话马上就可以告诉您:您把事情完全搞错了……”
“还有,既然您昨天晚上没有见到您父亲,您大概没有钱了?”
“您讲得对极了!”
“那么您到哪儿去找钱呢?”
“请别为我担心……您能让我……”说着,他把水倒在脸盆里开始梳洗。
罗森不慌不忙地在房间里又踱了几步,随后走了出来,又走进了两个女人在等着他的隔璧房间。
这时候,最激动的是王小娜。至于宇文娜,她正坐在软座圈椅里,轻轻地咬着手帕,她那象在沉思的大眼睛注视着窗外的天空。
“怎么样?……”白冰的情妇问。
“没有什么。您可以回去了……”
“是他的父亲吗?……”
突然,她皱起眉头,神情严肃地说:“那么,他要继承遗产了?”她若有所思地走了出去。
在人行道上,罗森问宇文娜:“您去哪儿?”
她做了一个表示无所谓的手势,随后说:“我去‘蓝色磨坊’,如果他们肯再要我的话……”
他深为同情地注视着她说:“您很爱白冰吗?”
“我昨天就对您说过了:他是一个慷概的男人!……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我向您发誓……怎么会想到有一个坏蛋把他……”她流下两滴眼泪,不说下去了。
“就是这儿,”她说,一面推开一扇供演员进出的小门。
罗森渴了,他走进一家酒吧,喝了一杯啤酒。他还要去孚日广场,看到一架电话机,使他想起了他还没有到局里去过,那儿也许有急件在等他处理。
他要他办公室的听差听电话:“你吗,小翰?……没有什么给我的东西吗……什么?……有一位夫人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戴着孝……不是白冰太太吗?……嗯?……是马冰太太?……我这就来!”
马冰太太戴着孝而且她在司法警察局的前厅里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罗森不认识她,只看到过她在窗上的影子:昨天晚上三层楼窗口上那个可笑的影子,那时候她正挥着胳膊在破口大骂。
“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女门房这样说过。
还有那个可怜巴巴的登记局的好好先生,他忘记了他的手套,一个人跑到漆黑的洛河边去散步……
在罗森半夜一点钟离开那个大院子的时候,楼上玻璃窗上发出的声响!
他慢慢地登上了司法警察局灰溜榴的楼梯,
一路上和几位同事握握手,随后从半开着的前厅的门口伸进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