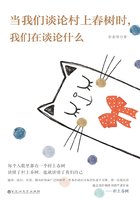40年代的散文创作,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却仍然呈现繁荣景象。抗战初期(尤其是1938年前后)报告文学几乎抢占了整个文坛,而当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大致是1940年之后)以后,以揭露抵制社会弊端为主要内容的杂文,又占了主角。
中国新诗在30年代,存在着以殷夫为前驱、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和以徐志摩、陈梦家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及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两大派别相互竞争的局面。抗战爆发仿佛突然抹平了这两大派别的对峙,民族解放的战歌几乎成为所有诗人的同声歌唱。中国诗歌会所倡导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战斗性的写实主义诗风风靡诗坛,成为不同流派诗人的共同归趋。这一时期的大量诗作,如郭沫若的《战声集》,冯乃超的《宣言》,臧克家的《从军行》《泥淖集》,徐迟的《最强音》,戴望舒的《元日祝福》,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等,都具有了时代共同的风貌,而诗人以往个人的风格反而淡化了。所有的诗都满溢着抗战初期的全民族大奋起的昂扬与乐观,抒情方式大多是直抒胸臆的宣言式的呐喊,叙述描写方式则回到了直接描摹、具体再现的简单粗陋形式上。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强烈呼声。诗人们运用民间形式积极进行诗歌形式的探索与改造,同时,为了使诗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斗争,接近群众,还出现了街头诗运动和诗朗诵运动,这都推动着新诗的语言和形式向着通俗化、散文化方向发展。正如朱自清所说,“抗战以前的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道路”,“抗战以来的诗又走到散文化的路上”这样,自由诗体在中国文坛上再次崛起,成为抗战时期诗歌形式的主流,出现了像田间这样的“时代鼓手”,其鼓点式的诗对抗战时期诗歌散文化、民间化倾向无疑是一个新的创造与推动。
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在亢奋的呐喊中,抗战初期诗歌艺术和审美特性的缺失日益凸显,越来越为诗坛和社会所不容。于是出现了对诗歌艺术的进一步探讨,以及对诗的形式美和个性的自觉追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诗歌流派,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是七月诗派。七月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等杂志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其主要代表诗人有鲁藜、绿原、冀汸、网垅、曾卓、芦甸、孙钿、方然、牛汉等人,他们继承了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正视现实,强调主观与客观、历史与个人的融合统一,以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一阶段,在大后方的西南联大,聚集着另一批诗人——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等,在他们周围还聚集着一批才华洋溢的年轻诗人:穆旦(查良铮)、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等。战争环境使中国新诗史上的主要代表诗人都集中于此。他们在这特殊的环境里进行着战乱流亡中的生命体验与思考,又在广泛吸取基础上进行着现代诗的思维和语言的探讨与实验。其诗歌创作的特殊风貌,给这一时期的诗歌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对以后的新诗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冯至在他的《十四行集》里首先实现了这样的探索和思考的成果,并且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果说战争在七月派诗人那里,唤起的是关于一个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在冯至这里,却转化为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与思考。同样是从身边的日常生活与自然中发现内在的哲理,在冯至这里,才真正成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并自觉上升到生命哲学的层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评价说:“由27首诗组成的《十四行集》”,是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冯至《十四行集》的整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使得它在40年代文学,以至整个现代文学中,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同时,它也表明中国现代新诗人,已经有足够的思想艺术力量,消化外来形式,利用它来创造中国自己的民族新诗。
随之而来的在新诗创作上有重要突破和影响的是中国新诗派的出现。受冯至等老一辈诗人的影响,同时也是因战争中特殊的生存体验,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青年诗人进行了更为深远的艺术探索,其思维、心理与审美,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抗战结束后,他们在北平、天津,与南方的杭约赫(曹辛之)、唐湜、陈敬容、唐祈等人联合提倡“新诗现代化”,强调诗的思维和语言的根本改造。最能体现中国新诗派的这种反叛性与异质性的是穆旦(1918—1977),他不仅在诗的思维、诗的艺术现代化,而且在诗的语言的现代化方面,都跨出了在现代新诗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从而成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中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诗人。
“新诗歌谣化”在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诗人那里,就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诗歌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有机部分。在40年代的敌后根据地,由于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诗的歌谣化发展到了极致,不但群众性的新歌谣创作蓬勃开展,诗人、作家也纷纷对民间歌谣进行搜集、整理、加工,使新诗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间诗歌资源成为发展新诗的主要资源,“诗的歌谣化”成为新诗发展的主要方向,“五四”时期所提出的“诗的平民化”主张被发展到了极端。“颂歌”成为新诗的主要内容与体式,诗歌不再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和民谣一样,表现群体的思想感情;表现手法不再注重抒情,而趋于对群众斗争与劳动生活的如实描写与具体叙述;尽量吸收借用民谣的形象原型、体式,语言追求朴实、易懂。该时期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这样的歌谣体新诗创作的代表作品。该诗借用传统“比兴”手法,完成了民间抒情诗体向现代叙事诗的转化,同时又保留了信天游诗体中的浓郁的抒情色彩。它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民间文学与农民文化对现代新诗的一种渗透与改造,另一方面,则是利用民间形式进行革命宣传、启蒙教育的一个尝试。这两方面都对以后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诗人们以空前的热情与勇敢,用诗歌做武器,参加了争取民主,迎接新中国的战斗。讽刺诗与政治抒情诗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潮流。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人不约而同地拿起了讽刺的武器。
20世纪40年代戏剧创作广场戏剧和剧场戏剧先后兴起。在国统区,抗战初期适应宣传抗战的需要,戏剧由剧场走向广场,兴起了广场戏剧,引起了戏剧观念、艺术表现、写作方式、演出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和“话剧民族化”的尝试。演出形式方面抗战初期的演剧队有许多创造,有街头剧、广场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谐剧等。面对文化程度不高而又长期受到民族戏曲熏陶的观众,广场戏剧的演出就必然地要吸取锣鼓、杂耍、曲艺等民间艺术,以及民族的音乐曲调。而反过来,广场戏剧对传统戏曲的这种利用,也推动了传统戏曲自身的改造。许多爱国艺人与戏剧工作者除了选择具有民族意识的传统戏曲作为宣传抗日救亡的武器,同时还以新的观点编写新戏曲。
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1943年的春节以延安的新秧歌运动为标志,抗日根据地一改演出中外名剧为主的状况,掀起了广场戏剧的高潮。这次转变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一方面要以民间形式来改造中国话剧与话剧工作者,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利用与改造民间形式,对广大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并以戏剧为突破口,推动整个文学艺术转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后,在群众性秧歌剧大规模创作与演出的基础上,出现了“新歌剧”的创造试验,先后产生了《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赤叶河》(阮章竞)、《刘胡兰》(魏风等)等代表剧作,而《白毛女》更成为现代民族歌剧的奠基之作。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的成功,带来了敌后根据地(与后来的解放区)文艺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促进了话剧的民族化。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剧作如《把眼光放远一点》(胡丹沸)、《抓壮丁》(陈波儿等)、《战斗里成长》(集体创作,胡可改编)等,都是在艺术上力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另一方面是促进了京剧、秦腔的改革,出现了《逼上梁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集体创作,杨绍萱、齐燕铭执笔)、《血泪仇》(马健翎)等实验性作品。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批原来活跃在战地宣传阵地的话剧工作者又逐渐集中到重庆、成都、昆明等大后方据点与香港、上海等大中城市,话剧又开始成为都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话剧运动再一次发生了向职业化、商业化的转变,广场戏剧向剧场戏剧倾斜。这一时期,大后方与孤岛上海剧场戏剧的创作出现了三次大的潮流:
一是历史剧创作的繁荣,这是与抗日战争中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重新认识与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文化思潮以及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相联系的。先后出现了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桃花扇》等优秀剧作。这些剧作与上海孤岛阿英(笔名魏如晦)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于伶的《大明英烈传》一一起,构成了现代戏剧史上历史剧创作的高峰。由于这一时期政治在民族生活中所占据的特殊重要地位,以强烈的时代性、现实针对性、高度政治化为其主要特征的上述历史剧,受到同样高度政治化的观众的空前热烈的欢迎,并且在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中国民族特点与时代特点的历史剧理论、创作的特色与传统,在现当代戏剧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出现了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戏剧创作潮流。在抗战中后期,大后方剧坛出现了一批歌颂性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长夜行》(于伶)、《少年游》(吴祖光)、《祖国在呼唤》(宋之的)、《法西斯细菌》(夏衍)、《岁寒图》(陈白尘)、《万世师表》(袁俊即张俊祥等)。这些作品有一个重要转变,剧作歌颂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已由抗战初期理想的民众英雄,转变为现实的普通知识分子。这表明了对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文学中理所当然的正面主人公的历史地位的一种确认。如果联系以后出现的对知识分子历史地位、作用的人为贬抑的极“左”思潮及其在文学上的相应表现,那么,这一时期正面歌颂知识分子的创作潮流,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的意义。
三是讽刺喜剧创作的发展。抗战戏剧中“暴露性”作品从一开始就闪现出讽刺的锋芒,具有喜剧的品格。起初阶段讽刺中夹杂着愤激,喜剧里内含着悲剧的因素;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讽刺的对象越来越集中在反动统治者,出现了政治批判性极其强烈的喜剧。在整个抗战戏剧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喜剧艺术自身发展的历史线索,形成一股最后成为时代戏剧主潮的喜剧创作潮流。在这一创作潮流中,影响较大的有陈白尘的《魔窟》《乱世男女》《升官图》,老舍的《残雾》《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等,袁俊的《万世师表》和三个戏剧“故事”:《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以及《美国总统号》,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妙峰山》等喜剧作品。
沦陷区处于殖民统治的高压下,出于商业的或纯艺术的动因,自发地出现了“剧场戏剧”的创作与演出的畸形繁荣。商业性演出的繁荣,同时意味着市民观众影响的加重。市民的生活、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欣赏习惯以及市民文化传统、语言等等,全面地进入了沦陷区剧作家的创作视野,影响甚至支配着他们的创作。这种“市民化”的创作倾向,与同一时期敌后根据地(与以后的解放区)创作的“农民化”,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戏剧(文学)创作的两极。影响较大的有姚克的《清宫怨》,秦瘦鸥、顾仲彝、黄佐临、费穆合作的《秋海棠》,杨绛的“喜剧双璧”《称心如意》与《弄假成真》,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