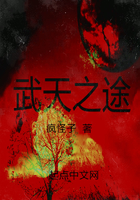概述
20世纪30年代,不同散文创作理路的作家朝着各自的路线探索追求,使散文发展走向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周氏兄弟仍然是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主角,各自代表了两大不同的散文流派。林语堂提倡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在散文文体的探索方面功不可没;夏衍的《包身工》的发表,使报告文学由这一时期的有意提倡而有了早期代表作。杂文、报告文学、小品文、抒情散文不同程度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中,对民族灵魂的开掘也有了历史的深度。
杂文从“五四”时的“随感录”、“语丝体”,一路传承下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再度形成了创作高潮。鲁迅不以“杂感家”为耻,大力倡导,对杂文的地位作用、文学价值都作了高度评价。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杂文作者。当时的左联作家实际上处于国民党当局实施的文化围剿的压迫中,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杂文就成了他们的首选文体。在对现实的批判和文艺阵线的论战中,发挥了投枪匕首般的战斗作用。这一时期杂文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杂文作者队伍庞大、新老交替以及流派纷呈,而且表现在杂文论争激烈,从杂文功能、效用到表现形式,不一而足。而杂文刊物的林立更是蔚为大观:不用说《萌芽月刊》《前哨》《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海燕》《芒种》《杂文》等左联的或进步的文学刊物,就是连《申报·自由谈》《东方杂志》等,在一个时期内,都刊登左翼杂文。这一时期的杂文可以用“鲁迅风”来概括。主要代表人物,除鲁迅、瞿秋白外,当推唐弢和徐懋庸。
唐弢(1913—1992)是有意识地师法鲁迅笔法的杂文家。他的杂文虽然不及鲁迅的深刻与广博,但吸收了鲁迅杂文泼辣善辩、警拔简练的笔法,形成了简约犀利、幽默沉郁的杂文风格。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杂文集有《推背集》和《海天集》。其中《谈礼教》《鬼趣图》《狗和养狗的人们》《文苑闲话》《看到想到》《东南琐谈》《<周报>休刊词》等篇,或批判封建文化,或抨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或揭发旧势力的恶浊……文笔锋利,击中要害,是政论和艺术散文笔调的结合。“孤岛”时期,他的杂文集有《劳薪集》《识小录》《长短书》等,侧重于从历史角度发掘社会病的渊源,在尖锐泼辣的批判中,将一切社会病毒都置于他的笔锋之下。他的杂文像鲁迅杂文一样,善于勾画世相,但缺乏鲁迅的那种剑拔弩张,在《从奴隶到奴隶》《略论吃饭与打屁股》《氓》《丑》《逃与趋》等篇中,西崽、汉奸、奴才等一个个可鄙形象粉墨登场,活灵活现,是“群丑”的展览。唐弢建国后虽仍有《学习与战斗》《繁弦集》《春涛集》等杂文集问世,但主要转向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
徐懋庸(1910—1977)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主要收集于《打杂集》《不惊人集》等。他的杂文也深受鲁迅的影响,林语堂曾误认其杂文为鲁迅所作。鲁迅曾为他的《打杂集》作序,称其杂文贴切,泼辣,能移人性,是有益的。这也概括了徐懋庸杂文的特色,但他的杂文没有达到鲁迅杂文的深刻程度,视野相对不够开阔,力度较小。《不惊人集》中的《揣》《“泼臭料”》《过年》《赏月》《上帝的心》以及《打杂集》中的《神奇的四川》《秋风偶感》《苍蝇之灭亡》等篇,都能较深刻地触及时事,于对时弊的针砭和社会人生的分析中交织古今中外丰富的文化史料,构思精巧。他用娓娓而谈的文笔,质朴流畅、尖锐泼辣的语言,记述生活片断,谈论中外掌故,别有一种风致,也给当时的杂文创作增添了异彩。鲁迅在为他作的《打杂集》序中说他“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并说“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徐懋庸来自生活底层,历经人世的磨难,反映在他杂文中的思想也比较沉实。徐懋庸建国后还有《打杂新集》等杂文问世,于原有拙直、质朴文风的基础上,在写作态度、内容、方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自觉的自我调整,提倡杂文的多样化,而在《对百家争鸣的逆风》《不要怕民主》等文,于直截了当的表达显得平和从容,《武器、刑具和道具》等文,机敏睿智而又语语中的,风采各异。在建国后当代杂文的第一次“振兴”中出力最多。
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在鲁迅和“左联”的影响下,还出现了巴人、柯灵、聂绀弩等众多杂文新秀,其创作成就大都在抗战以后。而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的繁荣更是“左联”因势利导,大力提倡的结果。
左联成立后,十分重视文艺大众化问题,号召工农通讯员运动,同时也将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左联”执委会先后于1930年8月和1931年11月两次做出决议,号召积极开展报告文学创作,并于“左联”领导的文学刊物上刊登了大量的报告文学理论和国外报告文学的优秀译作。袁殊的《报告文学论》,阿英的《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周立波的《谈谈报告文学》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理论文章。《光明》《中流》《文学界》是当时重要的刊载报告文学的刊物。周立波翻译的基希的《秘密的中国》,阿雪翻译的狄弥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都是当时著名的译作,对推动报告文学的创作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发表于1930年9月,记叙了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实况。东北“九·一八”与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各类报刊相继出现了一些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形成了初次的报告文学热潮。1932年4月阿英主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我国第一部以报告文学题名的作品集,标志着群众性报告文学的创作热潮和丰硕成果。1936年9月,由茅盾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征文集《中国的一日》出版,选编的近五百篇文章来自三千多篇应征稿件,是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记录。从而引发了20世纪4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潮。
报告文学以其新闻性、纪实性,和新闻记者有着不解之缘。这一时期,除了一般文学作家外,一些新闻记者也加入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生活》《大众生活》的主编邹韬奋和著名的进步新闻工作者范长江。20世纪30年代,标志着报告文学创作成熟的代表作则是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夏衍本是著名剧作家,但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在当时却产生了更为强烈的社会反响。《包身工》于1936年发表于《光明》杂志创刊号上。是作者在上海工厂区进行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后写成的。作者用饱含血泪的笔墨,真实描写了上海日本纱厂中国少女们惨绝人寰的不幸遭遇。这批少女来自农村,被骗到纱厂后又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包给了带工的老板,因而称作包身工。这群现代奴隶、一个个不戴镣铐的囚犯、一台台“没有固定车脚的活动机器”,在“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工厂里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收入,完全失去了人的自由而且还要遭受非人的虐待。作品以大量的事实,强烈控诉这种罪恶制度,并指出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而产生的一种“奇妙的方式”,也是万恶的殖民统治的畸形产儿。作者不仅对剥削者进行了愤慨的控诉,而且严正地警告说:“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鞭辟入里,铿锵有力,而又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包身工》的深刻思想内容是和艺术表现上的杰出成就相辅相成的。它的“不虚构,不夸张”的真实性;它的形象塑造的典型性;细节描写的具体性,以及在表现方法上,把艺术描写与新闻报道、社会调查的有机结合,使作品既有小说的细致刻画,又有恰如其分的理论分析,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结构上以形象的描写为经,以理性的分析为纬,把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和大量的数字列举以及分析说明交织起来,结构严密完整而又脉络清晰,是现代报告文学的珍品。
宋之的也是戏剧家出身的报告文学家。他的《一九三六春在太原》同样写于1936年,却稍晚于《包身工》。如果说《包身工》反映的是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国女工的悲惨命运,那么《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是在国内反动军阀白色恐怖下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用新闻剪辑的形式,为报告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另一范式。军阀阎锡山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厉行种种“反共”、“防共”措施,“流言所播,草木皆兵”,诬栽密告,“杀人展览”,无所不用其极。作品用自然界的春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两相对照,剪辑得当,笔墨犀利,讽刺辛辣,是反动派的“活画像”,也是老百姓的“落难图”。
报告文学是大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左联”提倡的结果。由于它总是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因而,更能迅速地在读者中产生一种轰动性阅读效应,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左翼作家不仅以杂文的创作和报告文学的提倡而引领这一时期散文的主潮,对小品文也同样是一往情深,成果非凡。茅盾这一时期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力图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生活,思想性和时代性都很强,如《速写与随笔》中的《雷雨前》等;艾芜在他的《飘泊杂记》中用朴素清新的笔调描写西南边陲的浪漫风情;叶紫有《古渡头》《夜雨飘流的回忆》问世,于气氛的烘托中,刻镂人物;萧军以他清新流畅、跌宕奔放的笔调讲《绿叶的故事》,其中《未完成的构图》《为了爱的缘故》是对和萧红患难中爱情的回忆;萧红的散文则更加诗化,她的散文于淳朴、清新、明朗中洋溢着一种抒情诗般的笔调,《商市街》《桥》等集子中的作品如《搬家》《雪天》《过夜》《破落之家》《初冬》等都写得富有才情,有一种天籁之美,以风格独特著称。而接近“左联”的吴组湘则以小说笔法写作散文,《泰山风光》写芸芸众生,写社会世态,写得丰富多彩,而又风光无限,引人入胜。郁达夫这一时期写有《屐痕处处》《达夫游记》,也因之成为著名的游记作家;巴金虽不是“左联”作家,但思想激进,爱憎分明,他的散文总是洋溢着一种激昂和炽热的感情。这一时期辑录的主要散文集有《旅途随笔》《点滴》《生之忏悔》《忆》《短简》《控诉》等,可见其小说之外,散文创作的功力,是心的歌唱。“左联”和它影响下的这些进步作家大都是小说家,他们不仅以多样化的散文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更以不同体裁的创作从不同侧面参与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20世纪30年代,“左联”以外,形成于北方的京派作家群在散文的创作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师陀、沈从文、萧乾等人的散文创作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散文虽然各具风格,却都虔诚地追求纯正的散文艺术趣味,注重散文文体的创造,在现代抒情散文的探索方面有着突出的建树。
何其芳是一位诗人,也是散文家。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画梦录》就以浓郁的诗情,精美的文笔而获1936年度《大公报》“散文文艺奖”,其中的《黄昏》《雨前》等篇以其艺术性的独创而使“五四”以来的“美文”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他还有散文集《刻意集》问世,都是“独语”式的心灵探索。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还乡杂记》中的篇章已从唯美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老人》《街》等篇,已从个人的“独语”转向了对人民苦难的关注。《星火集》《星火续集》都是作者到延安后的作品,其中有对抗战的讴歌,也有对反动派的抨击。另一位和他有着类似思想、文学经历的散文家是李广田。
李广田(1906—1968)作为“汉园三诗人”之一,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画廊集》晚于诗集《汉园集》出版,却以善于结构故事,用朴素细腻的文笔抒写深沉的感情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风格。抗战前,他还有《银狐集》《雀蓑集》等散文集,都追求一种朴野无奇的境界,于平庸的事物中,寻找美和真实,曾受到周作人的赏识。《桃园杂记》《山水》《山之子》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抗战后,在大后方,他的思想和文风都发生了变化。《圈外》《回声》《日边随笔》等集中的作品,或从侧面反映现实生活、或描写知识分子的悲欢与追求、或写大后方的见闻,生活面较为宽广,有些篇章如《他说:这是我的》《建筑》等趋向于杂文的笔法,明快畅达地发表议论,但艺术上显得粗糙,思想上的进步并没有和艺术上的跃进同步。
吴伯箫(1906一1982)散文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有一种清婉、幽远的情调。这一时期他把在《京报》《晨报》《大公报》文艺副刊等陆续发表的散文结集为《羽书》出版。其中《马》《山屋》《天冬草》等,或借马抒情,回忆生活的经历;或写山屋之景,景中有静;或讲天冬草的来历,表达对生活的憧憬,有着充实的生活内容,文字精炼沉着,韵律整齐和谐,读来朗朗上口,铿锵有致。
小说家师陀这一时期的散文结集于《黄花苔》《江湖集》,他写对小人物的同情,也哀叹北方山野的凋零。他的散文能触及社会问题,却不能加以明晰的反映,灰暗中时有暖意,哀婉中透出一股田园诗的风味。同样是小说家的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这一时期写有散文集《湘行散记》,于素淡清丽的文字中描绘湘西风土人情,表现出一种淳朴而宁静的意境。另一位京派小说家萧乾这一时期结集的散文有《小树叶》《落日》《废邮存底》(与沈从文合作)等,文笔自然流畅,委婉亲切。
这一时期在散文小品创作上做出了独特贡献的还有“开明”派散文作家群,代表作家有夏丐尊,丰子恺、叶圣陶等。叶圣陶是小说家,也是教育家。这一时期的散文主要结集于《未厌居习作》中,风格纯净平实,针缕绵密,能见出“开明”派散文为中学生提供习作范本的特点。
这一时期,除了“京派”作家和“开明”同人,抒情散文领域还有缪崇群、丽尼、陆蠡等散文家各以不同的风格,丰富了散文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