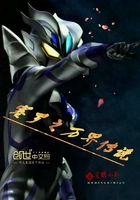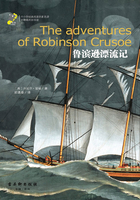1934年9月,四川军阀混战,局面不稳,谢居士觉得四川居住危险,想到苏州定居,向印老请示。印老回信分析苏州也有不安稳因素,如果战事一起,“则苏州之危,危于成都矣”。并告知安家费用不能随身携带,如果汇款,费用又很高,不值得。印老谦虚地说,对未来吉凶自己也不知,叫谢居士“至诚念观音一日,拈阄问其进止,或吉或凶,再做道理”。谢居士接到大师的信后,全家斋戒敬诵观世音圣号一日,然后在佛前拈阄,连拈三次,皆为留成都吉,于是决定不迁徙苏州。抗战后,苏州沦陷,果然不迁为吉。
其方法是,用小方块纸六张,如某事“可以办”写三张,“不可办”写三张,揉成纸团,在菩萨像前拈三次,每次一个,以两个相同的为定准。
而谢居士送给他的印光大师文钞中的教诲:“先尽人事,后听天命。人谋不及处,以三宝之威神是托,则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之转旋矣。”“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心若至诚,法法皆灵;心不至诚,法法不灵。” ……在这紧要关头都快速闪现在张耀枢的脑里。
他想也只有祈求佛菩萨这一条路了。
在张耀枢住地,有一处僻静房间,一直是作为他的佛堂,供奉着观世音菩萨。这一天夜深人静时,他来到佛堂,真诚到了极致地顶礼膜拜观世音菩萨,祈求菩萨为他指示一条道路以摆脱困境。
张耀枢用纸做成六个阄,“留”与“走”各三个,虔诚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后,拈阄,结果拈出的三个中两个为“留”。此时张耀枢心想:这留也太难了,怎么个留法?军事管制时期,县长兼师长,留在此地如何面对?越想越睡不着觉,于是半夜三更泡上酽酽的浓茶,一杯杯地喝着,在房间里整夜踱步,一直到天亮,体力实在不支,才迷迷糊糊地睡下。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来报:“外有一人称有重要事情请见县长。”
张耀枢忙传见客,只见来人戴着墨镜,称有要事相商。张连忙让人避开,把来人请进到内室,把门关上。这时来人去除化装,摘下墨镜,他才看清来人叫赵壁光,西充人,国民党师长,陆军大学毕业。
一年前,他找到“父母官”张耀枢,说自己是“兵败被俘”逃回来的,自己没当官了,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他,想请县长给他个“名分”(即官位)。张耀枢不知道事情原委,考虑再三,想自己是个“文官”,现在正是兵荒马乱之际,赵壁光毕竟当过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师长,于是让他做师部军事顾问并兼任师长。
1949年的一天,上面派了当时的省主席王陵基的一个师长作为专员来到西充。告知张耀枢:“得到国防部密令,赵壁光率部叛变,现潜伏本县,侍机作乱。国防部命令逮捕,由你负责!”当时张耀枢逮捕了赵,赵说冤枉。赵的妻子也来找张耀枢说情。
张耀枢对他说:“你回来无作乱,我可以证明,但你战场上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你说你没有叛变,你可找到证人来证明这一点。”于是赵壁光找到两个证人,张耀枢再根据赵写的材料出具了“保状”,并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张耀枢亲自带上证明送专员处,据专员说他也无权,只有送国防部。赵被押解重庆后,被押在西南长官署听候处置。后经乡人鲜英、张澜等人多方活动,又送上金条,加之民盟出面做工作,又有张耀枢的“保状”为据,国防部终于同意将赵释放。赵被释放后即不知去向。
其实,赵壁光在1948年11月11日,率残部二千余人在江苏徐州东碾庄地区投诚后,确实是受党组织派遣回县“潜伏”,为解放大西南做内应的,如果张耀枢去年不以身家性命出具“保状”,则赵壁光将是凶多吉少。
而此时,一大清早的,消失了的赵壁光突然来到张家,有何贵干呢?
这时的张耀枢才醒悟过来了:心想,此人不简单。
赵壁光很亲切地问他:“你咋个办啊,现在形势很危险。”
张说:“我主意还未定,必要时就转移。”
赵壁光说:“不能走,走是走不脱的。他们专门开会研究了你的事情。你在这儿为官三年无民愤,从未杀过共产党。你留下来,以后政治上还会有前途的。”
张耀枢忙说:“我不搞这些(政治)了,我都伤透心了!”
赵接着说:“你将来搞不搞是你个人的事,现在要保身家性命,只有这一条路。”
张耀枢信了他中肯的话,当时也的确别无他法,加上自己拈阄也是一个“留”字,就这样张耀枢才定下心来,并决定率部起义。
起义迎解放
1949年冬,时局愈加严峻。
张耀枢按照赵壁光的建议,首先将县府迁到附城山的一座寺庙里,以占领制高点,并以对付共军为由,构筑防御工事,以防暗算。驻军和特务很不放心,一次国民党特务借故上山搜查,所幸未找到证据。
同时,在赵壁光的授意下,张耀枢叫手下人在县内散布:县内的地下党正联络七宝寺的地下党将在西充武装暴动,结果将两个师先后吓跑了。
为了联络解放军,张耀枢出具县政府公函,交由一位女地下党员去找解放军。汇报西充情况后,部队的一位营教导员和张耀枢通电话,表示欢迎他率员投诚,但说自己的部队进军方向并非西充,希望张耀枢谨慎行事,并带回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文件。
张耀枢考虑不能再拖延,经地下党同意,他于当年12月率西充县机关法团宣布起义,与国民党决裂,并成立西充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及乡镇分会,作为过渡机构,维持社会秩序。
同月23日,改称西充县人民自治委员会,赵壁光任主任,张耀枢任副主任,地下党派一位叫赵仕奎的任秘书长,直至西充县人民政府接管。
在《西充县志?大事记》上,是这样记载的:
1949年12月12日,国民党最后一任县长张耀枢,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一军三十二师九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李长青的指示,派人前往南充联系解放西充的事宜。
12月13日,带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告》和《约法八章》等文件。
12月14日宣布西充接受和平解放。
12月23日,中共党员赵仕奎、民盟成员赵壁光、杨达璋、张抚均等组织成立县人民自治委员会,维持地方治安,听候人民解放军接管。
1950年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充。
……
1950年初,张耀枢率颜涓和不到三岁的儿子张正平及保姆离开西充,回到了文庙后街34号自己的家。
法师详述西充起义前后
关于在西充起义前后的这一段经历,昌臻老法师在不同的时间环境里,面对不同根基的人讲过数次,因而在史实基本相同的大背景下,老人有粗细之讲,断续之讲,略讲等,在细节处稍有出入,然而这并不影响史实本身。在下面将要向大家展示的是老人在圆寂前,最后一次极其详细地讲述自己在西充起义前后的心路历程,及自己的体悟。老人边吃饭边和侍者讲述,在轻松的聊天中,开示自然呈现其中,昌老的衣食住行,无不是在弘法。
以下是2008年侍者能慧、隆顺,在照应老人吃饭时的对话(根据两个时段的录音记录):
能慧:家里希望你老人家做什么?
昌老:希望我以做好人为主。他们以儒学思想为主,穷则独善其身,处乱世不要急于去求功名,我们当然功名心很切,看得到乱世,但是又舍不得放弃这机会,总想去试一试,自认为可以做得好。我又不想弄钱,还懂得一些如何做这些事情的道理,想去理论实践。(其实)想的都是脱离实际的,不做不了解,想的都是空想。
做了三年,很不好做。我第一不要钱,又懂道理,我自以为必定做得好,必定受欢迎,当时是那样想,当然做起来才知道,不是那回事。当然,我能够保到命,没有出大的问题,还是得力于我不想钱,我如果贪财的话,头都耍到地下了。
那时遇到很多事情,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的中央部队,打了败仗,都往四川跑,因为只有这一条路。他们全套美式装备,后勤部队都很有钱,与地方部队不同,后勤带了美国的奶粉、压缩饼干等,还有盘尼西林,拿到市场上,可以卖黄金(的价),那些押运的当官的已经一路卖起走,边卖边逃。他们又不敢卖多,怕不好交代,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经过一个地方,交给地方当官的,写一个收据,拿一部分好处给你,你给他收据,他就好交代了。
在当时,对县长是一个考验,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问题上遭起,那些东西很值钱,都是用大卡车装起,是一个集团军的后勤,他的办法是你吃多他吃少,但是你要打收据条。
能慧:逃到西充县后,他们想行贿你什么?
昌老:西充不当路,当路是资中、内江,当时乱跑,各条路就都挤满了。这种事不好处理,一个是自己会有贪心,想这一盘就完了,没人理麻(成都方言清查之意。——笔者注)你,存侥幸心理。下面的人都想我收,收了大家都有份。在这个关头,(我)能过关,主要是:深信因果,认为靠这种发财是不可能的,做这种东西,果报是很不好的。事情会怎么变,我们不晓得,由因果说话,我没有拿,但要说服下面的人是很难的一件事。
我倒希望下面的人帮我守到那个摊摊,不能散伙,不然谁都维持不下去。最后,“过路的财神”都要过完了,好多人来找我谈:这下一样都没有,人心思散,大家都要散伙。我当时有点怕,但心里考虑,如果要团聚人要给大家一些好处。他们问我,我也没有表态,但认为要看重这些矛盾问题了,最后来了一批军大衣,很好的,我就把它接手了,造了册子,打了条子,当时在岗位的人每人一件,分配时,也给我一件,我也要了。
后来,人民政府接管了,就有人检举,我当时还占了一个岗位,过渡时期的负责人,也被人检举了。我说好在东西都在,我带头退,按册子退。这个当然容易解决了。如果当时把盘尼西林、压缩饼干、奶粉接收了,肯定就变黄金了,肯定就拿不回来了,(大家)拿到黄金就要跑了。
后来,经过“三反五反”以后,一个西充人,留用的,后入团参军了,他给我讲一件事情:“三反”运动有一个专案,刚解放的时候,西充三家银行的金条子被人分了跑了。他们调查到(是)两个人,死了一个,在逃一个,下不了结论。专案组提出了一个意见:找当时的县长,可能要找他,这两个人一死一逃,那么那县长应该是知情人。
当时我已经在财经学院工作了。他们准备到成都来抓我,就在这个时候,在逃的这个人抓到,押回交代,结果没有我。审问的人认为不可能,说当时的情况,那个钱你们不交给县长,你们敢那样做?
当时从情理上说不通,以为他包庇我,要他交代。他说,这个人我们与他没有往来,我们知道他很胆小,不敢跟他谈,谈了就干不成。三家银行,两人负责,我们就先研究有好多金条,大家分好多。一天晚上就分了,当晚就离开西充,他(张县长)不晓得,晓得拿我们也没有办法。
结果就给我洗脱了(罪名),我认为这是佛菩萨的加持,如果当时把我抓了,我晓都不晓得。那时(解放前夕),哪个管这些事哦。我遇到的难题多得很,管不了这些事,我们那里的团队多,当时国民党还有两个师在那里。要解决你那个事容易,当时赵壁光,我们住到山上了,如果我们弄就遭起了。
他(赵壁光)懂军事,他与地下党有联系,他感恩于我,是我把他保出来的。我当时很天真,认为他不会与共产党有关系,他是民盟的人,民盟是被共产党领导,他是川北地区策反委员会主任,我当然不晓得。
赵说他是陆军大学毕业,国民党师长,兵败被俘,在押解途中,他逃跑了。我想,那时候,几个集团军垮,你几个师长被俘,容易(得很)。但是根据国防情报,说他是叛变了,回到西充是伺机作乱。专员也很世故,他对我印象就很可以,他说,你是文官,但是现在要会武啊。我叫他派人来,我想辞职,他很同情我,说我是文人,后来我辞职打电话告诉他,他也不敢。县长必须要政府任命,他领导我们,但做不了主。
我们这类人是不适合政治的,头脑里想的东西都很书生、天真。所以对赵,我想不到,后来赵跑了。(上峰)就拿我是问,怀疑我了,我把他(赵)叫来问,他说,活天冤枉,我绝对是兵败被俘,逃脱的。我说,我没有到前线去,这个事,你要找人证明,他说没问题,南充好多军长都晓得。不久他就找来了,证明是一同逃跑的。他两条罪状:1.兵败被俘,我们这些就那么天真,就相信他说的是真的;2.回到本县潜伏伺机作乱。我说他一直当我们的军事顾问,做戡乱工作。戡乱,国民党先安内后安外。他当时确实是在协助我做工作,看到我敢正大光明地保他,当然责任有人负了。他们就把他送到了国防部,国防部当时也弄不清楚,摸不透,后来我问他咋出来的,他说:当然你的保条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金条子。
民盟副主席,叫鲜英,西充人,是老牌师长。他是儒将,儒释道精通,有著作,有学问,很有钱,重庆的公馆就叫做特园,毛主席在重庆协商谈判在他那里住了几天,宴请民主人士等,都在他那儿。他那里特务都不敢去,他是四川的地头蛇,不敢惹他。他很有钱,在重庆办了一个嘉陵中学,一个巴蜀中学,掩护了很多地下党员,他有他的一套搞法,他拿钱给国防部的头目,就放了赵,那些人(收钱)胆子大,有保状,弄错了,有人抵(他们不怕)。
当时如果一旦真正查起来,我的头就保不住。自己很幼稚,把问题看得很简单,没有出问题是佛菩萨保佑。那个时候,国民党的保状印得很大,有字:本人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
当时送去盖印的时候,负责盖印的那人已经60多岁了,我到那时没有带人去,都是以前的。他们又不能做什么,我不弄钱,他们不敢乱来。盖印的人对办公室里的人说:“这个老几(四川方言,“家伙”之意。——笔者注)的胆子大啊,他有几个脑壳啊,他来好久哦,弄不弄得清楚赵是啥子人哦?他敢用身家性命担保。”另一个说:“算了,算了,人家喊你盖你就要盖,这个事情,反正不用我的头去顶。”后来才听别人告诉我这番话,更觉得是佛菩萨加持,我们对政治是不行的。
当时,与他谈不上关系,只是觉得跑的人太多,说他没有根据,国民党当时跑的人太多了。比他官大的都多得很,就这样,我完全相信(他)。当时一批批跑,一批批押起,中间逃很容易。
我当时想,他当师长,连房子都没有在城头,也没有公馆,在农村里,半耕半读,相法上看,长得也是仪表堂堂,30多岁的样子。也没有什么阴谋诡计的相,我就是凭直觉,当时叫我保,我就敢保。
当时他们已经怀疑我了。不准让他跑,跑了拿我试问。保他也危险,不保他也危险,鲜英在西充也办了巴蜀中学,当时的校长是王瓒绪的侄女,北师大毕业的。王瓒绪,当时是重庆卫戍总司令,当过四川省主席,是清末秀才,会写诗(写)书法,他还送过诗给我。他的侄女办教育很内行,掩护了很多地下党。
(当时)特务找了很多证据材料,但是特务不能逮捕人,逮捕人要县长(批准),可是县长也管不了特务。特务局来给我说,某人是共产党,把材料给我说,请我批准材料就逮捕人。我说你们不要那么轻率哈,她的背景是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瓒绪,你哪里惹得起?我说,我是惹不起的,西充是两派在斗争,这个是整人的,也是要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