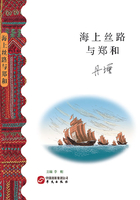不妨从现在开始,为与我们今生有幸擦肩的那些生命,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那或是一头牛,一条狗,或是一棵树,一朵花,或是一只蚂蚁,一粒种子……
为陌生人的纪念
文/安石榴
一
那一年雨水丰沛,镜泊湖吊水楼瀑布非常壮观,游人暴增。以我的身高,已然不算矮小了,但是马上淹没在观瀑的人群当中。瀑布巨大的轰鸣不断鼓动人内心的渴望,可是观瀑的地方就那么大,没有延伸的余地,保护铁链钎在壁立的火山岩石边上,下面几十米处是令人晕眩的黑龙潭,壮阔的瀑布瞬间奔腾砸进深潭,力量的美足够让人胆战心惊。
全景观瀑最好的角度是平视,非其他瀑布的仰视。由于这个独特角度的限制,人们的热望越来越高,后面的人想挤到前面去,而前面的人总想多流连些时候。这不怪。吊水楼瀑布是当时镜泊湖著名的八景之首,而且,并不是每年都可以达到如此境界,自然景观也是一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显现绝佳的姿色。
现场没有出现混乱,但是解决不了众多游客的愿望,群众总是有智慧的,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瀑布全景的人,突然发现观瀑台对面,也就是瀑布的左手(我们在右手),只有零星的几个看客,而空间却和我们这边相称。但是,怎么过去呢?两种可能。乘游船绕过遥远的湖水,在某一个船坞上岸,然后爬到上面去。另一个方法,直接从瀑布上面走过去!
吊水楼瀑布在突然垂挂下来之前是平的,非常平的岩石,怎么说呢?看上去,就是流动着水的一块平整高原。我曾经在某一年的深秋,就是这样从瀑布右手走到左手去的,跳过露出水面的小块岩石,到对面的时候鞋都没湿。但是,今年可能吗?丰沛的水流奔腾出震耳欲聋的气势,夺人心魄!
我身边的一家人,五口。那个大男孩右臂搂着一个靓丽的女孩子,他跟父母说,我们从上面走过去吧。母亲牵着手的小妹妹说:不要,我害怕。但是最后就这么决定了。五口人绕过一段火山岩石路,走了上去。我在他们离开我身边的时候很赞赏他们带着勇气的决定,但一旦他们走进水中,心就突然紧张起来——由不得不紧张。大男孩一手牵着女友,一手牵着妹妹,父母十指相扣,母亲连着女儿。远远看,五口人连成细软的线。当他们移到水流中央的时候,在脚下巨大的震颤下,细软的线崩断了!小女孩扑倒在水中与哥哥分手,母亲甩掉父亲的手,企图全力救护女儿,母女脱离家人被湍急的水流推动翻滚,父亲愕然呆立,哥哥牵女友的手没有放松,他奔过来要用右手抓母亲和妹妹,结果女友先扑倒,随后大男孩倒下,咫尺之外的父亲义无反顾地冲上来,但是完全没有用了,悲剧发生:他们一个跟着一个,翻腾着卷入水流,随着瀑布落下去……
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旅游业还不完善,设施更不完备。可是,二十年过去了,五口人、一家同时毁灭的情景从来都不能消失殆尽。我知道于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某一个西风乍起菊花遍地的日子,或者连绵的夏雨不断敲击窗棂,或者大雪纷飞、柳絮纷扬,它们合力造就的忧郁氛围中,我会想起他们,一家亲亲爱爱的人,活活泼泼的人,漂漂亮亮的人,陌生人。我总会默默地在心底说上一句:安息。
二
2007年9月29日。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某一栋楼。走廊。我在等待做钡透。当时我觉得我病得很重,我的感觉非常不好。钡透之前的几天我已经在协和医院拥挤的环境中做了几个检查,钡透是最后一个。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待叫号。我并不想参与病恹恹的交流,病友们在互通信息。
我只在别人问我的时候简短回答几句。后来,有个老太太碰我一下,说:他和你一样。我看看他,那是个很年轻的男人,三十二三岁的样子,他看着我,带着询问的表情。
你得相信,有人面善,有话缘。我于是站了起来,我们一样高,一样瘦得不堪。我问他:怎么样?
他说:不好。我问他:多久了?他回:我来北京三个月了,先在解放军医院,后转来协和的。我问他:现在如何?
他竟然笑了:协和医院把药给我用遍了,我现在没得药吃了。
我问他:做胃镜了?他说:医生不敢给我做了。我心里陡然一惊。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并不是医生胆子小。停了一下,我问他:吃东西?他回我:给我配的营养水,今天突然喝不下去了,所以医生让我做钡透。我低下头,颓然坐下,不想让他看到我惊惧的脸。我捧着自己的头没有和他再交流。我先做了钡透,做完,我从走廊另一侧离开,没有和他,也没有和任何病友打招呼。现在,三年过去了,我依然活着,也还很好,体重恢复到原来的九十五斤。每次感念命运恩惠从我心底泛起的时候,我会轻轻问上一句:你好吗?那个年轻的男人在我的记忆里永远苍白而奇瘦,一张没有忧伤恐惧的和善的脸,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知道他是山东人。
为生命取个温暖的名字
文/闲云
荷兰有一家神奇的奶牛农场。说它神奇,是因为这个农场饲养的奶牛每年的产奶量,总是比其他农场奶牛的产奶量多出500品脱。这个神奇的差距,令许多研究者着迷,品种、牧草,水源,圈舍……人们用尽了各种科技手段,也没有检测出这些奶牛和其他奶牛有什么不同。后来,有人找到了这个差别:其他农场主只是把自己的奶牛看作一群能挤奶的动物,而这个农场主却给自己的每头奶牛都取了一个名字,在牧牛过程中,他用名字温情地呼唤它们。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充满爱心的名字,使每一头奶牛都生活得愉悦轻松,可以产出更多的牛奶。
其实这个故事并不神奇,因为在我曾经历过许多这样的生命。小时候在乡下,任何生命都是有名字的。我们将家里养的黄牛一般叫大黄,马叫兔儿,骡子叫小黑,狗叫花花,屋檐上的燕子叫剪刀。甚至院子里的树和园子里生长的花草,也都会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果孩子们捉住了蛐蛐,黑的就叫它精灵鬼,黄的就叫它金刚。因为名字,人们和这些生命有了休戚相关的感情,牛、马和骡子干起活来,格外卖力气,小狗忠诚地看家护院,燕子年年都不忘再回来,大树和花草总是充满生机。那时候,淳朴的乡下人把一切生命都当成了朋友和家人。我无数次看过一头牛临死前的情景:主人一家难过得无语流泪,如同失去了亲人,而那牛躺在地上,依恋地看着主人一家,眼里也流出眼泪。看家的狗死去了,主人绝不会剥皮吃肉,而是选一个僻静的地方,在夜里悄悄埋了。
和人的名字一样,每一个为生命所取的名字,都是一个温暖的符号,它贴近了人类和所有生命的距离,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灵都平等对话,和谐共处。
每个人都会有丰盈美好的记忆,而这些记忆,总是由许多名字组合而成,除了同类的名字,更多的是其他生命的。这些名字,会成为我们记忆中一颗一颗闪亮的珍珠,它们让我们感觉到了岁月的有情和难忘。
对于那些被赋予名字的生命来说,名字,绝不仅仅只是几个条件反射的音节,因为每个生命都存有爱恶与灵犀,不被关注,缺少温暖的生命,当会情绪消极,缺乏生机与活力。而那些被尊重,被宠爱着的生命,才有了幸福感,有了诗意生活的力量和希望。
不妨从现在开始,为与我们今生有幸擦肩的那些生命,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那或是一头牛,一条狗,或是一棵树,一朵花,或是一只蚂蚁,一粒种子。
感谢一只流浪猫
文/辛利
这是一个飘着雪花的黄昏,我站在阳台向楼下俯瞰,一个人与猫的故事在街上上演。楼下有一个公交车站点,有大约七八个人正在焦灼地等车。而在距人群不远处,一只流浪猫在寒冷中徘徊着、嘶叫着,它显然无助到了极点。最后,它向等车的人群走去,也许,在它看来,在这冰天雪地的钢筋水泥世界里,只有不远处的人类才是自己最可依赖的吧。
猫钻进了人群,人群开始骚动。一个年轻女人一声尖叫,她身边的男人开始用力踢那只猫,猫挣扎着再次钻到人群,人们开始不停地躲着它、避着它。猫的希冀一个个都破灭了,它只好依旧无奈地趴伏在离人群不远的雪地上悲伤地哀叫。这时,我看到一个推着垃圾车的清洁工走过来了。这是一个年过五旬的老妇人,她显然发现了那只流浪猫,就俯下身子轻轻地把她抱在怀里,猫就不再叫了,乖乖地偎着她,并用舌头舔着她的手。老人用手拭去它干涩凌乱毛皮上沾满的灰土,然后脱下外面的褂子,把猫严实地裹在里面,放在马路边一个避风的墙角里,然后离开了。所有的人都看着这一切,肃静无声。
几十秒后,事情出现了令人想不到的逆转。其中一个男人把新买的电饭锅从纸箱中拿出来,他拿着空纸箱,走到那个墙角,把猫放在了空纸箱里;接着,有两个小学生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们从书包里拿出几包小食品,撕开包装,放到了那个纸箱里;还有两个男人走到纸箱旁边,他们好像在商量着什么,然后,一个男人拿出手机开始打着电话;公交车开过来了,开始尖叫的那个女人突然着急地与她身边的男人耳语着什么,最后,她跑过去抱起那个纸箱,和男人上车离开了。本已为事情就此结束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那个清洁工人又神色焦急地回来了,她来到原来放猫的地方驻足了很久,才推着车离去。
流浪猫应该感恩所有刚才救助过它的人,但是换个角度想那些动了恻隐之心的人,他们更应该感谢那只流浪猫,是它,救活了他们即将枯死的心灵。
橘子酸,橘子甜
文/乐都凡尘
冬天的时候,母亲生病了,城里的一个亲戚拎着一兜橘子来看望。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于乡下的孩子而言,能吃到一颗水果糖就已经幸福得流蜜了,如果能吃到甜甜的橘子,那更无异于过一场盛大隆重的节日。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一幕。亲戚走后,睡在床上的母亲让哥哥拿来那一兜橘子。我知道,她要给我们姊妹分橘子。人小心大,排行最小的我,贪婪地盯着那盘放在瓷碟子里的橘子,昏暗的灯光下,橘子光芒四射,引诱得我口水一阵阵在胃里翻江倒海。我是多么希望母亲把那最大的橘子给我啊。我用舌头舔着因为冬季的干燥而起皮的嘴唇,一会儿望着橘子,一会儿望着母亲,祈求的眼神如丝一样,越扯越长。
母亲慈爱地摸摸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个很小的橘子。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橘子,委屈的眼泪掉了下来,我是多么希望得到一个很大的橘子啊。我没有立即吃掉那个橘子,我想把它带到学校。晚上睡觉时我把橘子紧紧地攥在手心,舔着冰凉的橘子皮,不知不觉睡着了。
那时候上学很早,天还没有亮就要早早起床到学校。没有人给我们煮早饭,我们的早饭就是两个放在蒸笼里的馒头。厨房里的灯坏了,在黑暗中我将手伸进蒸笼,我摸到的不是柔软的馒头,而是一个冰凉的大橘子!这让我无比欣喜,我想是母亲特意给我们留的带到学校吃的,我将手又伸到里边,摸到的是一个小橘子,再摸,是一个馒头。拿大橘子还是小橘子,我犹豫不决。在姊妹当中我的地位并不高,学习并不好,大橘子肯定是留给经常帮着干家务活,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姐姐吃的。内心的贪婪使我将大橘子装进书包。
在课堂上我无心听老师讲课,满脑子全是诱人的橘子的味道,我盼望着早点下课,心里默默数数,一秒、二秒,数到六十秒,又从一秒重新数到六十秒,周而复始,以此计算下课的时间。愣愣怔怔中那只橘子如同长上翅膀的燕子,飞向我空洞的胃部。
终于等到下课了,我迫不及待地拿出那个橘子,躲到无人的角落,像科学家从显微镜审视肉眼看不见的化学物质一样观察橘子。我想吃,但又舍不得吃,不敢吃。我怕回到家中挨母亲的斥责。味蕾上涌起一股股酸水,舌头如同一只钩子,恨不得一下子把那只橘子钩进嘴里。最终,我把那只橘子放进书包,带回家。又悄悄放到蒸笼里。
晚上,母亲把我们五个姊妹叫到跟前,她表扬姐姐,说她懂事,爱怜弟弟,把大橘子留给弟妹,而自己却舍不得吃。母亲的话还没说完,姐姐和哥哥把各自的橘子全部捧了出来,说:“妈,你身体不好,还是留给你吃吧。”就那样他们把带有手心温度的橘子交给了母亲。
母亲把大橘子切成几瓣,把很大的一瓣给了我,把其他的给了哥哥姐姐。我们分享着冬夜里的温暖和甜蜜,仿佛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大橘子酸酸的,根本没有我所预想的那么甜。母亲看穿了我们的心思,又接连切了几个小橘子,我只顾自己,接连吃了几瓣,果汁从嘴里流了出来,那个甜呐,仿佛渗到骨头里了。姐姐吃得很慢,她说:妈,你也吃吧,小橘子可甜了!等到盘子里的橘子只剩一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吃一点。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姊妹为橘子到底是甜是酸而争得面红耳赤。妈妈说:别争了,好好念书,长大了你们天天有橘子吃,想吃多少,吃多少。
我暗暗发誓,努力学习,长大了考上大学,有了钱让全家人天天吃上又大又甜的橘子。第二年姐姐考上了一所师范。三年后她有了工作,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她买了好多橘子。就在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吃橘子时,姐姐说:“如果拿橘子来比喻人生,一种橘子大而酸,一种橘子小而甜。有的人拿到大的就抱怨酸,拿到甜的就抱怨小。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吃橘子的情景吗?当时我拿到小橘子,我就庆幸它是甜的,拿到酸橘子就感谢它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