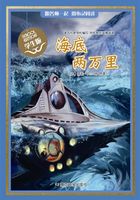只有一名男侍者,斜趴在服务台上,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审视眼光端倪着推门而入的周良。周良能从他因为疲倦而毫无生气的脸上看出一丝来不及掩饰的惊讶,此刻已近凌晨三点,属于夜晚而对白天充满敌意的人们尚且已转移阵地,酒精已向睡眠妥协或者发酵成更赤裸更纯粹的求欢心理。总之,相对于一些洗浴场里至情至性的服务,酒精在此刻已显得不合时宜。
酒吧里因空旷而显得狭小,空气中凝固着潮湿的烟味、过量的酒味以及令人恶心的呕吐气息。五平方左右不久前还挤满了诱人但并不火热的女性胴体的寄予众多正派与不正派男人眼光的舞台上,已经只剩下一条黑色的软塌塌的表演裤,其丝状的质地极像被弃之不用的蛇皮,泛着清冷、僵硬而肮脏的死光。而明晚,它将再次套在某位酒吧女郎的或瘦弱或妖娆的大腿上成为诱惑男人的工具。
在酒吧的尽头,唯一的顾客在抽烟,她的疲累从染黄的卷发里,从笼罩着黑色丝袜的暗红色罩衫里,乃至从双指间腾起的烟雾里都乍然呈现。她的面前摆着一瓶已经只剩一半的二锅头。
周良尽量显得有精神地朝男侍者打了个响指,示意他来一瓶同样的二锅头。但得到的不耐烦的答复是这里从来不卖这种劣质酒。
周良几乎未经思考,就快速走到那女人面前坐下。如果非要给他这个动作一个世俗的理由,那么男侍者嫌恶的表情再合适不过了。他还与其身份极不相称地嘟囔着,真是臭味相投。这话对周良而言恍若推动器,因为他还不习惯与人发生争执,特别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刻。即将与人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总是选择离开,而现在,又不能走出门去。
那个女人正盯着墙壁上一幅粗劣仿制的梵高的向日葵出神,面前的杯底还残存一点点酒。她面色彤红,表情憔悴神色萎顿,眼睛里满是疲倦和朦胧但却有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炯炯有神。总之,她看上去十分年轻。
周良很重地坐到她对面,从她面前拖过酒瓶,在冰冷的玻璃桌面上发出尖利的摩擦声。女人只是略微侧过头瞄了他一眼。
周良把自己的杯子倒满,然后把酒瓶举在半空,作势欲给她加酒说,没二锅头了,借一点,我叫周良。
女人把杯子推到中间,轻柔地抿嘴一笑说,不用客气,这里只是一个与酒没有太大关系的消遣场所,正常。我叫阿美。
周良带着一种回忆往事的神色说,是的,那年我去一个江城,也是这样一个初秋时分。我往一家仓库去闯,想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或者一辆去外地的运货车。我当时只想尽快能离开那个城市,而不管去哪里。那个城市很冷酷,像冰棱般刺人,或许这样形容也并没有表达我的意思。我已经四天夜里没地方睡觉了,城管、园林管理人员、甚至环卫工人都对我大呼小叫拳打脚踢,要知道,我并非真正的流浪汉。只有坐地分赃的小偷们偶尔还对我示以温情,有天夜里,他们还请我喝了许多酒,抽了许多烟,那是他们大获全胜的一夜,据他们说,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我不得不说,他们并不是些坏人,看着他们兴奋地干杯,我发自内心地为他们高兴,他们豪气冲天的样子,使少年时代的武侠书中绿林好汉的形象再次在我面前鲜明而切实起来。不怕你笑话,我年轻时这样的遭遇非常多。其实,我想说的还是酒。那个初秋的夜里我往一个仓库里闯。一个看门的老头喝住了我,我趴在窗户上与他交涉。他正在吃晚饭,一只煤火吊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白萝卜和肉,边上放着一瓶二锅头。老头满脸被酒气浸润得幸福无比。所以说,喝酒还是要一个人细细品尝。
阿美略微颔首。她起身去把面向街道的落地窗帘拉上。窗帘原先的质地和颜色已完全被各种酒精饮料和一些无处发泄精力的肮脏的手完全篡改。但有时肮脏却能让人感到温暖,就像拥挤或者醉酒才能真实地感到自己存在一样。重新落座的阿美很长时间才说话,尽管疲惫之态清晰显露,但她的言辞之间总有隐约的笑意——或许这本出自她的天性。阿美说,你看上去依然很年轻。我同意你关于喝酒的观点,很多事情都只能一个人做。
周良举杯找她干了一口,淡淡地说,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阿美没有抬头,眼神在空荡荡但又没擦拭干净还残留着些许唾沫或者呕吐物的桌面上来回穿梭,带着一种周良意想不到的玩世不恭的戏谑语气说,就是那么回事,说白了,这里和它的名字一样粗俗可笑,当茶楼这种再古老不过的场所都变得肮脏的时候,这里再不和纯粹的生理有关就万分令人意外了。我天天在这里。
周良深深地靠进座椅里,极力克制自己说话的欲望,但没有成功。柜台后面已经传来放肆而温馨的鼾声,酒吧侍者和妓女一样,同样需要睡眠和睡眠的恢复。周良聆听了很长时间还是忍不住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开夜班。我厌恶噪音,直接说吧,我厌恶肥城白天的一切。不过肥城的夜晚我也不怎么喜欢,只是相对白天我容易忍受些。我宁愿深夜里在街上开车溜达,我时常突然想聊天,于是随便找个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寂寞甚至同好的路人载他一程,不收钱,说好只是聊聊,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说,坐着就挺好。你知道,想在深夜大街上找一个同好再容易不过了,我能一眼看出来谁和我一样厌恶肥城。你应该也是,这么说你不反对吧。
周良来不及等阿美表态,这个夜晚他的诉说欲望如此强烈,仿佛很多天的沉默寡言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罢了。而且他意识不到他言语中的身份虚构和有关性欲的倾向,角色的转变是那般自然,连他自己都不以为意,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本就潜存于他的身体之中。似乎他的身体里真存在一个未及设防的突破口,喷涌而出的话语像亲眼目睹自己身体某处的伤口正在爆破鲜血汩汩而出一样使他有了一种难得的快感。
周良急速地说,但今晚我遭遇了一件怪事。一个女孩急冲冲地上了我的车。我有个怪癖,从不带女客,有意思的是还真有那无聊透顶的人去投诉我拒载,我才不管他妈的。今天晚上那女孩拼死才拦住我的车,死乞白赖地求了我半天,说她有急事,我信了,她的脸色确实像尿憋的时间太长了涨得通红又发暗,于是,我破例了。破例总不会带来好运。
果然,她一上车就很放松地七仰八叉地靠在后座上。我问她去哪,她想了半天却说还没想好,让我随便开。我不想跟她争执,就沿潜山路笔直往北跑。大约十几分钟的时候,她在后面唉声叹气说她想好了,就到梦幻演义酒吧。我本想劝诫她如此深夜一个小女孩去那种地方不好。你别介意,我没有其他意思。但我从后视镜里瞄着她的时候却发现她面部的化妆及表情妖艳无比。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一路无话,我把她送到这里。她又在后座幽幽地说,大哥,我没钱。我有点火了,转过身去喝斥她,并给她指计时表上的三十多块的数字。她仍然说没钱,并当我面把所有口袋掏遍,以示她确实分文没有。我不同意。其实我不在乎那点钱,只是突然觉得这样的夜里与一个陌生的女人吵吵很有点意思,我想看看这种状态下她如何收场。令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很抱歉地说,我想到了的,当时甚至有点渴望她这样做,她突然扒开上衣露出洁白的胸脯,里面没有穿胸罩,她说大哥,这下好了,我们给看一次五十,这次优惠你。她看我悻悻的样子,近乎顽皮地笑起来,说你再不让我走,我再脱一次给你看,你就要倒找我钱了。我也笑起来,眼睁睁看着她走上台阶。这事发生在两小时之前,我想来看看她是否还在。
阿美轻笑起来,脱口而出说,可能是小绿,只有这鬼精灵的家伙才干得出如此顽皮的事情。
周良试探地说,她应该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孩子吧。或许开一个酒吧也挺好?
阿美似乎没有听到,又侧头看那幅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