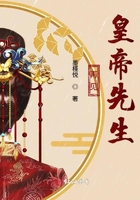当天晚上,我总想找个机会单独问问韩国佬,王蓓现在怎么样。直到睡觉我也没找到机会,不过当晚我梦到了王蓓。
在梦中,我站在大雨里,王蓓走在雨里,但我看不出她是在走向我还是在离我远去。雨一阵阵洒在我身上,我只能看见自己的睫毛挡住了视线。不久,王蓓就不见了,再不久,王蓓就又出现在我面前,抬头看着我,她的头型居然跟阿明一样。我变得害羞,不知道该说什么。王蓓说:我还剩三个月了。
我夹起一块肥腻的红烧肉说:好久不见。这时候我已经感受不到雨水了,只能听见雨声,淅淅沥沥,不可断绝。
王蓓说:今天我们上第三课。
我说:老师,外面下雨了。
接着我闭上了眼睛,听见了雨声。我醒了,外面传来雨声。醒来之后我又适应了很长时间,渐渐相信外面真的下雨了。我突然感觉心情愉悦,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有听见雨声。总之梦到王蓓令我很长时间里都难掩激动心情,即便这场梦境混乱不堪,我甚至看不清王蓓的脸。我的梦里看不清王蓓的脸,原因可能是我忘记了王蓓的样子。
我又摸着黑走到门外,摸着黑又走出一个门外。雨不算很大,但是雨声却很响亮。我伸手去接雨水,被它狠狠烫了回来。我立即扇了自己两巴掌,再次伸出手去接雨水,这次雨水是冰的。我再次扇了自己,把手都扇疼了,伸手去接雨,什么也感觉不到,这次是因为我的手麻了。我索性站进雨里,不到几秒钟就被淋湿透了。
早上我两次被吓醒,一次是唐兰的叫声:你尿床了!
她刚喊完我就醒了,不过我懒得理她。她的叫声并没有如她所愿,于是她装作刚惊醒的语调又叫了一声:你尿床了!
我还是不理她,装作熟睡。她自讨没趣,只好走出房间。接着我就再次睡着了。
第二次是被张小姐的妈妈吓醒,她的声音从屋外传来:哈哈,我还有两个月零二十九天。
她不断重复这句话,我实在睡不着就爬了起来。张小姐的妈妈仍坐在沙发上絮絮叨叨的对四周人说:我还有两个月零二十九天。我打开大门,门外一群白色的小鸟迅速飞走,地上只有一堆鸟屎,看不出昨晚下过雨,于是觉得心情很失落。我慢慢走进屋里,张小姐的妈妈四周坐满了人,大家终于开始关注她了,但是电视开着,所以好多人的注意力还是放在电视上。我也找了个位置坐下,盯着电视心不在焉的听着张小姐的妈妈说胡话。看腻了屏幕上单一的颜色,我就到处乱看,一不小心就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张小姐的妈妈终于停止了自己的讲话,人们的注意力都不在她身上了,她于是做了一个不雅的动作,挖鼻孔。那时她先是装作随意的四处看看,发现没人看她,她就将左手慵懒的放在脸上,掌心撑着下巴,五个手指随意张开,渐渐的,她移动自己一根不惹眼的手指,悄悄伸进了鼻孔。伸进去之后她的动作依然轻巧,搅了两下之后拔出手指,将那块异物置于食指上,再将拇指拿出,使其与食指相互摩擦。再过一会儿,异物变黑,她不动声色将其弹飞。
这是我观察出来的,并且仔细认真的总结出来,看样子我有自虐倾向。但是张小姐的妈妈那一套动作尚未结束,她用拇指弹异物,异物没被弹飞,而是粘在了拇指头上;于是她接着用食指弹,异物又粘在了食指上。如此循环了好多次,黑色粘稠的异物还是没飞走。张小姐的妈妈有些不耐烦了,便将手放下,把黑色粘稠的异物抹在了沙发上。这一系列的动作总算完成,张小姐的妈妈仍旧不动声色。
张小姐的妈妈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与挖鼻孔无关,与死亡有关。因为她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掉,并且对这一点显得相当固执,每个清晨她都会跑来告诉我们她还有多长时间,我们都是伴随她的声音醒来,她成了我们的闹钟,以及日历。再过三个月就到冬天了,我很想看看疤庄的冬天是什么样子的,张小姐的妈妈刚好可以给我计时。她的变化还有一样,就是跳得更高了。平时她不会轻易往上跳,但是只要别人在她面前提起“时间”以及与时间有关的东西都会使她纵身一跃。但她也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会往上跳,而是站在我们地下室大门往里一米处往上跳。比方说你问她多少岁,她就会立即跑到离大门一米远的地方,垂直往上跳,并且一边跳还一边发出叫声。到后来她的弹跳力越来越好,不需要太用力就能撞到天花板上。天花板是塑料扣板,撞上去不会疼,但是该扣板可能是免检产品,质量很不过关。这里就有一个国家免检的电风扇,用四个字形容它就是:喜怒无常。张小姐的妈妈只要跳一下,房顶就会给人摇摇欲坠的感觉。而且她总是撞在那一个地方,使那里格外白。
因此只要张小姐的妈妈在,我们都会克制自己,尽量不提到跟时间有关的话题。但还是不行,因为墙上的那台钟每隔一小时就会叫一次,也就意味着她每隔一小时就会叫一次。
就这样,张小姐以及和她长得一样的她妈妈,这两人我能够轻松分辨出来了。
每天早上我都会被张小姐妈妈的声音吓醒,无一天例外。我走出房门,她凑上来对我说:济济,我还有两个月零二十天。
为了让她知道我很厌烦,只好不予理睬,她并不会因此闷闷不乐。她总是守在沙发上,对每一个从房间出来的人说:我还有叉叉天。她通常一整天都坐在沙发上,也不怎么吃饭。她说自己是胃癌,吃进去什么都会变成癌细胞。我很惊讶,因为我一直以为女性只会得乳腺癌。她的饭量不及信哥爸爸的一半。老爷子每天都能看见我三次撞墙,心情很愉悦,吃起饭来还左右摇晃。我相信要是有人愿意每天为张小姐的妈妈撞三次墙,她的饭量应该也会增加不少,但是没人为她这样做,她只好自己撞天花板。
由于墙上钟的存在,她每隔一小时就会撞一次天花板,后来信哥把钟扔掉了。没了钟之后她也消停了两天,但是后来信哥的两个孩子爱上了磨牙,没东西啃的时候就开始磨。她觉得磨牙声音与秒针走动的声音很像,并且频率差不多,于是她就一直将天花板撞个不歇。每次张小姐妈妈一来,信哥就会把两个孩子赶出去玩。
那天一起吃饭,张小姐的妈妈先站起来报时:我还剩两个月。接着阿明就湿了眼眶,并且说:妈,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张小姐的妈妈:那你让我怎么死?
阿明:我一定会为你拍一部电影,主角就是癌症患者,表达了她与病魔做抗争的顽强精神。
张小姐的妈妈:结局呢?
阿明:死了呗,不死怎么能叫悲剧,不拍悲剧怎么能算作文艺片,不拍文艺片怎么赚文艺暴发户的钱。
张小姐的妈妈:我能不死吗?
阿明:这只是我的构思,实践早着呢。
我好奇的问:你还会拍电影?
阿明:我在台湾就是混文艺界的。
我问:那你拍过电影?
阿明:拍过电影啦,拍过好多。我被誉为台湾电影界最特立独行的人,我做导演那会儿,别人都喜欢改编小说或历史,我不一样,我最喜欢改编音乐,不过都没有成功。
我说:你拍歌舞片?
阿明:不是。
我又问:你为什么不带墨镜?
阿明:我很讨厌我的编剧,他是大陆人,写剧本速度太慢,场景都搭好演员都到位就等他剧本。后来演员说不要剧本即兴演,这下我高兴坏了,拍出来的想不是文艺片都难。我的编剧最擅长历史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爱新觉罗,他全写了个遍,不过我都不满意。演员即兴表演毕竟差了些,剧本迟迟不来,从冬天一直等到夏天,演员都热死了,扒光衣服对我说,导演我们拍原始人吧。后来又有演员对我说,再不拍我就去日本发展,反正衣服都脱了。然后我们又等了一个冬天,搭的景都塌了,我一拍脑袋就决定拍灾难片。没剧本还是不行啊,我就去找编剧催稿,编剧说他只写历史剧,灾难片太不考验编剧了。我说那你写一个能拍的历史剧给我啊,我快急死了。最后他从稿子下面抽出一本书拍在我面前说,里面剧本多得是,你自己选吧。我一看,原来是本初中历史书。
阿明说完将一杯酒饮尽,眨眨眼挤出一些泪花:那个编剧还气呼呼的说,妈的繁体字完全看不懂。
我问:后来呢。
阿明:后来啊,乡愁是——哦不对,后来我就气得夺门而出,外面下起了暴雨,几天几夜不休,河水猛涨,我就来了灵感决定拍一部关于洪水的灾难片,主题不是灾难,而是洪水。不过停滞了。
我问:为什么停滞啊?
阿明:因为洪水。
我大呼原来如此,又问道:再后来呢?
他说:那场洪水空前绝后,据说三百年不遇,我觉得不是,不过他说三百年就三百年呗,反正三百年前的人都死了。我们剧组的人随着洪水漂啊,漂着漂着就永远漂下去了,有人漂到树枝上被插死,有人漂到石头上被拍死,还有人漂到电线被勒死。不过我运气好,抱着一根大木头,一路畅通无阻的漂了几天几夜。那几天我一直在大木头上待着,肚子饿了就伸手从河里捞鱼,刨些木头皮然后钻木取火在木头的一头烤鱼吃。有一天我终于上了岸,一询问才知道我到了福建。
全桌人都惊奇的看着他,但是张小姐没什么反应,我觉得她下面肯定在不停跺脚。
那条废弃的公路上,除了有无数盏路灯以外,还有一个大型电子显示屏,镇里人都称之为“绿色电视”。所谓绿色电视,并不是说他环保,而是它长期淋雨导致显示器出了问题,任何红色的东西在显示屏上都变成了绿色,播放战争片的时候溅出来的血是绿色,西红柿也是绿色,屏幕上的动车也复古变成了绿皮车,个个女演员都像走火入魔,最主要的是红旗也成了绿色。
本来绿色电视是用来播广告的,但是这条路废弃了,因此它也失去了自己的价值,镇政府懒得修,就随它这么一直绿下去。绿色电视通常都会播放一些弘扬民族精神或者主旋律的影片,通常片头都会先蹦出来一行字,什么什么三八制片厂,这些字还不怎么稳定一直晃荡,本来应该是红色,现在也成了绿色。有时候还会放些动画片,动画片最在意颜色了,一般的也不敢放,只能播放蓝精灵。外国大片也会有,比方说绿巨人什么的,不过本镇人民逆向思维极好,都以为绿巨人本来是红的。
这是本镇的一大标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外人将此地称为绿色山庄,也有外人将此地称作牛庄。关于“绿色山庄”我已经解释过了,现在来说说“牛庄”。以废弃公路作为一条直线,然后作一个36度角,画出另外一条直线,该直线上有一座工棚,里面有一位姓朱的中年男子,和一群大黄牛。大黄牛就是朱姓人养的。至于养牛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以前一直有个外号叫做老猪,他当然不喜欢这个外号,为了让人们改口,他养过各种动物,但是那些动物都太缺少震撼效果,因此他的外号并没有随着他所圈养之物而改变。后来他一狠心养了许多头牛,渐渐终于有人改口称他为老牛。因此,那个名叫老牛的人,其实姓朱。这也就好解释之前我所说的那个名叫“姓孙的”的人为什么可以不姓孙了。
通过信哥的介绍,我们有幸认识了老牛。如你所知,我在D城时已经认识了一个名为老牛的人,他们两人的外貌完全不是一种风格,不过他们有一个相同点是都不姓牛。
疤庄的老牛(后面简称“老牛”)是个短小且不精悍的男人,通过废弃公路边的一条小岔路走进去,经过成片成片的旱田,看到第一个棵大树,走左边那条更窄的路,不到百步就能遇到老牛的牛棚。大门边养了三只狗,要是它们同时叫唤起来,你就绝对不会相信只有三只。我们很喜欢去看那些牛,每次看牛也要顺便看看老牛。其实我和老牛挺熟,但我觉得他于我而言一点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