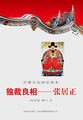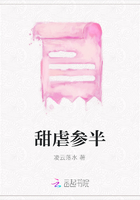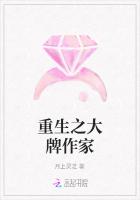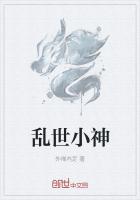柯庆施把毛泽东的讲话传达给张春桥,于是,张就赶快写出这篇文章,发表于《解放》半月刊1958年6期。张文先是引证了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肯定红军实行供给制的一大段话,强调这是“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也是“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他批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
他认为,这些人要刺激的,“并不是刺激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思想理论界的关注和争论。
此事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张春桥文章的基本观点也就是毛泽东北戴河会议讲话观点的复述和阐发,因此,自然引起毛泽东的好感和肯定。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转发了张春桥的文章,并发表由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编者按。按语说:
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这样,就使这篇文章非同一般了,不仅扩大了张春桥在全国的知名度,也成为张春桥以“无产阶级理论家”自诩的一个重要资本。这篇善于辨别风向、投其所好的文章,就成为张春桥后来受到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关键一环。当然,把张春桥直接带入“文化大革命”领导核心地位的,还是他伙同江青、姚文元共同炮制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些我们后边再谈。
3. 姚文元:看风转舵的文坛打手
1931年姚文元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其父姚蓬子曾是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作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为叛徒。解放后,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关于这件事,鲁迅曾写过一段很深刻的话:“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所谓‘文学家’,在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了,又立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姚文元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
姚文元于1948年在上海一个中学里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参加工作,一直在意识形态部门,如卢湾区团工委宣传部、区委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等。在这些部门中,他并非主要领导人,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业绩,但却颇有点小名气。这个名气概而言之就是,善于看风转舵、改变面孔和勇于讨伐文坛老将,无限上纲打棍子。下边就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一次是反胡风。姚文元因为父亲的关系,很小时就认识胡风。他曾公开赞扬胡风是“鲁迅的战友,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以有这样一位著名作家“胡伯伯”而引为自豪。并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胡风的著作,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专著。可惜,专著还没有完稿,批判胡风的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
姚文元一方面为自己的辛苦劳作泡汤而沮丧,另一方面也为稿子尚未送出而庆幸,不然就泼水难收了。但他赞颂过胡风是大家知道的,于是想了一条妙计:反戈一击。在1955年初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上,24岁的姚文元作了调门高昂的批判发言,说“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如此等等。这种180度大转弯使了解他的人大吃一惊。
这里附带说一句,张春桥和姚文元虽然早就见过面,但张对姚比较冷淡。正是在这次批判大会上,使张春桥感到姚文元是一个可用的“左”字号打手,而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结合。也正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文艺月报》发表了姚文元这次大会批判发言的一部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随后,姚文元又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多篇调门高昂的批判胡风的文章。1955年6月1日,经张春桥推荐,姚文元的一篇题为《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的文章,又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
此前的六年里,姚文元发表过八篇作品,但都是“读者来信”之类的小“豆腐干”。与这几篇批判胡风的文章真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这些批判胡风的文章是这位“文艺理论家”的发家之作。
凭借着那篇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青云直上。
再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姚文元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后的表现。在批判胡风大大出了一番风头之后,姚文元有一年多没有发表文章。据了解情况的人说,姚文元这不寻常的沉寂主要由于三个原因:一是他的爸爸姚蓬子由于同胡风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同潘汉年案有牵连,而被拘捕审查;二是姚文元本人也因此而受到组织的审查,要他交代与姚蓬子的关系,还有宣扬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三是与前两件事直接有关的是热恋的女友同他吹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这位小有名气的“棍子”再也提不起打人的那股劲。他只好请求张春桥的帮助,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新筹办的刊物《萌芽》半月刊,当了一位诗歌编辑。
姚文元这个人是很会看风头的。1956年到1957年春的政治缓和,提倡“双百”方针,特别是整党初期的鸣放,也影响到姚文元。于是,他也鸣放起来,发表了一些面孔完全不同的文章。比如《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论知音》、《放下架子》等,大喊“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而且公开赞扬了很快被打成“大右派”的王若望、刘宾雁等人的文章。按照当时的标准,姚文元的这些言论是足够划为一名右派分子了。这次又是张春桥救了他。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随后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就在这之前两天,6月6日上午,张春桥打电话给姚文元,透露给他这一重要消息,而且告诉他要轰《文汇报》。姚文元十分紧张,立即发挥其政治投机的特殊灵感,连夜写成一篇《录以备忘》的千字文,以上海两家报纸《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对待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谈话的不同态度为例,批评了《文汇报》编排的政治倾向错误。《文汇报》迫于6月8日后的政治形势,在6月10日刊登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
可是,恐怕连姚文元本人也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却产生了极大的政治效果。毛泽东这个时期十分重视上海《文汇报》,是当时抓的右派舆论的典型。从该报上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颇为欣赏,而且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当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同时让《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一篇《〈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两文同时发表于《人民日报》6月14日第一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同日的新闻节目中还作了摘要播发。
毛泽东的肯定、中央报刊的转载和中央电台的播发,这在当时是一件全国瞩目、非同小可的事情。柯庆施听过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马上下令召见姚文元,并当面夸奖他“阶级斗争的嗅觉很灵敏”。于是,姚文元一下子成了“反右英雄”,被提拔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时年26岁的姚文元顿时神气大涨,不可一世,大写批判右派的文章。从6月10日发表《录以备忘》开始到年底,在1957年下半年里,姚文元共发表大大小小的反右文章五十多篇,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坛打手,也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
虽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亲自出面为姚文元抹粉,称他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但棍子就是棍子,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打人的功能是没有区别的。
当然,直接使姚文元青云直上的是那篇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关于这篇著名的大批判文章我们在下边讲。不过,从上述反胡风和反右派的两段经历,我们就不难了解姚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被江青选中作为打开“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的先锋官不是偶然的了。
4. 王洪文:不想吃技术饭的“造反英雄”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时年38岁。
王洪文于193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郊区农村。小时除上学外也帮家里干一些农活。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志愿军入朝作战,但没有什么战功。1956年复员后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一个几万工人的大厂,先是当保全工,以后又当上保卫科的保卫干事。同厂托儿所的保育员崔根娣结了婚,这样就落户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十年的经历几乎是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当工人时不好好学技术,公开说自己“不想吃技术饭”,要“吃政治饭”。经济困难时期被下放到崇明岛种地,被大家评为:“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到保卫科工作后,经常偷拿厂里的东西,什么木料、花布、修房子的水泥等,以致“四清”时成为工厂里被清查的对象,当众出丑。从而也打破了他想当保卫科长的美梦。无怪乎他后来青云直上衣锦还乡时,得意洋洋地对小兄弟们说:“想当年如果提拔我当科长,我能造反吗?不造反,能够有今天吗?”
这就是曾被吹捧为“种过地,打过仗,又是工人领袖”的王洪文的真实历史经历。王洪文的真正政治经历是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开始的。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全国也就没有几个人会知道有过王洪文这样一个人了。
上边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下边就要进入正题了,谈一谈他们是怎样勾结成帮、青云直上、骄横一时、祸国殃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