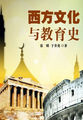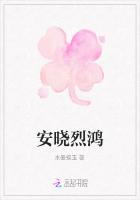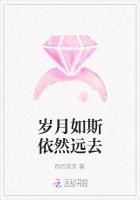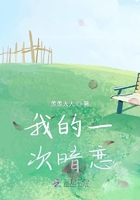有一段时间,中午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去大昭寺门前晒太阳。午后时分,我双脚不自觉地奔向老光明茶馆,来一碗藏面,倒上甜茶,只当是午饭。在老光明茶馆,总能结识一些陌生人做朋友,人与人的投契,“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甜茶满了,又见底了,阿佳不知道在我面前重复了多少遍倒茶娴熟的动作。直到夕阳日落,茶客稀少,我才起身离开。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人很容易陷入一种习以为常的程序生活,但在茶馆里的时光,并不是每一秒钟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内容。一杯甜茶里,注入许多未知的戏剧成分。茶馆,它一方面帮助人们克服隔阂、孤独、陌生、寂寞、无聊而创造出大众参与、集体共享的种种方式;另一方面,它提供的常常是一种精神的松懈、暇时的消逝、情感的释放。 连我这个异乡人都对茶馆如此痴迷,又何况是当地的藏民呢?
光明茶馆能够吸引大量茶客,因为甜茶,也因为这里的娱乐活动很多,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尽享乐趣。最常见的,就是打扑克牌、下象棋,还有“格尔让”。“格尔让”是一种手指弹击的、像克郎棋似的娱乐用品,藏族人将它从印度引进,使之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娱乐用品。甜茶和“格尔让”都是外来的,这一饮一玩,似乎毫不相关,在西藏却做到了默契。每遇婚礼、乔迁之喜、逛林卡等欢聚的日子,惬意的人们总是一边喝甜茶,一边弹击“格尔让”,玩得非常开心。
茶馆酒肆,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成像工具,生动地呈现出一个城市市井生活的真相。情感与欲望,常常不是因为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层次的忧患,而是从直接的生活表层,即从柴米油盐这一类生存状态的趋向所引发。 它反映着市民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心态,表现出浅近而表面化的喜怒哀乐。在这里,我看到真实生活镜头里的藏族人。我一直以一种高于宏伟叙事的方式去理解藏族人。我一直以为藏民都是为了朝圣而活着,为了终极宗教意义的理想而赎罪。我的目光只是注视着他们不食人间烟火,如同普罗米修斯献身的那部分精神呈现。而这无意间,也强加给每一个藏民不应有的精神枷锁。我曾视那些虔诚的藏民为神,反照没有信仰者的卑微弱小。但却没有意识到,原来他们亦是平凡大众,他们亦有选择生活的权利,选择实现价值的权利。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拥有对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自由。
我发现八廓街里,不同的空间地域展现出的多种存在状态。光明茶馆与大昭寺,磕长头的人与喝茶打牌的藏民,神灵与俗人,崇高与粗鄙,藏民的生活是那么的真实。在磕头念经,供奉神灵,在饮食男女,柴米油盐里,履行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教义。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因为产生不妥的是我们。妄图出走,逃出原本生活桎梏的人是我们。拉萨,是我们臆想出来,救赎内心的神灵之地。一旦与我们想象不同,就会悲伤失落。但这些与生活在这里的人无关,他们从不把灵魂、西藏、救赎挂在嘴边。只有我们一再滥用这些误以为深刻的词语。如同李敬泽所言,来西藏的人,向往西藏的旅游者和跪拜者,我们心中是不是深藏着不可救药的空虚和自欺?
四
在光明茶馆我认识了一个波拉(藏语,爷爷的意思),每次到茶馆,见他坐在角落一隅,手拿佛珠,念念有词。杯中的甜茶,总是满了又空了。有时遇见他的朋友,相邀坐下,交谈的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小道消息,大到国际形势,小到柴米油盐,都尽在甜茶里。他亦爱打牌,偶尔来两手,赢了钱就请周围的茶客喝茶,输了亦不苦恼,一杯甜茶入肚,一笑视之。后来,在交谈中了解到,他泡在光明茶馆的“工龄”已有三十多年。不管刮风下雨,午后时分,他的身影总能准时出现在光明茶馆。他被公认为光明茶馆的“元老”,颁发一个光明茶馆的忠实粉丝奖,绝对不过分。久而久之,光明茶馆成了他名副其实的藏身之所。他说起一件往事,当年他的妻子临盆,他恰好不在家。亲戚们四处找他,都不见踪影。经一个茶客的指引,亲戚们在光明茶馆找到了他。没想到他竟然在茶馆里悠闲地喝甜茶、晒太阳。当时,真把亲戚气得暴跳如雷。回到家,孩子已经出世。是个男孩,波拉和亲戚们都喜极而泣。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年,但波拉说,妻子偶尔还是会因这事与他争吵。再加上,有其父必有其子,儿子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也爱上光明茶馆。如今儿子娶了妻子,足下有两个幼儿,最近开了一间店铺。波拉小声告诉我,就开在光明茶馆附近。我一听,不由得笑了起来。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与这间光明茶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一间其貌不扬的老茶馆,却承载着多少人的甜酸苦辣,见证多少人生命中的悲欢离合。
光明茶馆,这里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典型的无时间性的空间世界:“这个不大的空间世界,受到局限而能自足,同其余地方、其余世界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然而在这有限的空间世界里,世代相传的局限性的生活却会是无限的绵长。……世代生活地点的统一,冲淡了不同个人生活之间以及个人生活的不同阶段之间一切的时间界线。地点的一致使摇篮和坟墓接近并结合起来(在同一角落、同一块土地上),使童年和老年接近并结合起来(同一处树丛、同一条小河、同一些椴树、同一幢房子),使几代人的生活接近并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所见景物相同。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
或许,对于茶客来说,他若不在茶馆,那一定是去往茶馆的路上。
吉祥天母节,看不见的鹊桥仙
一
吉祥天母节的前一天,阿佳对我说,明天就是吉祥天母节,你应该购置一件喜庆的衣裳。于是,我走进了八廓街的一间民族服饰店“在这里”,一件大红棉布长袍,瞬间映照我心。绣着牡丹,鸳鸯,生动逼真。一针一线,都是手工细活,可见功夫。牡丹花先用彩色丝线勾勒花瓣轮廓,再用小细珠串联,密密麻麻,工序复杂。衣裳的风格,沿用于古典旗袍,有一种自在从容的端庄。“女为悦己者容”,在阿佳的鼓动下,我便买下这件大红棉布长袍,为了赶赴一场吉祥天母节。
吉祥天母节,藏语称“白来日追”,又称为仙女节,是藏民族尤其是藏族女性祈求幸福美满爱情的大好日子。每年的藏历十月十五日,由木如寺全体僧众向拉萨大昭寺的护法王尊吉祥天女举行隆重的例行年祭。僧众于十四日清晨,将吉祥天母面具模拟像迎请到大昭寺顶圆廊下,于黎明时分沐浴。十五日旭日东升时,藏族女子盛装打扮,来到大昭寺,为吉祥天母献哈达,焚香话愿。据说,这一天是藏族女子求姻缘的最好日子,愿望很容易实现。
十月十五日一大早,我从睡梦中醒来。推开窗,阳光铺天盖地。着新装,对镜贴花黄。从旅馆出来,便是八廓南街。只见万人空巷,拥挤不堪。年轻的藏族妇女盛装打扮,穿皮袍,长及脚踝;头戴珊瑚、松石做的头饰,耳戴金银镶绿松石的耳坠。左手戴银镯,右手戴白海螺。甚是隆重。平时在八廓街摆摊,吆喝买卖的阿佳,今天全都不见影踪。空空的档位,只有老人闲坐于上,安逸地晒太阳,摇动手里的转经筒。原来,今天这个节日,相当于三八妇女节。女人享受放假权利,充分享受娱乐。但与三八妇女节不同的是,这里还多了一项权利。藏族女子可以随意向男子要钱,称为“白拉姆顿羌”(意为白拉姆的酒钱)。最有趣的是,男子不能回绝,否则就会折福。于是,在街上,我总能看到女子正大光明地向男子要钱,男子亦是大方,一脸微笑,从口袋里拿出零钱,还不忘说一声“扎西德勒”。女子接过钱,喜上眉梢。这让我看到平时缄默不言、辛勤劳作的藏族女子,开朗直诚的一面。尽管是向陌生男子要钱,亦是一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神色。
我和珊珊去光明茶馆喝茶,坐在我对面的是两个藏族妇女,后来几个康巴中年男人来茶馆喝茶,因为没有空位,便与这两个藏族妇女拼桌。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足为奇。但让我惊异的是,倒甜茶的阿佳每次为这两个藏族妇女倒甜茶时,身旁的康巴男人总是抢着付钱。两个藏族妇女的脸上,高原红绽开了花。不仅仅如此,今天妇女享受莫大的尊荣,喝茶,吃饭,包括零用钱,都是男人给的。藏族妇女今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与尊重。
“吉吉索索拉索罗,吉吉索索拉索罗”,虔诚的祈祷声萦绕在拉萨大昭寺周围,涌动的人群不停地向香炉香堆中煨桑。一炉桑烟,袅袅直上。大昭寺门口架起围栏,早有从各地而来的信徒排着长长的队伍,手里拿着哈达、酥油,等着进大昭寺敬献吉祥天母,其中以女性居多。尽管今天是藏族妇女的节日,收到很多馈赠的钱财物品,但藏族妇女的内心认为,没有吉祥天母,便没有这个节日。于是,妇女又慷慨地将钱财、哈达、酥油虔诚地敬奉给天母。藏族妇女将一切荣誉回归至天地间让人信服的神灵。我仿佛觉得这是一场关于信仰的传递,男子将钱财给予妇女,而妇女又将它献给吉祥天母。最终的所得,都归属于神灵天母。妇女最后看似无所得,但似乎又收获累累,内心丰盈充足。在施与舍、得与失之间,我们只看到要钱过程,殊不知,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操纵着这一场程序复杂的转盘。
现在想想,陌生男子的慷慨解囊,女子的正大光明,的确有一种理所当然的道理所在。因为这一天,藏族妇女是吉祥天母的仙女,呵护藏族妇女不仅仅是出于男人应有的道德责任,亦是宗教信仰的力量使然。
二
宗教故事,大多来源于传说。吉祥天母节的由来,亦有一段传奇的故事。班丹拉姆是个性格古怪的藏族老婆婆,她有个女儿叫白巴东则,长得虽不好看,但非常多情。白巴东则瞒着严厉的母亲,偷偷爱上了护主将军赤尊赞。没想到最终还是被严厉的母亲班丹拉姆发现了,母亲大发雷霆,把赤尊赞赶到拉萨河南岸的奔巴热山(法瓶山),每年藏历十月十五日,也就是"白拉日珠"这天才允许赤尊赞与白巴东则见一次面。这一天,又是藏历算法的“情人节”。
这节日的由来,与汉族的七夕相似。源于传说,相爱的两人,被迫一年一会。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一样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尽管汉族与藏族所处的地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性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心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忽然想起秦观,想起那一首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爱情层面时,则是相通的。”
燃灯节,一只失落的尿囊灯
一
燃灯节,藏语音译“噶登安曲”,意为“五供”。1419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是藏传佛教格鲁巴(俗称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成佛的日子。
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立者、佛学家,青海湟中人,3岁时被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授戒,赐号贡噶宁布,7岁出家,16岁往西藏深造,19岁广转法轮,讲经说法,25岁时,已深入研究了"弥勒五论"、《俱舍论》、《量释论》、《入中论》及律藏、五明等,并在寺院立宗答辩,产生了一定影响。36岁开始讲经收徒,同时系统地研习密法,42岁时智增慧广,对显密经论造诣很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被公认为藏传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宗教领袖、佛教寺庙和信徒,于藏历十月二十五日,诵经、磕头,举行灯供仪式等隆重的祭祀活动,祭祀宗喀巴大师和祈愿大师赐与善良的人们以聪慧、平安、吉祥、幸福。
燃灯节除了纪念宗喀巴,后来又加入了许多超度亡灵、祈福纳祥等内容。传说宗喀巴大师圆寂时,他的两大弟子之一的“克珠杰”(后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正在后藏的日喀则,听说这一消息后,就在牛蹄壳中加入一些不带腥味的牲畜脂肪油,点上祭灯供奉。这样做的原因,是藏历10月的时候,藏地牧区正在秋宰,为了让被宰杀的牲畜的亡灵得到超度升天,或者免于投生为“三恶趣“(地狱、畜生、饿鬼)。所以后来“燃灯节”的晚上,除了在寺院屋顶点上数百盏供灯,还要念经祈祷众生来世投生为“三善趣”(天神、阿修罗、人)。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传递困难,宗喀巴去世的讯息,传到各地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各地过“燃灯节”的具体日期,也有差异。比如遥远的藏东康区(昌都和四川甘孜、阿坝一带),就是在藏历的十月二十五日过燃灯节,比拉萨晚了五天。内蒙及内地一些信黄教的地方,因为不通晓藏历,一般把汉地农历的十月二十五日定为“燃灯节”。这种按农历过“燃灯节”的做法,有时与藏地是同一天,有时相差一个月,与农历春节与藏历新年的关系一样。因为格鲁派后来成了藏地的宗教“老大”,所以藏传佛教的其他派别,如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尤其是这些派别的信教群众,也都要过“燃灯节”。
二
在燃灯节前几天,藏传佛教的信徒们就开始做酥油灯,寺庙里的喇嘛每个人都要做三十盏以上的酥油灯。到了燃灯节的晚上,家家窗台上放满了酥油灯。藏族好友贡布说,窗前放多少盏灯也是有讲究的。在藏族人的观念里,单数的数字有吉祥之意,所以,酥油灯盏的数量都是单数。
晚上八点钟,大昭寺门前,水泄不通。法号、法螺、金唢呐声响起,僧人们在道路两侧、佛塔周围、殿堂屋顶、窗台、室内佛堂、佛龛、供桌等凡能点灯的台阶上,点上一盏盏酥油供灯,并在佛堂内供一碗净水,灯水相映,把佛塔、殿宇、佛堂、屋子照得灯火通明。特别是大昭寺寺顶围墙上那一圈圈闪闪烁烁、连成一片的酥油灯光,远远望去,那一盏盏排成一字形或宝塔形供灯犹如繁星落地,把夜空照得通亮。信徒们齐声唱起经文,悼念宗喀巴大师。我不懂藏语,但却能感受到一种空前绝后的肃穆与庄重。而此时,只需用心,无须言语。
转经的人潮如滚滚波涛,涌流向前。信徒手里的经筒飞转,诵经声嗡嗡不绝。大昭寺周边的煨桑炉,白烟蒸腾,直升夜空。许多人将大把的柏枝投入炉中,并对着大昭寺或天空念道“拉……索罗!”(神,必胜)每当这高呼升起,气氛会变得格外的热烈,人群中不分男女老幼,都会仰面向天,喊出这震撼人心的声音:“拉……索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