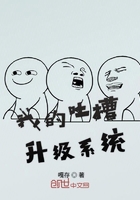光影交叠,钟小念眯着眼细细地看着手边的包。
橙色的鳄鱼皮Birkin,Hermes的招牌名包。
她仔细地看着,心口突地一跳,被灯光扫过的脸有些泛白。
不得不说,这包仿得不算精细,不去论拙劣模仿的款式,单是手指宽的提带上那偌大的Hermes,就假得太过张扬了。奢侈品向来推崇低调的华丽,何来会把品牌印得如此招摇?
这包是下午才从小嗳学校里取来的,她拿好包就被林奕扬接来这里。若不是她们提及,她根本不会注意到这包如何。
“我看这包蛮像假的啊。”女人低笑,眼里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
“怎么会,你的意思是钟大小姐去买假包?”旁边的人一唱一和,极为嘲讽地轻哼,“想当年钟大小姐一个包抵死我们一年生活费,林大院长怎么也不像是小气的人呢。”
“嘁——你看她那手糙得,我妈操劳了一辈子手都没像她那样。”
“也是欸,不是说她们家几年前破产了,我之前早听人说她在英国捡破烂欸。”
这个包再次给了她们八卦的材料,一群人故意地压“低”了声议论纷纷。欧梓羽靠在靳慕白肩上,一径微笑,沉默不语。
钟小念怔怔看着包,无暇去理会那刺耳的声音,一股莫名的焦急涌上心头。
她抬头看向门口,应该有十几分钟了吧,林奕扬怎么还没回来?
“可是这包假得也太离谱了吧,你看——”
“这包当然不是市面上专柜的包。”钟小念烦躁地开口,目光一落再入凝着手中的包,“你们要喜欢,也可以去巴黎总公司定制一个印上你姓名的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
包厢里骤然安静下来,七嘴八舌的人全都哑了口。
一瞬间,仿佛以前那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钟小念又回来了。
可是只有钟小念自己知道,她心里底气全无。强自镇定地抿了抿唇,她把握着提带抖得厉害的手收回衣角下。
“不——”
“原来林院长上次去时尚周就是为这件事啊……”靳慕白若有所思地沉吟,嘴角倏尔扬起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林院长还真是用心,亲自飞巴黎,当时问他他只说保密。”
这什么跟什么啊?
钟小念愕然地张大了眼睛,他是在帮她说话么?可是听语气,又带着他一贯反讽的嘲弄。
不止是她,一包厢的人都快跌破了眼镜。靳慕白和她以前的关系搁在那里,无论他什么时候搭话,无论他说什么话,都让人忍不住往深处猜。
“你看林奕扬多疼女朋友~”欧梓羽撒娇地戳戳靳慕白的肩,娇嗔一笑,“小白,你都不学着点。”
小白……
钟小念心头忽的一疼,抓着包急促地站起来,“不好意思,我出去一下。”
瞥着她单薄的身影逃跑似的走出包厢,靳慕白慢慢喝光杯中的酒,放下酒杯,轻拂开还放在肩头的手。
“怎么,生气啦?”欧梓羽打量他的神色,不怀好意地一笑。
靳慕白冷眼瞧着她,“我说过,下不为例。”
“不就一个昵称么,她以前可是天天叫呢。”欧梓羽不甘地撇撇嘴,见到他眼中怒气一闪而过,她这才有些收敛,放低了声,“我就开开玩笑嘛。”
原本看钟小念可怜兮兮低着头,一个人孤零零坐那儿,窘迫地被那群尖酸刻薄的女人围攻,她心里是有那么点欣喜。
哪晓得他竟然会开口帮她,一时胸闷这才叫着玩玩。
看着钟小念因为她那一句“小白”而露出的被人踩到痛脚的神情,她就知道,她叫对了。
KTV外走廊上,钟小念拨了好几通电话给林奕扬,一直占线。
她心里着急,再等下去就大晚上了。咬着唇思忖了几秒,她掏出手机给林奕扬发了条短信去,告诉他她先走了。等他挂了电话应该就能看到,到时候在电话里再细说。
看着显示信息已送达,她松了口气,抬起头。
“嗬——”
她一直心不在焉,根本没留意到他什么时候走到自己跟前了。
“有事?”靳慕白顺着她的眼神看向门口,了然地扬起眉,“要走?”
“我有点事。”钟小念干脆地点头,“刚才谢谢了。”
林奕扬哪会儿去巴黎给她订什么包,她知道他帮了他。
她才一转身,手臂便被靳慕白抓住,“不等他,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钟小念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犹豫不定到最后,心一横,抬眼看向他,“你有时间吗?不会耽搁太久,我不太清楚从这里到大学城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如果快的话,你可不可以帮忙载我过去一下,或者你告诉我坐哪路公交。”
靳慕白拧起好看的眉,淡淡道,“应该算是有时间吧。”
见着她还有些犹豫,他径自握住她的手,跨步走向门口,“走吧。”
黑色迈巴赫内,钟小念把向小嗳借包的事大概解释了一遍。
“你很担心她?”靳慕白问。
“是有点。”她眨了眨眼,看着前方沉寂的夜空,沉沉地叹了口气。
小嗳豪爽的性格在“人间”是出了名的,而且她和她接触了一个来月,知道她是那种没心事,大大咧咧的女孩子,有时为了帮她冲业绩还故意点贵的酒。
听她说家里是做房地产行业的,往常也是各种奢侈品不离身。
她不会故意借一个山寨包给自己,也断然不会不知道这个包是山寨包。
要是她没猜错,小嗳家出事了。她那天忙着和Joy斗嘴,未曾留意到她有什么反常的举动。今天去拿了包,她也是一副匆匆忙忙的样子。
刚才上车之后她就给小嗳打了电话,通了,没有人接。发短信过去,也没回。
小嗳不过才读大二,如果让她一个人面对这样颠覆的变故,估计她会难支撑吧。
钟小念咬着唇,恍惚间竟像回到了五年前。
爸爸尸骨未寒,妈妈又摔坏了脊椎躺在医院,成批成批的讨债人坐在家里。法院派出法警催她赶紧搬出去,她无力坐在地步上,看着爸妈精心布置的家被人搬空。
她数着钱包里所剩无几的钱,不敢买东西吃。
因为付不出医药费,好几天连妈妈的医院都不敢进。
原来没有钱的日子是这样艰难,走在路上她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寒碜的老鼠,连头也不敢抬。
那个时候深夜里她躲在医院门外,又冷又怕,第一次想到了死。
那个时候,死未必不是一个逃避的最好选择。
她曾经那么怕疼,却毫不犹豫握着刀片朝着手腕割了下去。
血流出去的感觉异常地清晰,她慢慢闭上眼,忽然想到万里之外的S大校园,想到那个住了二十年的小白房子,想透了许多事情。
那次她没死,醒来还在医院门口。
很讽刺,她一刀割得那么狠,却还是没割到血管。
她开始认命,先是低下头艰难地去求医院宽缓一个月,然后到处去找工作。因为David的缘故,那些小公司正式的单位连她的简历都不收。
不清楚怎么找到中餐馆洗碗的工作,也记不得才开始因为不熟摔破了好多碗换了几家餐馆,总之最后她可以蹲在那里洗一天的碗也不会摔坏一个盘子。
————————————————
这个月闭关忙毕业论文的事情了,所以拖到今天才更新,很抱歉,不好意思,就这么不明不白消失了一个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