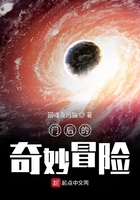正当茗波一家欢欢喜喜包饺子时,忽听院里有人声,茗波转脸一看,来的不是别人,却是他们的冤家张来福。茗波当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想着:“要过年了,他这是干吗呢,莫不是又来闹事的吧?”尽管他一再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但还是不由得紧张。这时张来福已到了伙窑跟前。茗波慌了手脚,将一张饺子皮捏成面团扔到箩筐里,刚想转身把张来福挡在院里,张来福却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张来福的到来,让茗波妈及巧芸也吃了一惊。茗波妈见张来福进来,慌忙跳下炕,想要问,却紧张得张不开嘴,心里直想着倪庆山能快点回来。张来福见茗波妈的神态,便嬉皮笑脸地说:“好端端的紧张什么,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咱们也不是外人,我就直说了,我来没别的事,只想着茗涛回来,你们有钱了,给我们借上三五块我们也过个年去。”
茗波妈一听这分明是狼借猪娃子,想占便宜的事,心里不由得生气,她瞪着眼睛说:“茗涛拿回来的钱我们全还账了,现在一分也没有。”
茗涛不知其中的缘由,只想着他妈虽是地主的女儿,当年庄里有些人嫌弃过她,也有人整过她,但她从没往心上放过。左邻右舍,不论谁家逢年过节有缝衣服之类的活,或者其他事情,只要她能帮上总要想着法子去帮。而如今,他家有钱了,他知道他拿回来的钱还在,但他妈为什么变得这么小气了呢?
茗涛看着他妈,为他妈感到羞愧。他又想着,他妈可能是苦日子过怕了,于是就掏出五块钱说:“妈,再别嚷了,我这儿有。”茗波妈一看茗涛已把钱掏出来向张来福递去,就气呼呼地说:“你钱多得很,拿来,有给他借的不如放着我花。”
茗波妈说着一把就把茗涛手中的钱狠狠地夺了过去。茗涛愣愣地看着他妈,却想不明白他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起先可怜着他妈,这时又有些气恨他妈了。但他妈不松口,他也奈何不了,只好坐到炕沿上抽烟去了。
张来福看着茗涛把钱递了过来,心里一乐,刚伸出手,还没来得及接,就被茗波妈夺了过去。他心里又气又恨,但脸上还是堆着笑容说:“他婶子,你就借给我们点吧,就三五块,也不怕我不给你们还的。”
茗波妈看张来福死皮赖脸的,就扯起脸说:“不借就是不借!”张来福说:“看他婶子,口气这么硬干吗?咱们都乡里乡亲的,就是要也该给点,何况借呢。”茗波妈说:“我就是借也给有良心的借,把你个坏东西,我凭什么借给你?”张来福说:“凭什么?就凭你们占了我的山头,偷了我的粮食。说实话,我今天就是来和你们要这钱的。”
茗波妈着实气了,她指着张来福说:“滚,还由着你了。那是公共的山头,就算要钱也轮不到你来要。你们的那粮食让哪个驴偷去,羞你们先人的好像没见过钱,有这么可怜的还不如一头碰死算了!”茗茹在炕上说:“就是,好吃懒做,还光想着占别人的便宜,欺负个人,看把你美的。”
巧芸一听茗茹在说混话,就忙遮掩着:“一个娃娃人,胡说啥呢。”茗茹不服气地说:“我们同学都这么说的,一个大男人家,老把脸装裤裆里使,连个女人都不如。”巧芸一听茗茹说得越不像话了,就顺手打了茗茹一巴掌。茗茹哭着说:“外面人都这么说,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
张来福立时涨红了脸,他不由分说就向炕沿冲去,茗波妈慌忙拉住:“你要干啥?”张来福说:“我把这个碎杂毛子两脚踏死去呢。”茗波妈说:“你敢!”刚好手边放着菜刀,她便提在了手里。茗波和茗涛也慌忙过来拦住。
张来福一看倪家人多势重,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就只好站住骂道:“你个碎婊子儿再胡说我把你的嘴撕烂去呢。”
茗茹吓得战战兢兢直往炕拐里钻,茗波妈见张来福还发着狠,就厉声喝道:“滚,没见过世上还有这种人,大过年的跑别人家里来闹事,你还有脸没脸?”
张来福本想厚着脸混点钱花,不想钱没混上,反倒受了一肚子气。他又羞又愧,嘴上却说:“都乡里乡亲的,看在要过年的份儿上,我也不多说了。你们把我看准的山头占去不说,还乱打人,我今天来就是和你们算这账的。老倪来了你给他说,这账让他记着,我迟早要找他算的。”说着就走了。
茗波妈看张来福走后,气呼呼地把刀往案板上一扔,就要打茗茹,巧芸和茗菡急忙拉住,才没打上。茗波妈坐着骂了茗茹几句,又想起张来福为谋便宜,已不要脸到了这种程度,只不知往后还怎样呢。于是她就又骂起了张来福。巧芸和茗菡劝了几句,茗波妈才渐渐平静下来。
一家人本来欢欢喜喜地包着饺子,不想被张来福这一打扰,气氛变得沉闷了起来。沉闷中,茗波想到了张来福的可憎,也想到了自己家的可怜。刚才张来福发威时,他本可以狠揍张来福一顿的。但他没有,他觉得张来福比自己更为可怜,所以他几次捏起拳头却又忍了。忍了,却又觉得自己窝囊,刚才要不是他妈拦着,茗茹说不上真会挨张来福一顿的,而他就在茗茹的跟前。不过若他妈不在,他也许会过去拼命拦的,何况还有茗涛在身边,他也不用多怕。但是,张来福已经走了,是被他妈轰走的。想来自己还算什么男子汉,在最关键的时刻竟如此怯懦。
茗波低头纳闷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巧芸说:“还不快包饺子愣着干吗?”茗波一听巧芸说他,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闷气,竟一股脑儿地全倒给了巧芸。巧芸被茗波咒骂了一番,心里虽气,嘴上却直催着茗菡几个快包饺子。
茗波骂够了,气出了,却想不通自己好端端的为什么要骂巧芸,为什么要给巧芸发这顿无名之火。想来这样一个和自己素不相识的女人嫁给了他,本本分分做着他的老婆。而他,往往却以雄者的姿态随意地辱骂她,蔑视她。她究竟做错了什么?茗波追问着自己,又偷偷地看了一眼巧芸。巧芸正在擀着饺子皮。茗波看到了巧芸的憔悴,心里猛然感到一阵针扎般的难受。这种难受,是一种怜悯,一种同情,一种疼爱,还是一种别的什么感觉?茗波说不准,他只知道自从巧芸进门以来,他从没有过这种感觉。今天他有了,他想给巧芸道歉,并且还想把巧芸抱在怀里踏踏实实地亲上一口。可是他没有。他心里开始流起了泪,流着一股愧疚的泪。茗波意识到了自己的丑陋和无能。
“我还算什么男人!”
茗波的内心有了一种强烈震撼后的激动,他不由自主地把手中的饺子皮狠狠地砸在案板上,巧芸、茗菡被茗波的这一举动又吓了一跳。
茗波妈正坐在炕上咒骂着张来福,忽见茗波把面砸到案板上。她知道茗波又给巧芸发狠,于是半跪起身子大骂道:“茗波,我把你个不要脸的,不想包了滚着出去,把你还能得不行了,少在这里耍你的威风。”茗波自知羞愧,也没说话,就出去扫院子去了。
巧芸看着茗波的背影,内心产生一种说不出的酸痛。在她的心里,茗波是她的丈夫,是她终生的依靠,所以她对他百依百顺。然而,她的内心却是那样的孤独凄清。她面对着的,是一张冰冷的面孔和喋喋不休的无情辱骂。男人的体贴和疼爱对她来说太遥远了,虽然她在梦中都渴望着那种生活,但那毕竟是梦境,与现实有着极大的差距。
巧芸认命了,所以她默默地暗守着孤独。就在此时此刻,她也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悄悄地忙着包饺子。
饺子包好后,茗源就跑出去催他大哥赶着贴对子,巧芸和茗菡忙着炒臊子下长面,茗波妈从箱子里取出茗源几个的新衣服,准备让他们忙完活就穿。茗茵和茗茹小姊妹也忙着糊窗子贴窗花。
茗茵和茗茹贴好窗花,倪庆山进来一看心里也是乐滋滋的。茗波妈见倪庆山进来,本想说张来福借钱欺负人的事,但一想大过年的,她若说了,倪庆山定要去找张来福算帐,或是在家里乱骂一通。所以,尽管她真想把张来福一把捏碎,但张来福寻茬的事她仍然只字没提。偏茗茹不知高低,见她大进来,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倪庆山果然一脸怒气,他出门提把铁锨就要去找张来福。茗波妈慌忙拦住说:“大过年的,你干吗去?全当那是个可怜虫罢了。”倪庆山把老婆一把推过说:“婊子儿,让他骑到老子头上撒尿,我就趁过年揭他的皮呢!”
巧芸和茗菡一看,也就慌慌地出去拦挡。倪庆山还想去,却猛然想着大过年的,好不容易全家人欢乐一回,张来福已经搅和得够扫兴的了,若自己再去一闹,家里的这年咋过呢。所以他强压着怒火进了屋。进了屋却又觉怒气难消,就又叨叨叨地乱骂了一通。
茗波妈也不搭理,只忙着和巧芸做饭。吃过饭,倪庆山在耳房将各尊神的牌位子供好,就喊茗波、茗源过来磕头放炮。茗波妈将瓜子、花生等倒在碟子里,茗源端到耳房炕上,他们做好了守岁的准备。今年因为各人都有新衣服穿,还有各种吃的,再加多了个巧芸,年过得格外热闹。
茗波看他妈把装干果的碟子放到炕上,就取出扑克牌要玩。巧芸见耍牌,就第一个冲了上去。茗茵、茗茹也上炕去挨巧芸坐了。茗源骂着不要茗茹。茗茹兴冲冲的,见茗源不要,就有些失望地看着巧芸。巧芸心疼地把茗茹往怀里一拉说:“不要就不要,茗茹和我同玩一牌。”茗茹一听她大嫂要她,就又得意地看着茗源。茗源见他大嫂袒护着茗茹,也就没再说不要茗茹的话。
茗波妈待巧芸一伙围成圈坐定,也就满面欢笑地上炕去坐在旁边。倪庆山在地上转着,看一家人乐融融的,果是春风满堂、气象更新。虽然他一看茗涛就来气,气他胆大且不受管教,致使招来许多祸殃。但这会子是过年,儿女们坐着半炕,看他们开心的样子,他也不由得满心欢喜。他甚至庆幸今天没去找张来福,要不然,这会子的欢乐早不属于他们家了。
倪庆山想着,便拿起茗涛给他买的酒自斟自饮了起来。他还想着,应该把张来福和魏新旺叫来,让他们看看这是什么酒!
这时,富梅跑来说她大叫倪庆山过去玩儿。倪庆山笑着说:“大过年的,还要守岁呢。”茗波妈说:“现在是新社会,咱们也得改革改革了。今天大家都这么高兴,想玩就玩去吧,有娃娃们守着就行了。”倪庆山想想也是,儿女们玩耍,他在一边转着也实在无聊,就提着一瓶酒去了。
第二天一早,茗波几个正玩得热闹,突听外面锣鼓响,茗波把牌一推说:“快,人家都出行去了,咱们也走。”巧芸因把自己的牌让给茗茹玩,她在一旁打着盹,迷糊中听茗波说要去出行,就爬起来跑伙窑里找出两根红布条,茗波和茗源接过布条出去拴到驴头上,然后赶着驴就往庄外跑去。
在庄外的一块空地上,已经站满了牲口和人。熊金保打着鼓,张世清敲着锣,几个老汉拿着香表及酒敬着土神。那些牲口被锣鼓声惊得乱踢乱跳。它们想跑,刚到一处,几个娃娃撵过去放一阵鞭炮,它们吓得又折回头。茗源和他大哥把他们家的驴也赶进圈里,就跑着放鞭炮去了。刚玩到高兴处,茗源猛然看见张正福家的红梅穿的衣服很耀眼,他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茗源正出着神,熊富生跑过来说:“倪茗源,你在干吗呢?”茗源说:“我咋看张红梅穿的衣裳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熊富生说:“你曾说过你们家衣裳和粮食一块丢了,这衣裳是不是你们家丢掉的那件?”茗源猛然想起这正是他妈没舍得让茗茵穿过的那件,他心里纳闷:“粮食不是魏新旺家偷的吗?可裤子秋艳穿着,衣裳张红梅穿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但庄里有他和红梅的传言,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红梅,更不希望这事与红梅有关,所以只好站在一边发愣。
熊富生看出了茗源的心思,他拉一把茗源说:“走,咱们过去问问。把这衣裳的来历搞明白,你们粮食被偷的事也许就搞清楚了。”茗源还犹豫着,熊富生说:“倪茗源,你怕个啥,到跟前你不好意思开口我给你问。”茗源这才跟着熊富生向张红梅走去,但他心里总忐忑着。他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只想着,但愿这事与红梅没有任何关系。
熊富生并不在乎这些,他只想着给倪茗源帮忙。所以他到张红梅跟前就问:“张红梅,你穿的这衣裳是哪里来的?”